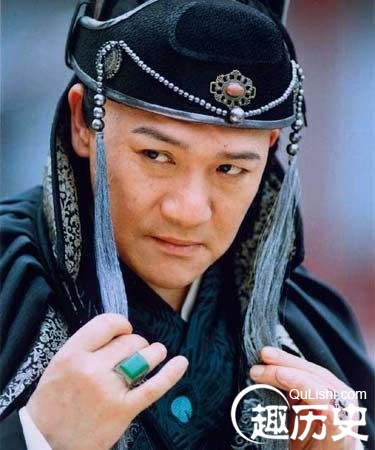|
二,崇祯有无下过收葬魏忠贤骸首的密旨? 这一点,至少是缺乏可信史料来佐证的,毕竟,“传谕收葬忠贤骸首”一说,仅仅出现在并非专业史料的古人笔记中,且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崇祯下过此密旨,也不能轻率的说成“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1,至少崇祯在位期间,从未给阉党“逆案”平反翻案,直到死前,亦未留下重新肯定魏忠贤或对钦定阉党逆案有所反悔的只言片语。 2,当时京城面临兵祸,而京营兵力和城防任务大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其他宦官眼中,虽说魏忠贤之死与己无关,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心也难免会存在于部分人中。崇祯若真的下过收葬的密旨,也没什么值得做文章的地方,合理的解释:那不过是笼络和鼓励宦官的一种策略。历史上不乏类似事例,康熙时期,为了全力对付吴三桂叛乱,康熙就收回了本已发出的裁撤其他二藩尚可喜、耿精忠的谕旨,但没有人会说康熙此举“是对藩镇存在价值的重新肯定”。与所谓的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样,康熙此举亦属权宜之计罢。 3,崇祯在亡国前尚为自己开脱责任:“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甚至临死前也不忘责备臣子:“皆诸臣误朕”,这哪里有“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的意思?
若真要举出崇祯对自己全盘否定的例证,还不如随便列出其众多罪己诏之一,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在李自成军将陷临晋时,他下罪已诏曰:“...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从这里可以看出崇祯对自己的责备和反省,比起传说中的下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事要深刻得多。 三、一点后话 关于魏忠贤此人,是否如天启皇帝所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及是否如原帖作者所谓“他(魏忠贤)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偶就不多说啦。正如一个人定要说煤球是白的,你没必要跟他抬杠一样。 实际上,为阉党翻案的黑白颠倒事例,早在朱由崧的南明小朝廷时就有了。弘光元年(1645),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操纵下,原阉党逆案中刘廷元、吕纯如、王韶徽、徐兆魁等一大批人被分别“予谥荫祭葬”或“复原官”[10]。这不合人心的举措招来时人广泛批评,如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所著《幸存录.门户杂志》中就说:“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虚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 综上可见,说崇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并为魏"修坟立碑",是经不住推敲的,至于是否下过收葬密旨,亦属不能肯定。以上拙见,或有不当处,尚望转帖者或原帖作者指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