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远]对天桥的美好想象从何而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5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1月30日 徐鹏远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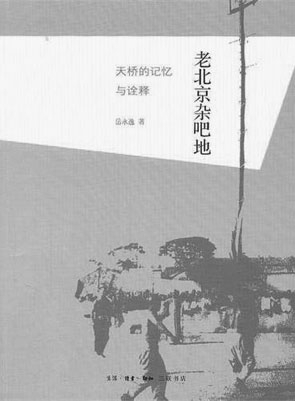 《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岳永逸著,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一版,49.00元 作为老北京市井文化的聚集地,天桥已经成为一个符号,频现于众人的笔底。对于老舍、张恨水笔下那个已经失落了的江湖,大家似乎充满了怀念。但历史上人们的真实感受未必如此。岳永逸先生在新著《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中提到在解放初期天桥是作为“邪恶的杂吧地”(P374)而接受整治的,天桥民众特别是艺人们也是真心欢迎和拥戴的(P399)。这揭示出,其实是我们怀着现实的诉求改写了天桥的形象。 《老北京杂吧地》分为绪论、上编和下编三部分。绪论主要梳理了以往的天桥叙述,并阐明自己的思路和视角,基本属于学术研究中的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案;上编是根据田野调查整理出的访谈材料;下编则是基于不同视点的理论阐述。尽管全书符合规范的学术体式,而且明显是将下编作为核心,然而最引人注意、最有意思的地方却是上编的“口述史”,从篇幅上看,这一部分就将近全书的2/3. 14位访谈者中既有天桥老艺人及其后人或传人、当年的观众,也有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其中有12位都出生于上世纪前30年,他们见证了天桥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他们的叙述中既有坐视沧桑的感慨,也有淡看春秋的平静;既有身怀绝技的骄傲,也有谋生艰难的落魄;既有把式行当的规矩,也有市井江湖的世故;既有以充谈资的轶闻奇事,也有未必入流的学问常识……通俗的文字里具象出一个我们似曾相识却又陌生新奇的“老北京杂吧地”. 当然,口述材料的精彩并不表示可以忽略这本书的理论价值,恰恰相反,此书在学术上的闪光点是极难被掩盖的。在分析了施坚雅、艾莉森、王笛、黄金麟等人以往的城市研究之后,根据“八臂哪吒城”的传说以及老北京城的“凸”字形态和内部的具体功用,作者提出了独特的“城市生理学”的说法:“外城、天桥是下体,但又不仅仅是下体,它既是与内城、紫禁城这个上体相对的下体,又是涵盖、承载和孕育上体的下体,是低俗而又神圣和伟大的下体。”(P327)这一描述不仅概括出天桥及外城的杂吧地特征,也体现出其在北京城整体内的区域意义。 前面说过,这本书更适合作为一本回忆录或者口述史来阅读。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整本书在理论上始终没能回应这样的问题:既然天桥如此“杂吧”,拥有着“下体角色”涵盖的种种不堪形象,甚至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解放后整治之前处于“失范”状态(P339),那么为何于今又会转变成一个“失落的江湖”而获得美好的想象呢? 书中提到的商业化大潮固然是原因之一--“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一度被冷落的技艺首先被定性为文化、传统、国宝,成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想兼具的象征资本”.(P429)然而这个原因无法解释许多人其实并不喜欢那些具体的技艺,很多当年的营生--譬如蹭油的--放到今天也未必有市场、受待见。他们真正怀念的是那个抽离了具体内容的、意象化的天桥。而且书中也提到过的天津“三不管”,虽然与天桥有着相似的形态和功用,却没有获得同等的殊荣和凭吊,这又如何解释?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天桥早已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想象体。一方面,由于故都身份,旧京以及天桥极其幸运地得到许多文人的偏爱,从而成为了一个超越实体的文化意象。相较前者,后者拥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也承担着更厚重的情感和更深刻的意义。赵园先生曾说过,北京“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北京:城与人》)于是这样一个天桥对于当下,不仅具备唾手可得而又韵味无穷的审美意义,更凭借那隔日的乡土味道慰藉着闹市里奔忙疲沓的心。失落不是因为挥别昨日的江湖,而是因为对今天太不适应。 另一方面,老北京独特的城市生理结构和文化肌理,天然地决定了天桥作为与“上体”相对的“下体”,独立于皇权体系之外而自成天地。其外部虽然显示出与“上体”相反的混乱、不洁和愚昧,却在内部构成和运行上呈现出与“上体”相似的层级、模式。这样的“下体”可以不依靠“上体”而独自成活,也可以平静地接受着“上体”的支配和统辖,无怨地供养着“上体”,但同时也保存了颠覆“上体”甚至取而代之的实力和可能。岳氏书中表达过类似意思:“地处内城的紫禁城是一个绝对神圣、威严的地方,而地处外城的天桥则是一个可以放纵、寻欢作乐、为所欲为的地方,是一个有着臭水沟、妓女、艺人、烟馆、倒卧、缝穷等显露人生众相的肮脏、邪恶、下贱的地方,也是任何处于非主流的个人或者群体都可以染指的’非法‘地方。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就曾经计划在天桥召集群众大会。晚些时候,在京西涞水县成立的中国三教道德圣会也曾以天桥为据点,在北京进行宣教活动。这些都被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府千方百计地防止、规训,希望能纳入他们认为的正常轨道,在自己的掌控之中。”(P327)这样的一个天桥江湖实际上寄托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侠客梦”.在经历过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年代后,人们急切渴望拥有一个能够逃离体制的江湖,于是天桥这样一个虽被神化却真实存在过的江湖便沾染上满足现实诉求的理想色彩。这里的江湖不是小说中那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世界,也不尽同于范仲淹“处江湖之远”的所指,有些类似于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却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政治诉求,也不与权力体制界限分明,只是单纯地希望保留一份退隐性,让人们在找寻快乐的同时享受自由,回归世俗的生活本身。 不过,往者不可谏,来者似乎也未必可追。昔日位于“下半身”的崇文、宣武如今已并入东西二城,“招安”于“上半身”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宋海年]为消失的村庄存留历史
- 下一篇:[何承伟]与钟敬文谈《故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