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波: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44 《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邹立波 参加讨论
二、格桑泽仁推动战时汉藏贸易的具体策略 格桑泽仁建言“西陲企业计划”、创办近代企业来推动汉藏贸易应基于两大目的。其一是辅助抗战资源的供应,改善战时汉藏关系。另一目的则为应对“商战”,通过振兴汉藏贸易,抵制英印商品侵销和藏区资源外流,挽回国家利权。对此,康藏贸易公司在1944年十分明确的申明,公司建立的目标在于“维护国权、拥护抗建(全称为抗战建国——引者注),不论环境如何困难,力求促进增强康省与西藏、中央与拉萨间之关系经济联系,以图挽回利权而免整个西藏经济商业为英印方面所操纵支配”。[20]因利权之争,格桑泽仁甚至有意规避借道印度、运销内地商品入藏。云南康藏茶厂报告中就将创办缘起归结为:“为巩固滇茶藏销市场及谋避免印缅境内之苦难与不当之损失起见,实有恢复北路运销之必要”。[21]可以看出,格桑泽仁推动汉藏贸易的重心是传统的陆路商贸。 但是汉藏传统的陆路贸易路线极为漫长。驮帮由丽江至拉萨约需80天。由康定至拉萨则要1年。[22]跨区域和族际通商特征非常显著。政治环境、交通条件、运销方式等均显恶劣、陈旧。如何突破种种束缚,推动汉藏贸易,适应战时需要,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抗战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格桑泽仁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开拓性的贸易策略。 第一,以政护商,以商促政,将商业贸易与国家力量有机结合。 传统的汉藏贸易以私家商号经营为主。商业力量分散。资本相对薄弱。各商号以盈利为目的,常有掺伪作假行为,市场竞争力较弱,无力承受和应对英印商业资本在藏区的扩张。在抗战前大行其道的“统制经济”学说影响下,国家介入乃至直接统制边茶等重要战略物资,受到抗战期间业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23]格桑泽仁援引成案,将国家力量引进“西陲企业计划”及其实践中。按照计划,拟建的西陲企业公司在藏区开展活动,“必要时由公司呈请中央转嘱拉萨政府(指西藏地方政府)给予保护,即可以达到保障之目的”,又可“与有关西陲之康青滇等省府协议及各地国家银行联络合作,以统筹计划,办理西陲经济金融各事宜”。[24]事实上,康藏贸易公司、云南康藏茶厂多次在原料采购、商品运销、资金贷款、资源开发等方面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或得到政府大力协助。 另一方面,格桑泽仁策划由云南康藏茶厂或康藏贸易公司统购统销汉藏贸易中的茶叶、羊毛等物资。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已陆续对重要农矿产品强制实施统购统销。针对北路销藏滇茶产制混乱的状况,格桑泽仁有意借助政府权威,将北路各大茶商以入股形式整合进茶厂中,“统制藏销茶叶”,以期达到禁绝杂牌劣茶、扩充销藏市场的目的。[25]康藏贸易公司开采后藏硼砂、收购西藏羊毛等业务,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统购统销。 国家力量的引入能够为战时汉藏贸易发展创造出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资源和资本的集中增强了商品产制运销规模化和应对市场波动的总体实力。但是推动贸易发展、沟通汉藏经济联系并非唯一目的。云南康藏茶厂创办后,格桑泽仁与管理层屡次强调,“本厂之事业非徒为商业行动,抑别具政治作用之大义”,即“谋求汉藏两民族政治经济之联系目的”。[26]格桑泽仁“康藏商人代表、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双重身份正是对“商”与“政”关系的极佳诠释。 第二,采取“产销合作”原则,整合、发挥“官商”与私商的各自优势。 在传统汉藏贸易中,商货的生产与消费相互分离。商货在内地生产后,由汉藏中间商合作运销到藏区,再批发或零售给消费群体。但是藏区的政治环境不容许国民政府完全掌控汉藏贸易。汉藏中间商仍然扮演着难以忽略的贸易媒介作用。为此,“产销合作”原则被运用到云南康藏茶厂、康藏贸易公司的产制运销中。 以云南康藏茶厂为例。茶厂产销合约书规定,“依据产销合作之旨趣,凡滇境内产制运输事宜,由甲方(指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本政府立场,给与充分便利;在康藏境内运输事宜,由乙方(指康藏商股代表人格桑泽仁)本地方立场,尽量推进”。[27]也就是说,茶厂原料采购、产制技术、厂务管理及运往丽江销场等事宜,由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统筹安排。推销业务交由入股商号负责。茶厂在下关设有制造部,又将营业部设在丽江。制造部在原料收购、雇驮运输及“实际出品方面,得藉官股,大力占到种种便利”。流动资金“则多赖滇公司(指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借垫及短期借款,以为调节”。[28]经格桑泽仁推荐,营业部主任由从商30余年的丽江“达记”号商人李达三充任。借助达记的声誉和推销,康藏茶厂所制紧茶颇受藏商欢迎,“在丽(指丽江)能独树一帜,信誉日隆”。[29]格桑泽仁利用政治声望,在“产销合作”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沟通、协调作用。1943年茶厂所产成品茶的2/3运往丽江推销,1/3发往维西、德钦销售。经格桑泽仁联系函商,饼茶运至维西后,即委托仁和昌商号代理销售,运到德钦的紧茶则委托达记代理。[30]由此,茶厂能够结合国家资本、产制设备、技术优势、政策扶植与传统商号的商业信誉、人际资源、推销能力等,实现公私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实力整合。“产销合作”原则是对传统边茶销藏方式的继承和发扬,有效弥补政治环境限制下“官商”无法应对藏区特殊运销状况的缺陷。 第三,实施跨省贸易合作,破除省际贸易藩篱,注重区域间商贸协调。 抗战期间,川、滇、康、甘、青各省区是商货进出西藏的主要产销和中转区域。各省区出产商货种类有异有同,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竞争。如抗战前川茶、滇茶已在藏区市场上形成竞销态势。1935年四川茶商控诉,“康藏概为川茶销场,今则西藏地方已为滇印唯一销茶处所,川茶但销西康境内”。[31]部分川康人士抱持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不满滇茶销藏,竟直言道,“抵制边茶不独印茶,近年云南亦如印茶形式以滇产造成砖甑贩藏售卖,无非争此利权耳”。[32]省区之间既无贸易合作之事,商业资讯亦不互通。 格桑泽仁特别重视跨省经济合作。在1940年制造西陲适用货币呈文中,格桑泽仁已将西陲各省区视为一个联动的经济整体,建议“应即充实康定、西宁两中央分行,并宜加设丽江、拉萨两办事处,依西陲经济商业之周转情形,必须此四地贯通联络,始能有效”。[33]由于身居滇、康两省贸易机构要职,格桑泽仁最先提出和实践边茶的跨省产销合作。 1942年初,日军侵入缅甸,仰光沦陷。滇茶销藏南路中断。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被迫筹辟紧茶由滇入藏的运销路线。5月,居留康定的格桑泽仁致函云南康藏茶厂,建议茶厂与康藏贸易公司“以最善之方法共同合作”,复苏边茶销藏市场。[34]为尽快促成合作,格桑泽仁数次致函郑鹤春,商定产销合作办法,以便大量运销滇茶销藏,且承诺可由康藏贸易公司提供运输便利、协助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郑鹤春随即复函,愿以佛海茶厂所制千余驮紧茶运往丽江,分批试由康藏贸易公司承销。[35]至次年8月,双方在付款方式、脚价运费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合作最终破裂。格桑泽仁无奈的函复郑鹤春,“康藏公司本年拟向贵处定购二百担佛茶一事,其主旨为保持双方联系,发展北路运销,以待双方将来互需互利之较大合作……此事即暂作罢。康藏公司今后若有滇茶之需要,亦又可向康厂分购”[36]格桑泽仁倡导和推动省际贸易合作的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合作的意图相当清楚,即摈除区域贸易界限,不分彼此,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增强贸易竞争力,为内地与藏区之间商品销售、流通创造良性的市场环境。 第四,遵从藏人的商业文化和消费心理,尊重藏人的消费习惯。 格桑泽仁年少时家道中落,由其父“劝令习商”,曾跟随滇商“往德钦操奇计盈”。[37]所以对藏区的商业环境、消费形态较为熟悉。汉藏贸易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族际交往,也是不同族群之间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在“西陲企业计划”中,格桑泽仁就已特别提醒,“由内地调派人员服务,亦须仿习藏人之衣食语文,而保持所谓‘跑草地商人’之本色”。[38]汉藏传统商人,尤其是草地商尊重和模仿藏人生活习惯,将贸易活动巧妙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格桑泽仁主张极值得借鉴此类传统贸易策略。 坚持仿照销藏川茶旧样制造砖茶是格桑泽仁顾及藏人消费感受和商业习惯的另一突出表现。川省砖茶由荥经茶商创制而成,色味俱佳,在藏区极受欢迎,销路甚畅。为满足藏人购茶习惯和饮茶需要,格桑泽仁多次鼓励、协助云南茶商、技师试制川装茶或川省砖茶。云南康藏茶厂筹建过程中,依照格桑泽仁的意见,试制砖茶的重量、规格、形制等“式样完全仿照藏销川茶之旧样,即圆长方形。大砖上用黄丹印一‘云’字。小砖上略贴金箔”。[39]对于仿川茶形制的缘故,格桑泽仁解释称:“藏人用川茶已久,秉性固执。吾人之滇茶创制,其质味上尚须附销人相当致力宣传,求其通行,若再由形式上之不同,令买者猜疑,岂不更加附销之困难”。[40] 因此茶厂商标、广告的设计同样充分考虑到藏人消费群体的购物心理和文化习惯。商标最初拟用“燃宝牌”图案,后改称“宝焰牌”(  )。经格桑泽仁推荐,茶厂专门函请学者杨质夫缮绘商标图案。[41]图样和广告由格桑泽仁审阅后送交茶厂印制。商标图案与七政宝之一的神珠宝( )。经格桑泽仁推荐,茶厂专门函请学者杨质夫缮绘商标图案。[41]图样和广告由格桑泽仁审阅后送交茶厂印制。商标图案与七政宝之一的神珠宝( )极为相似。作为常见的藏传佛教符号,神珠宝的象征内涵往往与财富有关。此外,广告词汉藏文兼具。汉文广告写为:“原山设厂,份量加重,诸君赐顾。大量制造,质料提高,认明商标”。藏文写作: )极为相似。作为常见的藏传佛教符号,神珠宝的象征内涵往往与财富有关。此外,广告词汉藏文兼具。汉文广告写为:“原山设厂,份量加重,诸君赐顾。大量制造,质料提高,认明商标”。藏文写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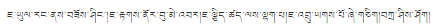 (产自茶区,宝焰商标,份量实足,茶料纯良,圆满吉祥)。[42]商标、广告分别用道林纸、厚磅纸印制,贴附于茶筒或茶箱内,以利宣传推销。
(责任编辑:admin) (产自茶区,宝焰商标,份量实足,茶料纯良,圆满吉祥)。[42]商标、广告分别用道林纸、厚磅纸印制,贴附于茶筒或茶箱内,以利宣传推销。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张永攀:西藏研究20年评述
- 下一篇:变迁、认同与共生:拉卜楞地区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