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晖丨书籍史,可不仅仅是书籍的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2/03 06:12:3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近年来,书籍史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从上世纪初“新目录学”的兴起算起,书籍史在西方已有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但迄今在理论和方法上仍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性较强、赢得广泛共识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尝试梳理和整合书籍史的理论与方法,总结书籍史研究的核心旨趣,探讨书籍史的定义与研究模型。 
书籍史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广泛 书籍史是目录学、历史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汇的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其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十分广泛。举其大者,主要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中又以来自英美学界和法国学界者居多。 第一个方面是出现于英美学界的“新目录学”,这是书籍史较早的一个理论来源。新目录学又名“分析目录学”,它在书籍的文本属性之外,对书籍的物质形式投以特别的关注,主张对书籍版本的各种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细致分析。新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凸显了文本的物质性。 第二个方面是麦卡锡提出的文本社会学和麦克盖恩提出的“文本的社会化”,同样来自英美学界,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这两个理论都强调文本的社会属性,指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一个人构建的,而是由书籍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的诸多参与者共同构建的。法国学者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理论与强调文本社会性的理论密切相关,副文本是作为主文本的书籍正文之外的封面、序跋、广告语、插图、版式、字体等,这些副文本是由作者之外的出版商、评论者等提供的,对于文本意义的建构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法国的著名史学流派——“年鉴学派”。书籍史上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印刷书的诞生》就是由“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吕西安·费弗尔与印刷史学者亨利-让·马丁于1958年合作推出的。这部书用年鉴学派的方法来研究欧洲近代的书籍发展史,用社会经济史的量化统计方法来观察欧洲出版业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回答印刷书籍的出现如何影响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问题。《印刷书的诞生》标志着书籍的历史正式登上了历史研究的舞台。书籍的历史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书籍的发展史与周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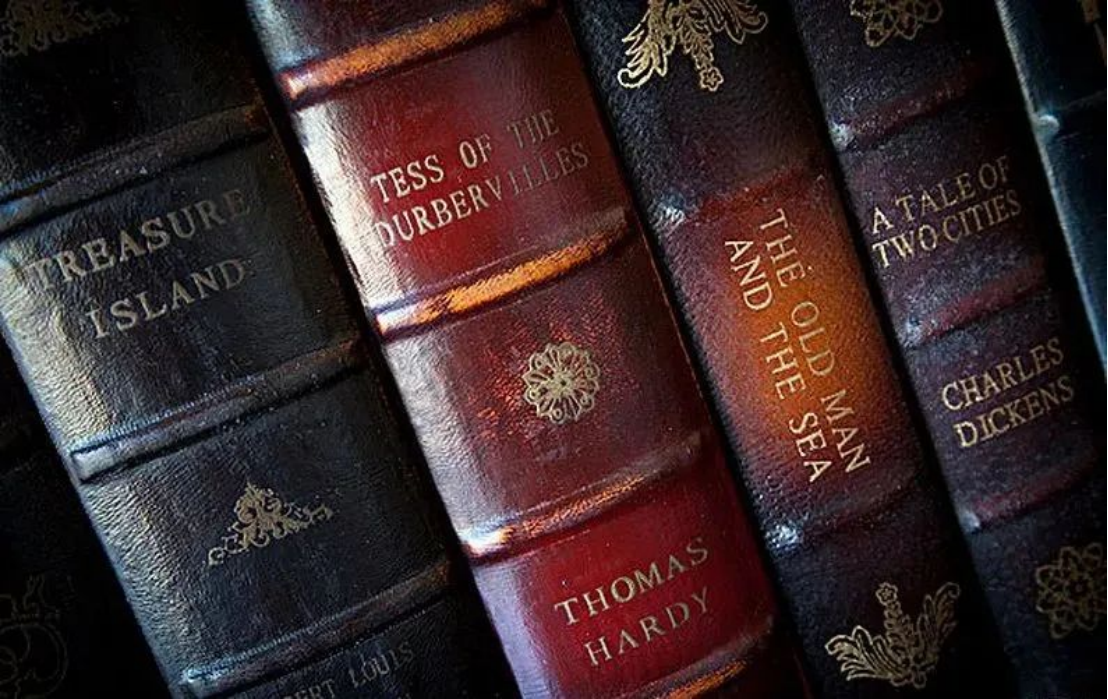
第四个方面是阅读史理论,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同样居功至伟。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指出,读者在解读作品方面拥有不受作者控制的自由。米歇尔·德赛都以“偷猎”比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作品的内容加以挪用。夏蒂埃则将阅读实践分解为文本、书籍、读者三个环节,对阅读理论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探讨。其他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也在阅读理论方面多有建树,提出了“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群体阅读理论”等学说。 第五个方面是新文化史,这一历史学研究趋势兴起于上世纪中叶。新文化史指出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注重对意义的阐释。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物质文化史与书籍史研究密切相关,在物质文化史视域下书籍的物质属性更加得以凸显,历史学家力图通过对作为物质实体的书籍的考察再现当时的社会文化。 第六个方面是来自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把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传、书写、印刷和电子时代等几个阶段。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命题,强调媒介形式本身对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有重要影响。印刷文化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重点,印刷文化被认为具有线性、统一、重复、同质化、集中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提出印刷具有“固定性”,在欧洲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受到印刷文化研究的启发,人们反思写本的特性,推动了写本学的兴起。相对于印刷的固定性,写本时代的文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作为物质实体的写本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现场感。 书籍史理论和方法的几个来源各有侧重,共同塑造了今天书籍史研究的样貌。在书籍生产环节,新目录学和文本社会学提醒我们注意文本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在书籍接受环节,阅读理论提醒我们关注文本意义接受的复杂性。来自历史学领域的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促使我们把眼光投向书籍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广阔背景。媒介环境学向我们提示了书籍作为一种媒介的长期演变规律,从宏观角度为书籍史研究提供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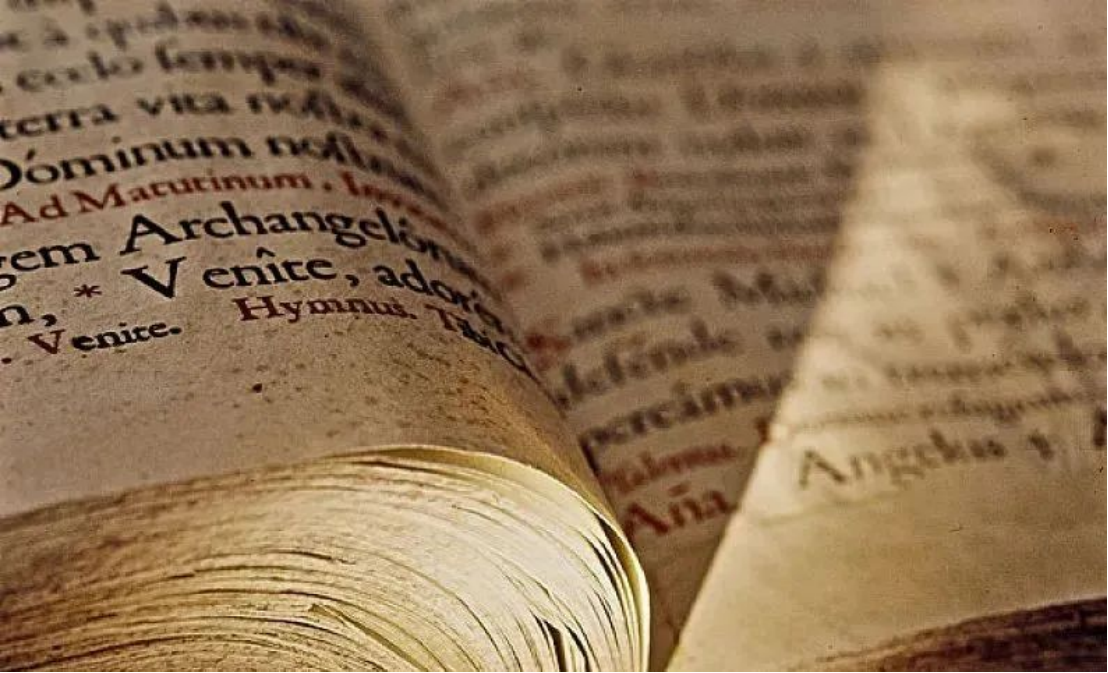
书籍史不同于以往的书籍研究 书籍史与以往书籍研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对书籍的认识来看,以往的研究比较注重书籍的文本层面,书籍史则强调物质实体层面;以往的研究大多把书籍看作知识的载体,实际上,书籍还可以充当宗教信仰符号、营利的商品,以及获取社会资本和权力的工具;以往的研究仅仅把书籍看作历史的记录者,书籍史则将书籍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看待。 从对书籍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的认识来看,书籍史强调这个过程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多元的;以往的研究聚焦于最终呈现的结果,书籍史则更注重对过程的追溯与分析。 从书籍研究的范式来看,书籍史在描述的基础上更注重采用来自多学科的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和阐释;书籍史打破就书论书的孤立视角和狭窄视域,强调把书籍纳入社会历史的宏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拓宽了书籍研究的视野;书籍史也更加注重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对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加以“深描”与精细化呈现,在更加丰富、立体的细节中探寻书籍的意义。 
书籍史的研究模型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个。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1982年提出了一个名为“交流圈”的研究模型,试图统合当时书籍史研究的各种理论。该模型以与书籍有关的人为中心,把书籍的生命周期分为创作、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关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对书籍的影响。两位英国学者托马斯·亚当斯、尼科拉斯·巴克对达恩顿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书籍史的研究模型应当以书籍,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并在图示中把影响书籍的各种环境因素从圈内移到圈外。加拿大学者莱丝莉·豪萨姆也提出过一个模型,该模型以历史学、文学、目录学为书籍史研究的三极,其中任意两级的结合可以催生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向,如目录学与历史学结合产生出版史,目录学与文学结合产生文本社会学,文学与历史学结合产生文化史、印刷文化研究,等等。“交流圈”及其变体是以印刷文化和西方经验为中心的,豪萨姆的模型则在解释书籍创作与阅读研究方面有些牵强。 “书籍之外”与“书籍之窗” 笔者在此以“交流圈”及其变体为基础,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模型。这个模型以书籍为主体,同时结合了人的因素,在书籍史研究中,书与人不可偏废。该模型分为三个部分:内圈、内圈标注与外圈。 内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其标注体现了参与到书籍生命周期中的人及其参与方式,外圈则是书籍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书籍的生命周期分为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这次第相接的五个阶段,从流传又回到创作,形成闭环。新增加一个从“接受”指向“创作”的箭头,因为流传环节适用于留存久远的书籍,而当代的书籍则不需经过流传阶段即可影响创作环节。每一个环节的标注旨在说明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并对应不同的参与者。如创作环节可分为撰作、汇编、注疏、评点等方式,分别对应作者、编者、注释诠解者和评论者等;生产环节可分为抄写、出版、印刷、装订等,分别对应抄写者、出版者、印刷者、装订者等;流通环节可分为颁赐、赠送、贩运、批发、零售等,分别对应颁赐者(君主和政府)、赠送者(贵族和文人)、贩运者、批发商、零售商等;接受(广义)环节可分为阅读、接受(文学史意义上)、评论等,分别对应读者、接受者、评论者等;流传环节可分为查禁、销毁、收藏等,分别对应查禁者、销毁者、藏书者等。 外部环境分为思想与文化、政治与法律、社会与经济三个方面,每个方面与书籍生命周期的关系,不同于以往模型的单箭头,而是使用双向箭头来表示,强调书籍不但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周遭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地统合东西方书籍史,并兼容印刷文化之外的书籍研究,这里主要强化了书籍史研究模型对写本文化研究的涵盖能力。 
笔者曾在所译《书史导论》前言中提出自己的书籍史定义:书籍史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定义与上述模型是相互吻合的。 书籍史研究的核心旨趣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书籍之外”,即跳出书籍看书籍。书籍史不仅仅是书籍自身的历史,也是书籍和周遭环境,尤其是与书籍有关的人与社会群体、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历史;二是“书籍之窗”,即透过书籍看历史。虽然以往历史学家也通过书籍看历史,但只是把书籍中的文本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书籍史则要透过书籍的物质实体及其形成、传播过程来观察、透视历史,丰富对历史的书写。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