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西底德的回憶——初讀《波羅奔尼撒戰爭史》(上)(2007022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55 万科周刊 林國華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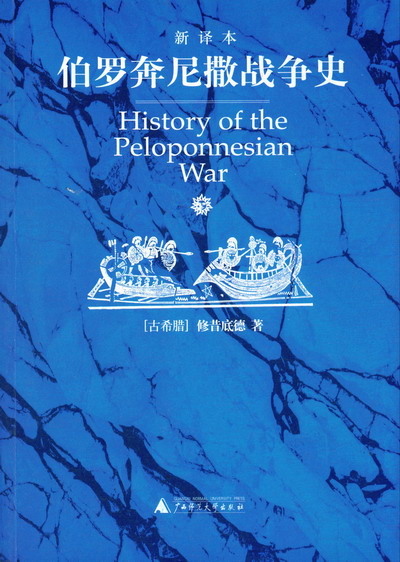 當帝國斜陽的時候﹐一種奇怪的哲學文體在羅馬城悄悄流行起來﹐人們把它叫做“安慰文”(consolatio)。哲學家們發明了這種文體﹐人們因此又把它叫做“哲學的安慰”。尼錄皇帝的老師塞涅卡曾經精通這種安慰的技藝﹐寫了很多這種文章﹐後來自殺了。那個混亂的年代消失以後﹐這種文體也就漸漸看不到了。也有一些零星書卷流傳了下來﹐比如鮑依修斯那部撫慰了很多人的名篇。據說他參加了古代那場最慘烈的文明衝突﹐在被殺害之後﹐人們把他叫做“最後的羅馬人”。在這之前八百年﹐在雅典﹐在同樣的夕陽下﹐一個叫修西底德的將軍在流亡的閒暇中用一種叫做“歷史”的文體寫下了他對那個混亂年代的回憶。據說﹐在那部書裡﹐人們找不到安慰﹐修西底德便難過地對他們說﹕“歷史”本是“記憶”的女兒﹐她不事安慰﹐她本身也是不慰的﹐因為她不知道來世的事情。 (1)雅典的瘟疫 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一場瘟疫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降臨。它通過地中海上的商旅悄悄流傳到了埃及﹑利比亞﹑波斯之西的愛奧尼亞﹐最後在前430年的春天到了雅典並驟然暴發。那時﹐雅典的宿敵斯巴達正兵臨雅典城下﹐舉世聞名的波羅奔尼撒戰爭剛剛進入第二個年頭。深受自然和人事的雙重窘迫﹐雅典的末日似乎要來了。很多人想起了斯巴達人在戰爭伊始從德而菲神廟求得的那個可怕的神諭﹕斯巴達人問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作戰﹐神回答說可以﹐並且說他將保祐他們﹐不管他們是否向神祈禱﹐勝利終將屬于斯巴達。雅典的老人們懮心如焚地說﹐雅典的覆亡是神已經註定了的。 那場瘟疫很可怕。斯巴達的圍城士兵發現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無數的新墳﹐詫異之下詢問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在城內肆虐。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命令馬上撤兵﹐波羅奔尼撒戰爭暫告停止﹐被死亡籠罩的雅典城更加顯得孤單無助。 城里死了很多很多人﹐連雅典的“第一公民”﹑民主領袖伯利克裡也未幸免于難。然而﹐有一個人奇跡般的活了下來﹐他後來用筆把記憶中的這場滅頂瘟疫寫下來﹐傳給了后人。這個人就是後來率軍遠征安菲古城的雅典將軍修西底德。 在修西底德的筆觸中﹐我們至今仍然能感受到他對雅典瘟疫的痛苦和冷峻的回憶。感謝他的回憶﹐我們也才有了那一段歷史。修西底德難過地回憶說﹐在那場瘟疫裡﹐醫生們束手無策﹐因為他們不知道瘟疫的來源﹐不知道醫治的辦法。醫生們大批地死去﹐因為他們和病人接觸最多。雅典城曾經一度雲集的哲人﹑學人﹑詩人﹑藝人一下子都看不見了。在瘟疫中﹐所有人類的知識﹑雄辯﹑技藝﹑聰明﹑謀略一概都沒有用處。連“宗教”這人類所能臻至的最高技藝也不例外﹕看到被病痛所苦的親人們在祈禱中相繼死去的時候﹐人們便拋棄了神﹐決心沒有信仰地等待死亡。而深諳世事的哲人蘇格拉底早早終止了對話﹐退出廣場﹐搖身一變﹐混進了雅典國民軍隊﹐終得以活過瘟疫﹔據說後來他當了逃兵﹐才又活過了那場更加可怕的波羅奔尼撒戰爭。 根據修西底德的回憶﹐瘟疫的第一個症狀是頭部發燒﹐既而眼睛變紅﹐發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難﹔干咳﹐嗓子變啞﹔胸部疼痛﹐後延至腹部﹐導致嘔吐﹔全身抽筋﹔皮膚呈紅色和土色﹐並有膿瘡和潰爛﹔體外低熱﹐但是體內高熱﹐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體浸泡冷水中﹔發病七天之後﹐體內高熱導致腑臟潰爛﹐病人開始死亡。垂死者的身體互相堆積起來﹐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滾﹐或者擁擠于泉水週圍﹐因為他們的口干渴。 死亡的慘狀幾乎使修西底德沒有勇氣繼續寫下去。他悲傷地說﹕“這場瘟疫不是人類的文字所能描述的。”我能想見他擲筆長嘆的樣子。修西底德一度避而不提那死去的和將要死去的人類﹐而是轉身竟去記錄死人屍體旁的野獸﹕“吃人肉的鳥獸一旦嘗了屍體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鳥類因此在雅典絕跡。”修西底德後來提到了三種野獸﹕狗﹑羊﹑蒼蠅。他說﹕ “狗提供了觀察疫情的最好機會﹐因為它們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由于看護病人而染病的人象羊群一樣成群死去”﹔ “在炎熱的初夏﹐流動在城里的鄉下人擁擠在空氣不流通的茅屋裡﹐他們象蒼蠅一樣地死去”。 修西底德似乎在絕望地暗示﹐他不能通過文字﹐而只能通過野獸來認識這場瘟疫。文字是出于人類的技藝﹐它代表著文明。然而在這裡﹐我們看到﹐與文字隱隱對峙的是狗﹑羊﹑蒼蠅。修西底德默默地告誡后人﹕文字是屬人的﹐它無法去摹寫那非人的事情﹔正如文明是脆弱的﹐它不能阻止人類在極限情境中再度野蠻。 人的再度野蠻意味著人不再是人﹑人的野蠻化。在對雅典城里的野獸的回憶中﹐修西底德暗示了瘟疫是怎樣使人不再是人的。然而﹐這只是身體意義上的非人化﹑野蠻化。讓修西底德更為沉痛的是雅典人的靈魂的野蠻化。他看到﹐瘟疫消滅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體﹐它更摧殘了雅典人的靈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處的脆弱﹑自私﹑和邪惡乘機復出。修西第德這樣回憶道﹕ “人們害怕去看護病人﹐病人由于無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為無人照顧的緣故﹐許多人全家都死光了。由于瘟疫的緣故﹐雅典開始有了空前的違法亂紀。人們看見幸運女神是這樣的變幻莫測﹐富人們突然死亡﹐而他們的財富卻落在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手裡。因此﹐雅典人現在公開地挺而走險﹐大行放縱之事。在過去﹐這種行為人們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隱蔽起來的。人們決定迅速揮霍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樂﹐因為金錢和生命都同樣是那麼短暫。至于榮譽﹐沒有人遵守它的規則﹐因為能不能活到享受光榮的名號的將來是很有問題的。人們相信﹐好的東西只是那些暫時的快樂和一切使人能夠得到這種快樂的東西。對神法的畏懼和對人法的服從不再有了。關於神明﹐人們認為敬不敬神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目睹了好人和壞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為的律法﹐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料到他能活到受審判和處罰的日子。每個人反而覺得﹐瘟疫已經向他們宣佈了一個更為沉重的判決。他們想﹐在這個判決執行之前﹐尋覓一些人生的快樂﹐這是他們的權利﹐它是自然的﹑正當的。” 死亡面前的“平等”﹗從死亡裡誕生的“權利”﹗我想﹐後世的大哲人霍布斯在構思其威風凜凜的“利維坦”從而為現代政治思考立下一塊冰冷的基石的時候﹐他必在修西底德痛苦的瘟疫回憶中找到了魔鬼般的靈感。然而﹐對于霍布斯﹐現代世界的瘟疫又是什麼呢﹖ 在滲透著末世死亡氣息的“平等”和“權利”的呻吟聲中﹐修西底德記下的是雅典人對人法和神法的遺忘和蔑視。我們知道﹐使人成為人的正是人法和神法﹕前者保證了人的政治本性(梭倫﹑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而後者則把人從獸群裡分離出來﹐放到高處(荷馬﹑荷西俄德﹑伊思庫羅斯)。修西底德說﹕ “這場災難有如此壓倒的力量﹐人們陷于絕望中﹐對人法和神法不再關心。昔日遵守的喪葬儀式不再遵守了。許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為他們已經埋葬了很多死去的親人。因此﹐他們採取了最可恥的方式來對待新逝的親人。他們跑到別人已經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們的死去的親人拋在上面﹐然後點火焚燒。或者﹐他們發現另一個火葬堆正在燃燒的時候﹐就把他們的親人扔在別人的屍體上﹐然後匆匆跑開。” 在對雅典人可恥的葬禮的回憶中﹐我們看到﹐在希望終結的地方不再有虔敬﹔而虔敬終結的時刻也就是人再度野蠻的時刻了。 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什麼東西最能深刻地表明人之為人的“人性”﹐那麼那個東西就是詩人荷馬曾經用以結束其特洛伊戰爭敘事的東西﹕葬禮 。葬禮定義了人世的最後邊界﹕神是不死的﹔獸雖必死但卻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這是一個藏在荷馬史詩中的古老訊息﹐它在後來以虔敬和正義而聞世的羅馬人的拉丁語言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人”(humanus)和“黃土”(humus)﹑“掩埋”(humare)﹑以及“該埋的”(humandus)共屬同一個字源 。在人世的黃土地上﹐如果人法刻下的是“正義”﹐神法刻下的是“虔敬”﹐那麼﹐那些忘記了人法和神法的人已然走進了瘟疫的暗影裡﹔縱然在身體上他還活著﹐但他的靈魂已經死去。 就這樣﹐修西底德的回憶告訴我們﹐有一種比摧殘身體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殘靈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種比身體性的野蠻更可恥的野蠻﹐那就是靈魂的野蠻。靈魂的野蠻﹐這對人法和神法的蔑視﹐深植于人的靈魂的深處﹐它對文明的人世構成永恆的挑戰。然而﹐總會有一些人在療救被瘟疫所摧殘的身體﹐那就是醫生﹔也總會有些人在療救被野蠻化的靈魂﹐那就是政治家(politicus) 。在人法和神法織就的“羅網”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這就是政治家的技藝和使命(柏拉圖)。 雅典政治領袖伯利克裡在其生前最後一次演說中重申了政治家的使命。當時﹐瘟疫退去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硝煙又起。活下來的雅典人不得不面對戰爭。哲人們又出沒在廣場上﹐傳播著古怪危險的生活教條。而大病初愈的雅典人心灰意懶﹑無心戀戰﹐民主政體的所有缺陷和醜陋都暴露了出來。雅典海軍大將特米斯托克利創下的帝國文明基業在伯利克裡手中岌岌可危。在他最後這次演說中﹐伯利克裡象多年以後尼西阿斯在敘拉古城下面對潰敗如喪家犬的雅典遠征軍所發表的最後一次演講一樣﹐要求雅典人與神和解﹑與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帝國的莊嚴﹕ “雅典人﹗我現在和過去一樣﹐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你們。我知道你們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認為﹐你們這樣做是不正義的。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個人在國家順利前進時所得到的利益比個人得到滿足而國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時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一個人在私生活中無論怎樣富裕﹐如果他的國家被破壞了的話﹐他也一定會被卷入普遍的毀滅中﹔但是只要國家安全﹐個人有更多的機會從其不幸的私生活中恢復過來。如果一個人有選擇的自由﹐能夠安靜地生活下去的話﹐那麼﹐進行戰爭是絕對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選擇,不是在屈服中成為奴隸就是冒險以求生存的話﹐那麼﹐我寧願選擇冒險而不是屈服。你們應當維持雅典帝國的莊嚴。如果你們不同時擔當起帝國的責任﹐你們就不能再享受帝國的特權了。你們不要以為我們戰爭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問題﹔戰爭還牽涉到帝國的喪失以及管理這個帝國所引起的仇恨與危險。在突然的恐慌中﹐儘管有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認為放棄這個帝國是一件好的和高尚的事情﹐但問題是﹐你們已經不可能放棄這個帝國了。事實上﹐你們是依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所以﹐昔日取得這個帝國或許是錯誤的﹐但現在放棄這個帝國則是危險的。主張放棄帝國﹐並且蠱惑公民們採納他們的主張的人﹐很快將葬送這個帝國﹔他們自己可以孤獨地活著﹐但是﹐如果帝國沒有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就沒有了﹐雅典也就沒有了﹐雅典人也就沒有了。雅典人﹗你們不該悲傷﹐不該怨天尤人﹐不該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動家牽著鼻子走進歧途。這些人比剛剛過去的瘟疫還可怕。瘟疫奪走的只是我們雅典公民的身體﹐但這些人將毀掉我們的公民德性﹐從而使雅典文明趨于真正的滅亡。這些人表面上生活在孤獨和自足之中﹐但其實他們的生存完全建立在雅典公民對城邦的的保護之上。在一個被敵人控制的城邦裡﹐這些人可以安穩的做奴隸﹐但在管理著一個帝國文明的雅典﹐這些人只是毫無用處的寄生蟲。雅典人﹗馴順地接受神明賜予的災難﹐勇敢地抵抗敵人﹗這是雅典人的古老習慣和德性﹐它是正義的。無論對城邦還是對個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記住﹐你們是一個偉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後的第二年(前329)﹐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裡與世長辭。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再度舉兵﹐橫穿科林斯地狹﹐進犯雅典郊野阿提卡。而雅典城群龍無首﹐個人野心瀰漫朝野﹐兩百年前大立法者梭倫創立的民主政體似乎蛻變成了最糟糕的政體形態﹕亂民之治。整個國家陷入在修西底德看來比“外侮”更可恥的“內爭”之中。“內爭”﹐這被所有經典政治思想家視為政治共同體的痼疾的東西﹐在十六世紀被“胡革諾”宗派內戰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的大法學家博丹(Jean Bodin)眼裡正是國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2) 瘟疫前的日子﹕帝國考古 來自非洲的瘟疫終于在雅典平息下去了。修西底德繼續把他的歷史寫了下去。可以明顯感到﹐他的筆觸突然變的象悲劇詩人那樣多少有些愴然。瘟疫改變了雅典﹐被改變了的雅典又改變了修西底德的記憶。 瘟疫爆發之前﹐帝國初創﹐雅典的繁榮和強盛使得同樣懷有帝國野心的科林斯人嫉妒的尖叫。對于那個黃金時代的雅典﹐修西底德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回憶。為了記錄這份回憶﹐修西底德採用了極端寧靜的筆法﹐一種連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學究都無可挑剔的筆法﹕考古。後來﹐近代有些好事者就是根據這種極端“客觀”的史實敘述而在修西底德的頭上加了一頂頗有派頭的桂冠﹕歷史“科學”之父 。在這項從容不迫的考古中﹐修西底德回憶了在希臘波斯戰爭末年﹐雅典把來自入侵希臘世界的波斯帝國的“外侮”轉化為有利的條件﹐從而在與近鄰斯巴達的“內爭”中取得勝利﹐既而在征服了二十余座城邦後﹐終于成了大半個希臘世界的主人。只是在對帝國的創建者特米斯托克利的回憶中﹐修西底德的筆鋒似乎隱隱有些顫動。修西底德回憶說﹕特米斯托克利深知﹐如果雅典想成為一個帝國的話﹐必須首先把它變成一個海上的民族。對此﹐修西底德一度中斷敘述﹐嘆到﹕“真的﹐他是第一個敢于對雅典人說﹐他們的將來是在大海上的﹗”後來﹐修西底德讓特米斯托克利這個忠告一再回響在雅典後世的政治家的記憶和言說中﹐直到雅典海軍在西西裡島全軍覆沒。雅典民眾後來放逐了帝國國父特米斯托克利﹐修西底德平靜但入微地回憶了這位偉人不應得的命運。與修西底德的平靜相對﹐後來的柏拉圖曾借蘇格拉底之口大罵雅典民眾“忘恩負義” 。身為政治家的修西底德之所以冷然不動或許是因為他深知那些飽嘗民主甜頭的雅典人並非“忘恩負義”﹐而是他們太愛平等了﹔由于對平等過度的愛﹐他們懼怕偉大。正是在這愛與怕的激情中﹐雅典人才放逐了偉大的特米斯托克利﹐哪怕他是他們的恩人。與修西底德洞察城邦的“習俗正義”相對﹐柏拉圖也許在哲人的“自然正義”的神話裡浸淫得太久了。這與其說是一種神聖的瘋狂﹐不如說是一種少年式的愛慾。 特米斯托克利遠走異響﹐客死波斯。修西底德情不自禁﹐寫下了他的歷史開篇以來第一份悼念﹕ “真的﹐特米斯托克利向世人顯示了他是一個極富天才的人。他是超凡的。他比任何人都值得我們欽佩。對于那些當場必須解決而不容長時間討論的事情﹐他用不著事先研究或事後考慮﹐只憑借他的天賦智慧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在估計將來可能產生的結果時﹐他的預測永遠比任何人可靠。任何他熟悉的問題﹐他都可以完美地表述﹔對于他本行以外的問題﹐他也同樣可以提出很好的意見。他擁有一種驚人的力量﹐可以看透未來﹐看出其結果好壞的可能性。由于天才的力量和行動的迅速﹐他能夠在最恰當的時候做出最恰當的反應。這一點﹐遠非他人所能及。他是希臘世界最偉大的人。” “最偉大的人”死了。修西底德的悼念誘使我們推想﹐特米斯托克利之後的時代不再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修西底德含而不露﹐我們便無從證實這個推想的真偽。但是﹐有一點很清楚﹐悼念之後﹐修西底德的“帝國考古”嘎然而止。在這之後﹐在瘟疫和戰爭中﹐雅典的故事將成為一場悲劇。悲劇需要一種悲劇的筆法。從“考古”到“悲劇”﹐與其說修西底德確證了“史”和“詩”的古老親緣﹐不如說他震攝于日後雅典這座悲情城市﹐不免有些惶然了。 (3) 瘟疫後的日子﹕民主﹑德行﹑愛慾 雅典的悲劇始于波羅奔尼撒戰爭。戰爭伊始﹐斯巴達人從德爾菲神廟求得的那個神諭以及從有著“祭司國度”之稱的神秘埃及流傳過來的瘟疫給這場悲劇蒙上一層命運的影子。帝國基業的繼承人伯利克裡在瘟疫中適時地早死。他留給雅典人的三篇演說不久就成了被背叛的遺囑 。戰爭的日子很漫長﹐然而修西底德似乎暗暗遵從著悲劇家的“三一律” ﹐漫長的日子在他的筆下飛快地滑過。密提林的暴動﹑科西拉的革命﹑派羅斯的幸運﹑底裡安的敗勣﹑尼西阿斯條約﹑彌羅斯對話等如水一般一幕幕上演﹐轉眼間就到了戰爭的第十七個年頭﹐該是遠征西西裡的時候了﹐而伯利克裡此時謝世也有十五個春秋了。悲劇的高潮(peripeteia)也該到了﹐這次遠征將永遠改寫雅典人的命運。 西西裡遠征是特米斯托克利之後雅典帝國慾望的一次最高表達﹐它以失敗告終。發動遠征的雅典青年將軍亞西比德稟有特米斯托克利式的天賦﹑氣質和領袖魅力﹐為哲人蘇格拉底所愛戀。據說﹐遠征軍出發前夕﹐亞西比德在一次通宵酒會上聆聽了蘇格拉底借女先知狄娥提瑪之口所講述的關於愛慾的悲喜劇的故事 。酒醒之後﹐亞西比德沖入大海﹐愛慾勃勃地踏上了遠征的路。 這次注定失敗的遠征因此將成為一場愛欲的悲劇。喜劇的缺場使得愛欲的生活似乎殘掉了一半。後世的柏拉圖思考良久﹐得出了答案﹕愛欲在人世裡注定是場悲劇﹐因為神早已隱退了(柏拉圖﹕法律篇)。看來﹐柏拉圖只不過重複了老邁的荷馬 。再後來﹐通過對雅典城的建造者特修斯的身世考古﹐普魯塔克以史家身份表述了同樣的發現﹐並進一步得出了一個頗為聳人的結論﹕雅典的存在是有違神法的(普魯塔克﹕特修斯傳)。和大多數對人類言語深懷狐疑的史家一樣﹐普魯塔克沒有多說什麼﹐但他的深意不難尋索﹕雅典是座“太人性”的城邦﹐它太信賴人的智慧﹑言語﹑技藝﹑德性和韜略﹐以至于屢屢僭越自然的限度﹐並蔑視喜怒無常的幸運女神 。普魯塔克的考古多少令人回想起虔敬的斯巴達人得到的那個預言了雅典滅亡的神諭。修西底德遺憾地說﹐對于那個神諭﹐只有一些雅典的老人才感到懮心如忡忡。 年輕的亞西比德在出征前的辯論中發表了一篇演說﹐言語中過渡的愛慾似乎並沒有驚聳修西底德的敘述。在這篇演說中﹐亞西比德雖是初露鋒芒﹐但已經鋒芒畢露﹕ “雅典人﹐我比別人更有權利做你們的將軍﹐我無愧于這個職務。一個人自視很高﹐而不把別人放在和他平等的地位上﹐這是正義的。因為當一個人窮困的時候﹐不也是沒有人來和他共患難嗎﹖我們失敗的時候﹐又有誰曾經關切過我們﹖根據同樣的原則﹐如果有人被成功者所鄙視﹐他應該學會忍耐。在一個人以平等的地位對待每一個人之前﹐他是不能要求別人以平等的地位對待自己的。我知道這類人﹐這是一類在所有方面都一枝獨秀的人。然而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卻不得人心﹐他們的平輩人尤其認不出他的偉大﹐儘管偉大就在這些人眼前。但是﹐你們會發現﹐到了後世﹐等到他死了很久以後﹐就是和他毫無關係的人也自稱是他的親戚﹔你們會發現他的國家不再把他當成一個外人或名譽不好的人﹐而是自豪地把他當成偉大的同胞。這就是我的志嚮﹗正是因為這個志嚮﹐我的私生活受到你們的指責﹐但問題在于﹐你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在處理國事上勝過我的﹖關於這次遠征﹐這就是我的意見﹕沒有誰﹐也沒有合理的論據﹐能夠證明我們不應該去援助我們在西西裡的同盟國。我們必須援助﹐必須派出遠征軍。勇敢地援助一切請求援助的人﹐不管他們是希臘人﹐還是非希臘人。這就是我們雅典取得帝國的技藝﹐這也是所有帝國的技藝。如果我們不肯行動﹐或者在援助的時候有種族的區別﹐那麼﹐我們根本不可能擴張我們的帝國﹐甚至完全葬送我們既有的帝國。一個人不但要在受敵人攻擊的時候抵抗佔優勢的強國﹐以捍衛他自己﹔而且還要首先採取手段﹐把敵人的進犯消滅于搖籃中。雅典人﹐你們應該記住﹐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就是我們不得不不停地謀劃新的征服﹐為的是保持住我們已經所擁有的。因為﹐如果別人不是在我們的統治下﹐我們自己則有陷入被別人的統治的危險。你們對于安寧生活的意見不應該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是帝國的子民﹐除非你們改變你們的生活方式而去採用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方式﹐那就是被奴役。另外﹐你們也要記住﹐城邦也是和其他任何東西一樣﹐如果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它各方面的技藝和德性會變得陳舊不堪﹐它自身也必然會萎縮死亡﹔但是在戰鬥中﹐它會經常取得新的經驗﹐更慣於以行動而不是言辭來保衛自己。一句話﹐我認為一個本性是變動不居的城邦﹐如果改變它的性質而使得它處于閑散狀態的話﹐它會很快滅亡。人們所能擁有的最安全的選擇就是接受他們已經有了的性格和制度﹐儘可能按照這種性格和制度生活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