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列文森奖《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书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1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以下内容转自雅理读书(yalipub)公众号 
编者按:2018年1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公布了倍受学界瞩目的是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s)获奖名单。该奖项为纪念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由梅林基金会(Merlin Foundation)设立,每年奖励两部中国研究领域杰出的英文学术著作。今年获得列文森奖的作品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教授的《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今日推送作品为本书的书评,原载China and Comparative Studies第11期,作者为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郭威廷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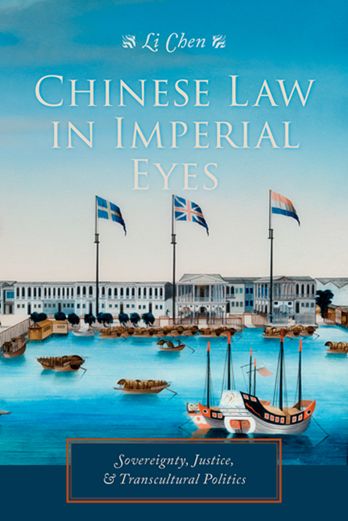
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6. 陈利:《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16年 作者简介:陈利,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ISCLH)创始会长(2014-2017)及现任理事、Law and History Review 编委。主要研究法律、政治及文化三者的交叉关系,涉及明代以来中国法律文化史、中西比较法研究、中外关系及近代国际法史、帝国与后殖民研究。出版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2016)。 过去三、四十年,学界对于帝制中国法的运作实况不断推出新的方法和观点。一个始终引人注目的老问题是:帝制中国法到底是否欠缺所谓的"理性"面向?其是否仅仅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产品?相对于近代西方法,中国法是否显得"停滞"或者"落后"?显然,环绕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关怀帝制中国法的运作本身,其同时也关注帝制中国法在比较视野中的定位。不少研究尤其关注中国法如何在明清时期发展和转变其内部运作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关联。相异于较早的静态与结构性研究,学者已不再满足过去动辄以西方概念、或过于专注抽象和规范性的探究模式。从一个较为宽广的学术范畴来看,近年的研究益加关注两种旨趣相异、却又相互联系的面向:一个是基层的法律实践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中国法,另一个则是中西话语与相互建构中的中国法。尽管不同的学者各自以其相异的学科背景探讨相似的议题,这两种研究方向已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帝制中国法在比较视野中的重新理解。前者通过特定范围的区域和时期,探讨个别制度实践和同时期其他国家或区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其探讨的范畴,包括从契约、公司、家族、土地秩序、和民事审判等,到法律知识、法律社群、以及司法程序转变等各种面向。后一种取径则关注中国法律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被理解、曲解、重构、甚至进一步影响双方的互动与各自的政治及法律运作。其关注的面向,包括中西双方互相观看和理解对方的法律、刑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和观念;或者,通过双方的交流和冲突,理解其如何交涉、妥协、并进一步协调关于法律纷争上的处理方式。不管是哪一类的学术范畴,学者通过平面的制度脉络以及纵向地历史化(historicize)中国法律转型的方法,重新探讨法律在历史以及社会中的作用。与其它新近的中国史领域相近,新取径影响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除了扩展宏观、与微观的各种考察,也逐渐关注不同文化与历史接触中的比较(comparison)和联系(connection)。通过这些学术成果,人们有了新的观看帝制中国法律动态发展的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视角让人们将原先的老问题转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到底,中国的法律发展是否和西方如此不同?如果是,此种"“中国特色"是在甚么样的脉络下产生?我们该如何通过"“中国特色"的生产和制作理解更宏观和长期的中国史发展?不同世界的人们又是如何因应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各种相互理解、误解、冲突,乃至进一步塑造对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各种想象? 陈利的新作《帝国之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便是在这样多重的学术脉络中发展出来。师承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陈利的治学也有和业师相似之处──一方面,关注18至19世纪中外的法律比较;另一方面,也关注司法程序的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等议题。事实上,如同前面所述的两类取径,陈利的研究旨趣不仅包含中西交流中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涵盖中国法律实践内部司法人员、法律推理、以及法律知识等议题(例如其关于幕友及秋审等研究)。在这本修改自博士论文的新作当中,陈利更展现出其对国际关系与中外政治的研究关怀。更重要的是,本书大量运用中国和英国双边的档案史料,不仅成功结合了中国法律史与清代外交史的既有研究,同时开拓了探究这两个领域的全新模式。 本书谈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帝制中国法的形象以及相关论述如何以及为何在近代西方的知识系谱中被建构出来。在此之前,新近的论著已在不同层面上探索中西法律交流中的知识建构。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律》(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卜正民(Timothy Brook)、巩涛(Jerôme Bourgon)、与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 )合着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以及柯塞北(Pär Kristoffer Cassel)的《审判的根据:十九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治外法权与帝国权力》(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如同其他探讨近代中西交流和帝国碰撞(clash of empires)的著作,这些研究超越过去强调单向冲击的取径,并将中国法形象的建构放在双边各自的历史与话语脉络中──例如,中国知识菁英与改革论者的「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以及西方国家以此合理化其对中国治外法权与外交交涉的各种要求。新的取径成为作者立论的重要资源,并成为作者用以批判过度简化的文化论、冲突论、和本质论的有力依据。时至今日,尽管学者已经批判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建立的「冲击-响应」模式,并反思费氏等人将中西冲突归咎于清政府无法有效面对"“文明化"挑战的论述,许多关于「文化差异」与「文化的不可共量性」(cultural incommensurability)的论述仍旧盛行于各种关于中西交流与冲突的解释当中。为此,作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此复杂的中西交流互动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并以其间关于中国法的论述建构作为考察的中心。一方面,作者引用刘禾(Lydia Liu)的著名宣称「文明之间不会相互碰撞,但是帝国会」(Civilizations do not clash, but empires do),认为中西的交流与冲突不能看作单纯的文明与文化的相遇,而是要通过「特定历史脉络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因素」来探究复杂的多样关系,并观察相互竞逐的政权如何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第6页)。另一方面,作者系统性地探索了西方关于中国法律形象建构的关键年代──1740年代至1840年代──,并探讨此时期中国和英国双边复杂的权力运作。通过对一系列中西交流与冲突的重大事件的爬梳,作者主张此时期西方世界建构的中国法论述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西关系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与国族边界在重构与协商上的重要场域。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此书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着重外交、思想、或文学层面上的研究,而是提供一种更为整合且具批判性的「档案上、大众层面上、思想智识上、和政治上」的中西遭遇与交流研究(第2页)。 
为了说明此种复杂多样的中西交流关系,作者引用蒲蕊特(Mary Louise Pratt)在其著名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跨文化过程》(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所提出的概念:「接触带」(contact zone)。在蒲蕊特的论述中,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相异文化相遇、冲突、竞争和缠斗的社会空间。蒲蕊特以此概念批判了传统强调"“优势"或"“从属"的权力不对等关系。其通过「跨文化过程」(transculturation)解释被殖民者如何巧妙发展混杂文化以及开创各种应对策略。这两组概念对于中西交流中的法律形象建构极具启发,但如陈利指出,在中西遭遇的场合里,这个概念必须经过适度的修正。首先,所谓的「文明的碰撞」与「文化的不可共量性」必须放在历史现象与论述建构的脉络中考察。它并不是预先给定的事实,而是通过接触带中文化代理人(cultural brokers)和跨帝国臣民(transimperial subjects)所不断协调、传述而产生。其次,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决定中西之间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持续占据了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了为何英国人和西方人在中西交流中始终缺乏安全感。这样的不安全感,最终也进一步形塑了中西双方在接触带中的相互关系。再者,过去对于中西冲突以及西方优势论的解释当中,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中西接触带的跨文化过程──亦即,欧洲国家也通过援引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观念,作为警示和参照对例来"“现代化"其自身社会(第8页)。另一方面,非西方社会的行动者,也并非总是被动接受殖民者或优势群体的文化,其本身也经常参与这种跨文化过程与"“东方主义"论述的建构。因此,作者指出,「跨文化过程」的概念需要视作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这不仅是用来挑战欧洲中心式的全球现代性叙事──比如关于被殖民者本身的「能动性」(agency)以及殖民政权底下的各个行动者──,同时也是理解欧洲国家自身、探究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来说,这是要将各种东方主义叙事建构「去中心化」(decentering),同时考察互动双方内部与相互间的多样化的帝国形成过程(various imperial formations)的方式。在此,作者引用德里克(Arif Dirlik)的「揭露迭层关系」(unfolding relationship)概念,指出对于中国法论述建构的研究,必须同时探讨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同行动者在不断转换的知识生产场域以及不断转变的权力平衡中的各种动态、偶发机遇、以及紧张关系。通过这样的理解,作者提出以「边界形成的迭层揭露过程」(unfolding process of boundary making)考察各种对文化差异和认同的建构。其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接触带」不仅是实体上、社会上的空间,同时也该视作中西之间观念、语言、认知、以及情绪上的文化与论述空间(第10—11页)。唯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出现在帝国与国际法逐渐从疆域上的主权演变为治外法权的一系列过程──尤其是关于甚么才是个别行动者所期待与彰显其主权(sovereignty)的行为与复杂交流当中(第12—13页)。 
更重要的是,作者选择以法律(包括国际法)作为研究对象,让我们更能理解法律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角色。过去的研究注意到西方法律论述如何被用来正当化欧洲国家海外扩张、又和基督教普世价值以及亚洲国家主权建构相互竞逐。这些法律论述不仅授予殖民者扩张的权力,同时也赋予远渡重洋的西方人法律上的保障。法律作为主权和意识形态的延伸,对18至19世纪的中国同样适用。更重要的是,法律不仅用于外交谈判和司法交涉,同时也是殖民国家用以维系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在中西法律的交流过程中,尽管中国并未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法律往往被用来建构双方文化和权力的等级关系,同时用来维系各种文化、社会、和种族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建构其普世价值和平等权利的论述时,也通过对中国法形象的建构来支撑其治外法权的主张和排除中国适用国际法等论述。通过对这些法律论述的建构与其背后的文化与权力分析,作者指出此书的研究提供了「法律的帝国形成过程」(the imperial formation of law)与「帝国的法律形成过程」(the legal formation of empire)的重要范例(第16页)。 第一章以1784年休斯女士号案(Lady Hughes case)及其后续之发展为中心,探讨中国法形象的表述如何在西方治外法权的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及帝国档案(imperial archives)发挥作用。1784年,停靠于黄埔的英国休斯女士号因鸣放礼炮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英方交出炮手,最终依中国法将炮手绞刑处死。多数的观点认为英国炮手仅系意外或过失杀人误杀,而忽略此案和相互竞逐的帝国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此,作者提出强而有力的批判,并爬梳多种过去尚未系统研究的档案史料,包括东印度公司地方代表给董事会的报告、董事会的回复、中西多方自1680年代至1840年代的其他法律纷争文件、以及19世纪以降西方汉学家与政府部门所作出的各种关于中西法律纷争的解释和评论。作者主张,不论是依照当时的中国法还是英国法,炮手的行为都难以认定为意外杀人。此种行为在双方法律系统里都难逃死罪,尤其在使用枪炮早受禁止、出事船只并排停泊且非处偏僻无人处、且休斯女士号已知中国船只在射程范围仍然开炮的情况底下(第35—37、44—45页)。有意思的是,早在本案发生前,西方国家就已长期惯称外国人杀死中国人的行为皆为"“意外"。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造成外国人死伤者,西方国家则大多认定其为蓄意谋杀(第37—38页)。对此,作者认为西方制作大量关于”“意外致死”的论述,并非仅是出于其对中国法本质和运作的无知了解,而更多地来自于西方国家在获得治外法权建立之以前,一方面既要原则上尊重中国法律和主权,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期望逃避免于中国法律制裁的种族优势和矛盾心态(第39—41页)。而在中国方面,清朝政府亦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在皇帝和地方官员巡抚不同利害关系的考虑中各自盘算下引导全案的走向。深陷于朝廷和西方的压力,广东巡抚孙士毅既要捍卫清朝审判权限、又要朝廷怀柔处置;而面对北方叛乱和与日俱增的外国势力,乾隆皇帝既要求地方官员要斥责严防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制造动荡官员,又不得不仰赖广东官员维系既有的通商模式和防患法律主权上的争端(第46—58页)。另一方面,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同样严斥身处广州的地方代表,认为其报告错误百出且自相矛盾,不仅有损英方形象,甚至造成可能的贸易损失。此案之后,英方对于船长与船只都有更多规范,包括废除礼炮以及要求船长对于水手危害公司贸易的失当行为应负连带责任(第59—61页)。综合言之,休斯女士号案不仅凸显了中英交流中"“管辖权政治"(jurisdictional politics)的多方运作,同时也成为日后西方国家主张建构治外法权的重要理由源头。一方面,多数的西方观点持续不断地将中国司法程序塑造为"“负面的他者"(negative other),尽管英国法对于命案的制裁几乎与中国法同样严厉。另一方面,在中西交流的实践上,西方国家也竭力创造作者所称的"“法律边区"(legal limbo);此种边区,使得在中国境内犯法的西方人,往往既能免于中国法裁判,也能免受其本国法的严厉制裁(第42、46页)。 第二章分析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翻译《大清律例》的背景和影响。过去的研究着重小斯当东在中英关系中的角色,包括其跟随父亲参与马戛尔尼使团谒见乾隆、其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经手中英法律案件、其参与阿美士德使团与中国再行交涉、以及其出任国会议员对于英国对中政策的制定与辩论等。然而,对于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背景,以及其翻译对于西方世界理解中国的深远影响,却少有人深入探究。此章的分析可谓填补了这片空白。作者一开始分析西方国家掌握中国语言的困境。自16世纪起,尽管欧洲国家体认到语言与教育的政治意义,通过传教士、贸易商、以及外交官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一直显得力不从心。到了18世纪时,清政府的「广州体系」更进一步强化对外国贸易的掌控。外商文件需通过官方核可的翻译才能通过行商上交政府。而私自学习中文或寻找未经核可的翻译更要面临严厉的处罚。一直到小斯当东的翻译之前,英国贸易商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不论是官方核可抑或是是私下经营的翻译均难以准确表达外商想要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为了处理法律纷争,英商不得不寻求其他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的协助,或通过间接翻译了解中文文件的原意(第71—78页)。在这样的困境下,小斯当东的出现为使得英国的外交和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获得了及时的协助。1800年起,小斯当东再次来到中国,并协助东印度公司处理多起法律纠纷。尤其在1800年的天佑号案(Providence case)中,小斯当东的翻译不仅让东印度公司顺利进行协调,还使英国官员首度获得参与审判机会,并以中文诘问证人且在程序进行中对审案清朝与官员施压官府人员沟通,最后使得此案不了了之,而该凶杀案中的英国被告也免于受罚(第79—83页)。更重要的是,尽管朝廷严禁外国人取得图书、官报、以及律典,小斯当东仍然设法取得上千本的中文图书,并翻译《京报》中与英国利益相关的奏折与圣谕。小斯当东对于中国法律与政府运作的知识,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接下来的中英冲突案件中得以摆脱中方的控制。尤其在一件聚众斗殴并使用凶器杀人的海王星号案(Neptune case)中,小斯当东对律文的了解让英国得以《大清律例》条文据理主张,使几十名大量英国涉案人员免无需受中国监禁与刑责审判。此种"“以中国法维护英方利益"的操作,最终逼使中国官员以假报案情和大事化小之计销案了事。有趣的是,在小斯当东之后的《大清律例》翻译中,此案文书件被收入附加至附录中,让并西方读者据此更加强化了清朝司法制度专断官员腐败、英国水手自保的东方主义形象。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交涉,让英方更加坚信翻译中国法律有助于维护英国利益(第83—86页)。之后的十数年,小斯当东翻译出版《大清律例》。其翻译深受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影响,一方面为了解探索东方法律和社会创造知识,另一方面也出于英国外交的实务考虑。为了使欧洲读者易于了解,小斯当东的翻译包含了大量删节、改变律例的内容与结构。而在强调自己做为优秀汉学家已能跨越文化隔阂的同时,他这种预设西方概念和删节原文的作法,实际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欧洲东方主义的想象。尤其在标题的选择上,小斯当东除了保留了富有异国风情的音译标题("Ta Tsing Leu Lee"),还自行创造了副标题,尤其是放大字体的"“中国刑法典"(Penal Code of China)。此种翻译强化了欧洲人对中国"“原始"法律的想象。不但让此 往后的论著普遍出现了"“中国只有刑事法、没有民事法"的见解,更让不少学者深信中国法律仍未完成梅因(Sir Henry Summer Maine)所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化过程(第91—99页)。更重要的是,小斯当东多次强调《大清律例》为理解中国法律与政府运作的唯一权威文本。此种强调单一文本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作法,在其强调律例作为理解中国整体法律、知识、以及国民性格的解读下,更加强化了帝制中国落后和静止不变的"“前现代"印象(第104—108页)。综合言之,作者认为小斯当东的翻译不仅仅是中英双方帝国形成的重要产物,同时更要放在全球脉络的帝国知识生产下考察(第108—111页)。这尤其和欧洲内部所形成的关于中国法律的知识相关,且与下一章要讨论的欧洲法律改革紧密联系。 
第三章谈讨小斯当东之前的多种观看中国法的方式,以及《大清律例》翻译出版后,欧洲国家兴起的新一波中国法讨论,和与此相关的现代性论述和法律改革。自十八世纪起,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法有非常多不同的论述。其中,孟德斯鸠对于中国法的描述,强化了各种关于" “东方专制主义"的想象。孟德斯鸠的分析将中国政体描绘为仅凭君主个人意志、不受任何基础法限制的法律系统。这样的描绘无可避免遭遇挑战,尤其在如何理解中国高度发展的法典和刑罚体系上。但是,孟德斯鸠一方面认为中国法律仅是统治者高压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承认了中国法的一些优点,包括具有预防犯罪功能,且依照精密的分析将不同行为以相应程度的刑罚处置(第115—121页)。跟孟德斯鸠同时和稍后的思想家,也分别提出各种对于中国法的理解。比如贝加利亚(Cesare Beccaria)虽然没直接援引中国, 却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孟德斯鸠受认为中国法启发而提倡的除了等比处置和刑法应着重于预防犯罪的这些现代法律的重要原则功能外,还发展出非常清楚且细致的法典;伏尔泰则指出中国法在死刑犯的审理上发展出极其复杂的多层级审查制度,且其高度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已经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简而言之,尽管许多思想家认为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专制且落后,但同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和传教士则又都认为中国已发展出开明、有效且具理性的法律体系(第121—127页)。这样的观点在小斯当东翻译出版《大清律例》后更为盛行,甚至不少人认为中国法远比欧洲法律先进、理性、且仁慈,其繁复的法典、统一而一致的结构、以及对犯罪行为与相应刑罚犯罪的精细等级分类等,均值得欧洲国家学习(第127—139页)。这样的特征正好反对照了映英国普通法体系久为诟病的零散法源、缺少统一法典、欠缺可预测性、以及刑罚判决过于严厉和主观等问题。在1811年左右的修法辩论中,不少议员和评论者都英国议会颁布的修法提示手册明确提到了刚建议参考甫才出版不久的《大清律例》英译本。一些提倡法律改革者在该手册除了批判英国现行法缺乏一致性以及刑罚过于严厉的同时外,同时指出应参照《大清律例》将英国普通法欠缺法典化,并引入 的英国法亦应纳入比例刑罚的规定以节制大量英国法官的恣意裁决。这场修法引来许多辩论,其中包括对法典化是否只适合像中国一样的“的"专制主义"国家特色的问题 及其"严厉控制人类全部行动"等的疑虑(第143—148页)。修法辩论的最终的修法结果并未将法典化带入英国,但法典化和法律现代化的运动却在英国殖民的印度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国家以传播以现代英国法制的名义取得了很大进展,颁布了包括著名的《印度刑法典》在内的一系列律典,并从而使英国法律制度能够在此后继续跻身于所谓世界上“伟大”的或者“现代 ”的法治体系之林"文明化" 的方式大力宣扬并纳入殖民地法律体制(第150—153页)。 第四章转向西方对中国法再现的情感层面,探讨西方观察者面对中国刑罚的影像与文字记录时,如何将"“感性的自由主义"(sentimental liberalism)转化为"“感性的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并进一步形塑关于中国法律的情感社群(emotional community)。西方的"“感性文化"(sentimental culture)与其自由主义传统紧密联系。不少启蒙思想家均强调同情与理解他人的痛苦。此种感性文化延伸至中西交流,并与西方对中国社会的想象、以及自身文化认同的界定密切相关。作者先以梅森(George Henry Mason)编着《中国的刑罚》(The Punishments of China)为个案,分析中国刑罚形象如何通过中国画家与西方收集者的想象与交流而呈现于编者所收集的中国水彩画中。不难想象,在这样相互揣摩的过程中,该书所收集的水彩画呈现出极具异国情调(exotic)和怖栗(horror)的中国刑罚景象(第164—169页)。此种曲解与误解自然混淆了中国刑罚(punishment)与酷刑(torture)的差异,但作者进一步指出此书图像凸显了感性(sentiment)对于西方想象、同情、以及将中国建构为文化差异他者的重要作用(第169—170页)。在此之后,19世纪广为流传的报纸与报导,也同样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观察,将中国死刑描绘为残忍野蛮的行为(第174—180页)。大量的游记、报导、照片、明信片、甚至旅游导览渲染着中国死刑充满奇异、惊悚、和超乎寻常的画面。而游历中国的西方旅行者,不仅难以抵抗亲临刑场目睹残暴的诱惑,还将此连结至人道关怀、以及"“情感社群"成员的道德责任和进行道德评判的资格。显然,如同作者指出,19世纪中的中国已被当作是一个"“残酷的剧场"(第184页)。而中国死刑的景观(spectacle)、甚至是中国官员刻意选择在西方商行门前船面前的处死鸦片死刑犯人执行,不仅对西方商人、水手、和外交官带来了创伤性的影响(cultural trauma),甚至时而造成西方水手暴动、扭打官员、以及激烈的抗争。这种将西方人拉进死刑执行景观的作法,最终造成西方群体在情感上更深的冲击,同时也在鸦片战前升高了西人对中国销烟行动的抵制(第192页)。就连在英方要求迅速处死中国嫌犯的案例中,中国官员仍被西方群体批为残酷不仁无道,而胁迫中方执行的英方官员则被赞为处置妥当(第193—195页)。通过这些案例,作者认为西方群体对于其所承受伤害(injury)的主张和论述──包括对生命、财产、条约权利、以及国族情感上的各种"“伤害"──,其对中西关系的影响实并不亚于西方其对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运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操作,西方"“感性的自由主义"得以加入"“理性的自由主义"而成为19至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中的重要一环(第197页)。 
最后一章探讨鸦片战争的法律层面。过去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着重鸦片经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free trade imperialism)、以及文化冲突等面向,但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也是一场"“关乎法律、帝国主权、以及文化界线的战争"(第203页)。早在18世纪中,清朝政府就已禁止非医疗用途鸦片的贩卖与传布。19世纪初清廷持续升高鸦片禁令的刑罚度。但是直到1830年代,当此情形持续恶化且贪污与走私日益猖獗时,朝廷内也开始出现如何管制鸦片的争论。而在1838年后,朝廷采取严厉取缔的政策,但在对中国烟犯除了执行更多和更快迅速的死刑仍然无法震摄住外国烟贩之后外,最终还在1839年从英商手中查扣了大量鸦片并大量销毁烟。面对清廷严厉的政策,英国内部产生了极多的辩论。除了既要坚守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又不愿承认中国享有对外国人司法管辖权外,这些辩论还涉及中西主权、以及中国鸦片泛滥的人道问题与合法性问题(第206—214页)。为了正当化其出征中国以及寻求赔偿的主张,英方还试图解释在中国境内视为非法走私的鸦片如何能被 合理视为外国人合法的财产(第214—222页)。而最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中国是否属于国际法体系一员秩序的问题,因为如果否认其国际法地位,西方国家将难以在理论上要求其负担违反国际法之责任。为此,包括小斯当东在内不少和律师出身的英国国会议员都曾提出修正观点。主张,其一方面应将中国视为"“半文明化"国家而且不能未能直接适用国际法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根据所谓(通过帝国主义)"“常理"(ordinary sense)的角度,坚持等认为中国有遵守国际法的义务,所以须要对其概念归责中国销毁鸦片之行为负责,并建立以国际条约的方式要求中国遵守条约义务(第225—238页)。 
本书立论详实、视角独具,且在档案史料上用力极深,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尤其其成功结合中西交流史与中国法律史研究,又能通过外交、法律、翻译、与感性层面深入解释中英冲突各个案件,为不同领域的结合开创了全新的典范。全书的分析环绕在中国法作为一种他者的想象如何在不同情境下接受多重建构、同时还能深刻影响中英关系。从较广的学术范畴来看,此书的研究更涉及法律与帝国、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通过"“接触带"的概念,作者探讨中英交流中双方相遇、缠斗的交织过程。其带领读者深入案件背后复杂的脉络,同时又能爬梳关键人物在个案进行过程中的复杂心态。若要鸡蛋里挑骨头、针对此书精湛的分析提出未来可能的探究方向,或许是关于此时期里中国法内部的复杂转变如何与中英关系乃至中国法形象的建构产生关联。如同作者所述,当18世纪末休斯女士号案爆发时,乾隆皇帝面对的不仅是中外之间的冲突,同时还有帝国内部的复杂动态。而与此同时,清朝法律也面临极多改革,包括皇帝对死刑、城市抗争、海盗、秘密结社、以及边疆叛乱的各种调整。乾隆皇帝本身的个人性格也相当鲜明,其对官僚与司法程序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究竟,乾隆个人对于司法程序与死刑执行,在中英交流中扮演何种角色?皇帝个人意志与法律制度的转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法律交流?在此之后,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清廷进一步延续省级司法程序的改革,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弹性的法律措施。此些改革,以及在此之前即已开始的大量死刑制定和即行正法扩张,对于中国法形象的塑造又造成了何种冲击?如果如作者所说,中国于中西交流中并非被动接受优势群体的政策与文化,那么,在这复杂过程中中国内部的动态与转变扮演了甚么角色?皇帝、地方官员、以及其他相牵涉的行动者,又对此带来何种影响? 或许,对于作者所称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到底为何,这样关键的法律互动发生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中?这个问题看似无需证明、甚至无庸置疑,毕竟这个时期是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国之间相互冲突的重要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从法律与帝国的互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文明化"与帝国主义发展来看,我们仍不禁要问到底为何所谓"传统帝国"在这个时期里"出了问题",最后除了因应内部的问题外,还得重新调整法律与制度以因应西方贸易和鸦片等问题。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18至19世纪考验着许多历史帝国相类似的问题。尽管类似的"普世法"、"文明化"、以及"正义之战"等议题早已于17世纪浮现,18世纪后半以降仍然凸显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由此观之,乾隆、嘉庆、道光等所进行的法律改革与内部转变,以及其与中西互动和背后复杂的全球历史趋势如何相关,或许是本书所开创的议题于未来可再进一步延伸探究之处。 <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