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5)巡抚与大儒的正面交锋|独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36 凤凰网历史 刘梦溪 参加讨论
【前情提示】 再高明的政治家,也会在利害关系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平衡和妥协,并且采取必要的策略,最大限度降低损失。湖南巡抚陈宝箴试图打破1898年春夏僵局,调和新旧两派的尖锐冲突,但战火远比想象更难平息,甚至还烧到他这个“裁判员”身上了。而直接挑战他这个巡抚的,竟然是湘绅领袖、原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对阵这位咄咄逼人的学界泰斗,陈宝箴如何应对呢?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  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相关阅读】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1)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3)守旧势力大举进攻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4)主帅陈宝箴的危机公关 陈宝箴本来希望在撤销熊希龄时务学堂的总理职务、南学会停讲之后,湖南两派势力之间的争斗会有所缓解;结果事与愿违,王先谦等守旧势力并未因陈宝箴的妥协和调整而停止进攻。《湘绅公呈》发表后,陈宝箴曾拜访王先谦,甚至谈到《湘报》可以停刊。当然后来没有停刊,只是加强了审查。王先谦因此写信给陈宝箴,说:“报馆一事,前面谈时,尊意拟即停止,后晤少穆,知系暂停,复启将牌示馆门,非经钧览,不准付刊,立法至善……1然值熊君决裂之余,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诵,莫不以停止为宜。论湘中之政务,去之无害,而颇有益;论台端之名望,行之无加,而或有损。”56等于逼迫陈宝箴必须将《湘报》停刊而后已。  湘报 陈宝箴的“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也曾送给王先谦过目,王不赞成陈宝箴对康有为的回护,主张不留“祸本”。他再次写信给陈宝箴说:“日昨惠顾畅谈,至为快慰。赐读请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于厘正学术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甚善!但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粤(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视君上之心。充其伎俩,何所不至。吾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有伤知人之明,或为大名之累。如先谦者,激扬有志,旌别无权,远师苏氏之辨奸,近法许公之忌恶,所谓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我公得毋笑为愚拙罕通乎?大稿敬缴,余容续罄。”2这无疑让陈宝箴碰了一个软钉子。但陈宝箴对王先谦的观点作了有说服力的反驳,不仅没有妥协,反而进一步为康有为辩,重申康有为之能言敢言为至属难能。他在回复王先谦的信里写道: 祷雨不应,惶迫万端。台从鉴其闭阖待罪之隐,复枉过门,弥深愧感。辱书具仰至爱。第区区之意,以谓今日之以康有为为悖乱、为祸本者,当不乏人。闻自许大司寇外,弹章已十数上。而皇上顾赐之召对,不加诛戮,而用之总署。岂不以其无悖乱之迹,而所陈皆勤勤君国之言,且有为内外诸臣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耶? 康有为之徒,不乏才隽,要皆以为依归,与其使为北胡南越之用,何如使为我中国之用?叛则征之,服则舍之,固王者之大公。况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前日面谈,谓投诚者尚可收之为用,即孟子“归斯受之”之指。而必毁其书者,以为其宗旨所在。乌喙去毒,而用之得当,则可以愈疾耳。程子我辈激成之言,与老泉辨奸之论,孰得孰失,此有气数存焉。进言者,惟期此心,先可自问。知我罪我,可以弗计。然盛意则良友执谊,不敢忘也。3 我们从此信可以看到陈宝箴学术和政治观点的坚定性,他守己见,而绝不迎合对手。“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右铭自然是对的,因为预设的嫌疑,不能当做真正的罪证。“此有气数存焉”六字,更具历史的辩证的思考。这是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第一个回合的对阵,可以说是打成平手。 第二个回合的对阵,关涉的问题比较严重。戊戌年的六月下旬左右,湖南省城流传一份匿名揭帖,将前者宾凤阳等致王先谦的信添加秽语,中有“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等诬词。为此,时务学堂生员向抚院提出正式禀词,要求提宾凤阳等到案,严加追究4。陈宝箴看到禀词及所附揭帖,极为震怒,立即写下长篇批语,要求布政司和长沙府彻底根究,严加惩办。陈宝箴的批语写道: 据禀并抄粘揭帖,所刊宾凤阳等上王院长禀函,殊深诧异。查本年五月间,岳麓王院长等,以“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以端学术,而挽敝习”等词,具呈到院,并附宾凤阳等呈王院长函禀各件。本部院查阅宾凤阳原函,只有指斥教习诸人学术宗旨之语,尚无格外污蔑之词。兹阅该学生等抄粘此函,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愤。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所不耻耳。又查揭帖所称“不解这班禽兽及学堂诸人,自命豪杰,至阴为此禽兽之行”数语,鄙俚恶劣,有如梦呓狂吠,为前次王院长附来宾凤阳等原函所无。是否宾凤阳等自行删去,殆刊布揭帖时,始行增入?抑或另有痞徒,假托掺杂?揭帖传播已久,宾凤阳等岂无见闻?如果系为人假托妄增,自应早为辩白,以自明其不为此市井无赖之行。乃竟嘿无一言,听其流播,是诚何心!此等飞诬揭帖,原于被谤之教习与肄业诸生,毫无所损。惟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既显悖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极堪痛恨!仰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迅饬长沙府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到司,彻底根究。究竟出自何人,刊于何时何地,务得确情禀复,严加惩办,以挽浇风,而端士习。切切。仍候学院批示。5 就笔者见到的陈宝箴的文字,很少像此批这样充满了愤怒的火药味道。“下流败类”、“梦呓狂吠”、“极堪痛恨”一类极端词语,一泻而下。如不是盛怒无状,已是六十有八的右铭,断不至此。而且指出攻诬者的目的,是要“谣散学堂,阻挠新政”,非常合适、不事夸张地给对方戴上了“阻挠新政”的政治罪名的帽子。 陈宝箴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下流的谣言所激怒,同时也不无另外的缘由。这就是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一道谕旨里,表彰了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改革,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6颇有要惩处阻挠改革者之意。时务学堂学生禀词就援引了此道上谕,企图给守旧势力施加压力。所以陈宝箴的抚院批语用了“阻挠新政”一词,并立即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决心对揭帖制造者严加惩办。 王先谦得知此事之后,颇为紧张,第三次写信给陈宝箴,力为宾凤阳辩护,说他敢保证必不是宾凤阳所为。但信的结尾,精神气象大为下降:“若使宾凤阳等以上书先谦与先谦呈书台端之故,而令宾凤阳等身受讼累,先谦复何颜面以对书院诸生?幸宏解网之仁,收回成命,亦为先谦稍留余地也。”7语意之间不无可怜情状。最后甚至还抛出了身体欠佳的哀兵之计,写道:“先谦孱躯善病,近复加剧。主讲之任,非复能胜。谨即告退,希择名师,以完残局。幸甚。”8王等守旧势力对前段的进攻未免过于忘形,故在皇帝谕旨之后,面对态度变得强硬的陈宝箴,不自觉地略带颓唐。然则亦绝非示弱,所以又以辞却岳麓书院主讲一职相要挟。 陈宝箴得王先谦信后,又作了回复,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反驳王先谦的看法,使王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陈信写道: 奉展惠书,至为惶悚。细绎词意,似台端于学堂公呈批语,有未尽察者,敢以毕陈左右。 弟前月偶闻人述揭帖一事,云有人与岳麓肄业生谈及,此生旋由书院携一纸未经粘帖者予之,中有宾某上院长及陈某致欧阳节吾两函;其宾某函,丑诋不堪,然未质言其若何丑诋也。欧阳节吾来省,言其乡涂舜臣曾见宾函,有不可出口等语。及前日至贡院考试,收到学堂公呈,则宾凤阳一函在焉。阅至丑诋之词,其刻毒诚令人痛恨,而其语则为公交来原函所无。因于批词特地标出,以见饬司查传根究者,乃因揭帖之刊有此函,非因院长之交有此函而传之也。此中界限分明,较然明白,与台端绝无干涉,似无因以此为罪也。 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实所不悉。其揭帖中语,是否为人假托羼入,不能无疑,而亦不能遽定。但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声口,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赧然不安,即不虑受谤者与之为难,亦当思亟为辨别,有以自处,顾何以嘿无一言? 省城之有无张贴,弟虽不能尽知,然早闻前月以来,得此帖者甚多,亦有编订成帙者。且书院既有此帖与人,宾凤阳等未必讫无闻见。闻宾凤阳系书院斋长,即未列名,亦应向之根究。既未辨白,又有主名,批令总理学堂之藩司查传根究,自为事理所应有,不得为过。且云究竟出自何人,务得确情,其非竟指为宾凤阳等所为可知,然不能不从宾凤阳等推究。 诸生被控,似非不可传问,如果无过,亦自可以辨明。且藩司非听讼之地,传又非拘拿可比,批语中亦无讯字。至于词气不类,固可一览而知。然人情变幻百出,亦何不可有意为之?此又人情所恒有,而不得谓为推求之过当。想台端易地而处,亦未必谓有此一节,遂足以资折服也。若谓为学堂诸生所自为,以图报复,而自污至此,此则弟之愚蒙,所不能逆亿,抑且有不忍逆亿者。以此咎弟,咎实难辞,先生但观过知仁可矣。总之,批词既明明与院长无涉,即更无地步可留。至台端之不袒生徒,而裁之以义,则固屡有明征。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又诸生之所共喻。但期不至有司之无理摧折,坐视不为一言则已耳。辞馆之说,恐非义之所安也。恃叨知爱,辄用缕。9 陈宝箴此函的措辞严肃冷静而不让分毫,可以看做是湖南两派势力发生撞击以来,主张新政的湖南巡抚第一次向守旧势力给以反击。 鉴于王先谦竭力保护肇事者宾凤阳,陈宝箴不客气地说:“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实所不悉。”意谓你说宾凤阳好,但我从未听你说过,究竟是否如来信所说那样好,我实在无从知道。如果宾真的品学皆端,看到揭帖中假自己名义的市井下流语言,而又确不是自己所为,应该脸红应该汗颜,应该站出来剖白,何以一声不吭?针对王先谦信中说的揭帖可能是时务学堂学生所自为,陈宝箴说,这是他不能想象的事,他也不忍作这种想象。实际上对王的说法表示鄙夷。至于王以辞馆相要挟,陈宝箴说,这样做恐怕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王先谦接到陈宝箴的上述信件,又写《四致陈中丞》,已无多少实际内容,只强词夺理地说:“台端之逆亿,不忍施之学堂,何忍加之书院?”10对学政徐仁铸批示要求的各学官应“传谕各士,确切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询究”11,王先谦向陈宝箴汇报说,已经传集诸生,但宾凤阳不在,他回了衡山老家。实际上是这位王益吾祭酒设法把当事人保护了起来。关于辞馆一事,王先谦说是因为“近日多病”,而不是由于宾凤阳的事个人有什么意见。陈宝箴无意继续和王先谦争论下去,于是复信给王说:“手示敬悉,论议往还,彼此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公之不袒书院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学堂,独不蒙见谅。则弟平日素行,不足见信于君子,非目前之咎也。虽然国家事势如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盐道另函,想仍辞馆。前说湘中物望在公,弟亦忝长群僚。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公非恋馆,弟亦非恋官。臭味之同,可不言而喻也。请释戈解甲,容再负荆,何如?”12颇有牢骚而不耐烦的情绪,意即我们不要这样争来争去了(“释戈解甲”),如果你一定辞馆,那么我就辞官,如是而已。 这一次陈王对阵,王处于下风。据王先谦《自定年谱》记载:“旋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诬蔑伊等,就宾等元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余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逢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极委婉,时已八月初旬。”13如是,则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矛盾,后来已发展到激化的地步。 王所说的“中旨”,系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光绪帝谕旨:“电寄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止,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14但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政变,历史未能提供陈宝箴和王先谦冲突的另一种结局。(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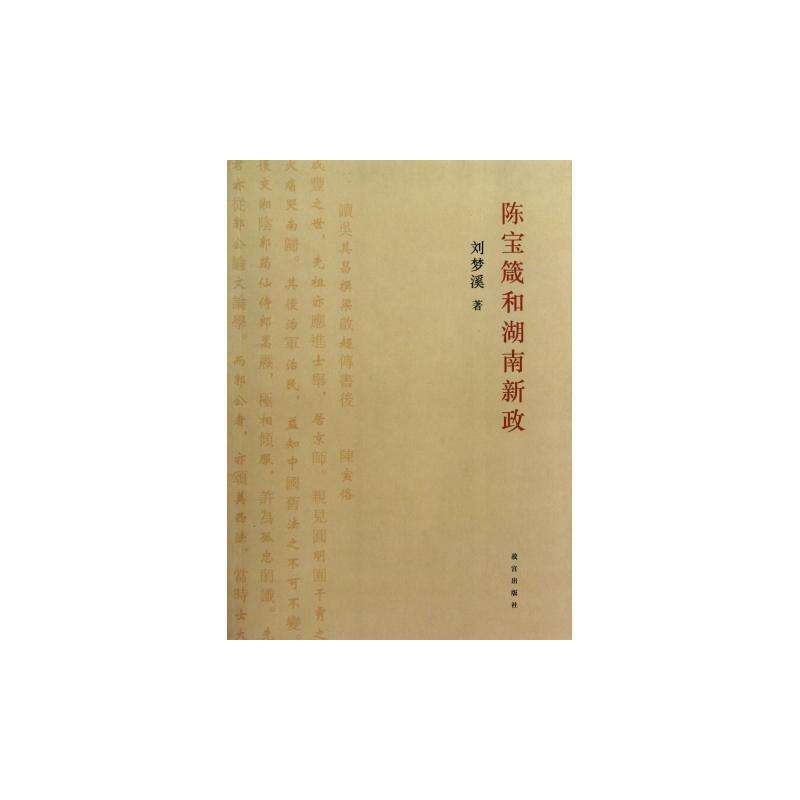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 参考文献: 1 王先谦:《致陈右铭中丞》,载《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第864〜865页。 2 王先谦:《再致陈中丞》,同上,第865〜866页。 3 陈宝箴复王先谦书(《陈中丞复书》),同上,第869页。 4 《时务学堂禀词》,同上,第871〜872页。 5 《抚院陈批》,同上,第873页。 6 《上谕》第125条,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2页。 7 王先谦:《三致陈中丞》,载《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第870〜871页。 8 王先谦:《三致陈中丞》,同上,第871页。 9 陈宝箴复王先谦函,同上,第876〜878页。 10 王先谦:《四致陈中丞》,同上,第878页。 11 《学院徐批》,同上,第874页。 12 陈宝箴复王先谦,同上,第879页。 13 《王先谦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蔡园四种》,第745页。 14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