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7)改革派内部为何分裂|独家
http://www.newdu.com 2025/04/11 05:04:17 凤凰网历史 刘梦溪 参加讨论
【前情提示】 相当长一段时间,讨论戊戌变法,总会不自觉陷入康梁话语体系,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改革的成败,全取决于阴谋及其背后的新旧实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微观史学告诉我们,改革进程的演变,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影响。譬如,“守旧派”的形成原因,未必天然就反对改革;又如“改革派”,未必从来就是铁板一块。1898年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留下许多线索供后人反思。其中起步最早、领一时风气之先的湖南新政,如若检讨改革阵营内部,也有诸多裂痕早已产生。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 【相关阅读】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1)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3)守旧势力大举进攻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4)主帅陈宝箴的危机公关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5)巡抚与大儒的正面交锋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6)张之洞为何转向  图注: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湖南新政在八月政变前一段时间的艰窘情形。 当1897年秋天到1898年春天湖南的改革达至高潮的时候,大吏、绅士、士人众志成城,集合在巡抚陈宝箴的周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湖南振兴为怀抱,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全国的改革人士无不啧啧称赞,甚至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可是到了1898年的夏天和秋天,形势急转直下,比之先前,判若两重天地。士绅雅聚,笑语喧阗的情景不见了,代之以攻击谗陷。南学会讲论、时务学堂问答的热烈场面没有了,代之以冷清散乱。原来仿佛一体的士绅,转瞬间分成了互有嫌隙的三个派别。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自是一派。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陈宝箴被迫调整了改革政策以及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开始对领导他们改革的抚院有了不满情绪,改革的激进和渐进的分野开始明朗并趋于对立。 谭嗣同因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官课出时文题目以及批评他称康有为作老师,给欧阳节吾写了措辞强硬的信。他说:“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其机括,是以有前书,却非敢抗函丈谓不当教训之,而己决意不受教也。”1向老师表示他与唐才常二人要以生命以之,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见一斑。  时务学堂遗址 而前此一函明显涉及和陈三立的矛盾,其中说道:“请转语伯严吏部,远毋为梁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妒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同,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 2 则此信之锋芒明显指向陈三立,说明彼此的裂痕已到相当程度。笔者研究此段史事,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不觉为之神伤。 熊希龄被撤去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除有要求整顿通省书院上抚院一函,另还有《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也是要以生命以之。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夫办事有二大患,一曰养奸,一曰酿祸。今省中物议纷腾,黑白混淆,若不打破此关,痈溃一发,受害更巨。矧湖南负天下重望,虽新政只有萌芽,而各国报章交相赞美,倘一事无成,岂不贻笑五洲?以后湘人更为外人所轻视,将来交涉之事,亦难与外人理论,其吃亏非小。况攻讦之风日炽,则办事者皆有戒心,所以汪颂年有辞总理之事也。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3 熊希龄平日并没有过激的言论,只不过态度坚决,肯于任事而已。因为遭到解职的处分,他发出愤怒的不平之鸣。他也要“以性命从事”,且自称“草人”,恰好可与唐之“横人”、谭之“纵人”并列为湘中“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王先谦给陈宝箴函里所说的“熊君决裂”云云,就是指的熊希龄这封态度决然的信。此可见当时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及意气纷争,已是无可挽回之事实。 邹沅帆致汪康年的信里,有一封详细叙述湖南改革派分裂的情况,虽有个人的情绪好恶羼杂其间,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原信写道:  汪康年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做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时务学堂各分教,均一律辞去。卓如得保,自不再来。右丈意拟请子培为总教,其分教则用湘人士之通达者。昨电请催子培(沈曾植字子培——笔者注)来湘,不知此君现在何处?甚盼甚盼。得此君,湘氛当可廓清,祈力赞之。”4 邹沅帆此信包含有诸多可靠信息。第一,熊希龄与抚院已经怒目相向,“决裂”之说看来非虚。第二,解除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黄遵宪代管一段时间,陈宝箴很快已委任汪颂年来接任。第三,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三位分教习,已经辞职离去。第四,时务学堂中文主讲拟请沈曾植来担任。这些,对湖南新政而言,应该是很大的变动,的确走向了停滞、停顿和倒退。另外邹此信还证实了改革派内部之矛盾,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邹沅帆信里讲到的另一件事情,是谭嗣同因受徐致靖的保荐,已经离开湖南。谭离开湖南的具体时间是戊戌年五月初,当往湖北尊人(湖北巡抚谭继洵)署中小住,六月十六日起程,七月初五日到达北京5。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光绪帝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后来谭嗣同尝电招唐才常赴京,因不久政变未果。黄遵宪也因徐致靖的保荐离长沙赴上海,光绪皇帝欣赏他的《日本国志》,因而任命他为出使日本大臣,并一再催行;但他因病滞留在沪,未及到任,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写到这里,我想引录皮锡瑞听说黄遵宪即将入觐写给黄的一封信,从而可知皮锡瑞离开湖南以后对湖南新政的拳拳之心。皮锡瑞的信写道: 顷阅电报,知公以盘盘大才,受非常殊遇,东山重望,克副苍生,西贼寒心,先知小范。康、梁奇士,谭君伟人,我黻子佩,同趋朝命,左提右挈,匡济时艰,甚盛事也。惟湖南新政初颁,保卫局、迁善所、课吏馆一切章程,皆烦经画,而仁风未遍,福曜速移,虽萧规曹随,不乏继起之守,而良法美意,究以创始为难,惟愿寇君一年,忍听邓侯五鼓。公之入觐,弟将为天下贺,而不能不为湖南惜也。深观时局以及乡评,天下未必即能维新,而有维新之机;湖南未必能尽开通,而有开通之兆。凡事机兆既动,则其势必不可遏抑。今之所以嚣然不靖者,正以两党相争,国是未定。数年之后,风波自息,风气自开。开通之人,必多于锢蔽;守旧之党,必不敌维新。此是一定之理,断非一二妄庸巨子所能挠。公在湖南,为国为民,殚忠竭智。人心狃于旧习,未能仰测高深,是非不明,毁誉参半,将来成效可睹,必当去后见思。前歌孰杀,后歌谁嗣,古之遗爱,非公而谁?弟以不才,过推讲学,未能开通民智,不免胥动浮言,反致纷纭,深负委任。公去后无人护法,中丞不能常至,讲学一事,未知能否复行?6 此函充满了对湖南新政的关切之情,不仅对黄遵宪,对湖南的维新人士均备极称赞,称谭嗣同为“伟人”,对争议最大的康、梁,也称之为“奇士”。他身在江西,却心系湖南,他走后湖南的每一新消息他都备加关注。戊戌年七月初五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得湖南来信,谷价昂贵,人心惶惶,新政阻挠,保卫局初行,城外即有劫局之事。湘潭抢劫,乱民可虑。鹿泉详言大局之坏,实由沈诸梁一人。学会将散,孝廉盘踞,宣翘已去,伊亦将辞。”7此又可见政变前夕湖南的混乱和不景气状况。听到谭嗣同等以章京行走军机,他说“闻此好音,不禁有老杜‘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之感”8。他还为陈宝箴担心,引江西布政使的话,说“湖南抚台难做”9。 就是说,戊戌政变前一段时间,湖南新政不只是停顿了下来,而且热心改革的精英们也先后星散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混乱。王先谦的气焰虽为陈宝箴所挫,但他以辞馆相要挟这一招,给陈宝箴造成很大压力。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未稍歇,至有“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的举动100。七月二十六日,湖南邵阳举人曾廉上封事,全面攻击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投出了重磅炸弹,他摘录一些最能触犯清廷忌讳的时务学堂札记批语,并加上评点按语,作为康、梁大逆不道的证据,提出“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其所附“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片”举了四条札记批语作为例证: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臣按:梁启超之意,是惟恐国祚之不短耳。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臣按:《论语》以拜上为泰,而以违众拜下为礼。梁启超习闻康有为平等之说,以为天子亦平等也,焉用礼乎?此所以欲去拜跪也。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做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极重,未有以为怨者也。苟不为民做事,虽轻亦怨矣。中国之赋税,至本朝而极轻矣,其不足以供币帛饔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国是也。以赋轻之故,及至官俸亦不能厚,恶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耶?”臣按:梁启超知引西人入中国,必大桀小桀,故预为之地步耳。其心无本朝久矣,故直斥为貉而不惮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臣按:本朝美举不可殚述,梁启超独拈出《扬州十日记》,无非极诋本朝,以惑人心。且又预为关说,若入中国必不杀人。洪杨之逆,先斥本朝之非,而后以不杀人诱人,遍告东南一带也。故臣实不知梁启超是何居心也。11 梁启超称曾廉的上封是“最有力之弹章”,甚至影响到政变的发生12。但光绪是否看到了札记批语,研究戊戌变法史的学者有不同看法13。我们只知道光绪让谭嗣同来处理这件事,谭建议以毁谤新政罪斩曾廉,光绪没有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又对陈宝箴所保人才提出严厉批评。 杨是戊戌维新的激进力量,与康有为关系至密,他在“为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诸新进甄别宜严、庶以重封疆而警贪酷、恭折仰祈圣鉴事”专折中写道: 臣前奏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遂奉温旨褒嘉,以励其余。讵该抚被人胁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固由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而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素属知名,余多守旧中之猾吏。王秉恩久在广东,贪险奸横,无所不至,前署抚游智开劾其把持各局,大类权奸,革职,嗣以夤缘李瀚章开复,兹且营谋特荐,此人岂可复用?欧阳霖久办厘金,刻薄性成,怨声载道。杜俞居心巧诈,营私牟利,历任上司无不能得其欢心者。杨枢以庶吉士入李鸿章幕,招摇纳贿,把握威福,捐升道员。至陈宝琛虽旧有才名,闻其居乡贪鄙,罔尽商贾之利,行同市侩。余人臣所未知,特能谙时务者少耳。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之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保举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其他大臣、督抚所保人才,亦有不孚物望及曾被参革者,虽未必蒙混为心,要是诹咨未的。他过或可痛改,惟贪墨者万无洗心之日,终不可与祓擢也。拟请旨严谕中外大臣,嗣后如保革员,必将其原被参事由声明,庶桀黠辈不敢欺大臣以求保,无从施其伎俩矣。臣非刻核存心,多否少可,诚以皇上举行新政、综核名实之日,举一人须得一人之用。若坚持旧见者,虽廉正犹乏济时之功,而况贪狡乎?虽平世犹在屏斥之列,而况艰危乎?谨不避嫌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14 据说这封奏折是康有为所代拟,所以对湖南情况非常了解。奏折中否定评论的几个人物,虽难免仁智互见,但康、杨的看法应不无道理。陈宝箴的保荐名单反映出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和不得不谨慎行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杨深秀此折所说的湖南“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只剩下一个保卫局,其实这就是戊戌政变前夕湖南新政停而后败的实际景象。幸好奏折对陈宝箴有所体谅,知道所以如此,是因为湖南的“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是“被人胁制”的结果。“胁制”者为谁?我以为是王先谦。王以辞馆相要挟,还不是胁制吗?因王在湖南士绅之中影响极大,他的绝然反对态度,可以使许多学子不报考时务学堂,其劣者则去南学会哄闹。  杨深秀 光绪知道杨深秀的奏折之后,在七月二十九日当天,发谕旨给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15陈宝箴面对光绪的谕旨,既有压力,也受到鼓舞。前引他针对王先谦的要挟说的“岂但辞馆,我要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惜湖南新政的另一种结局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六天以后,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便发生了。(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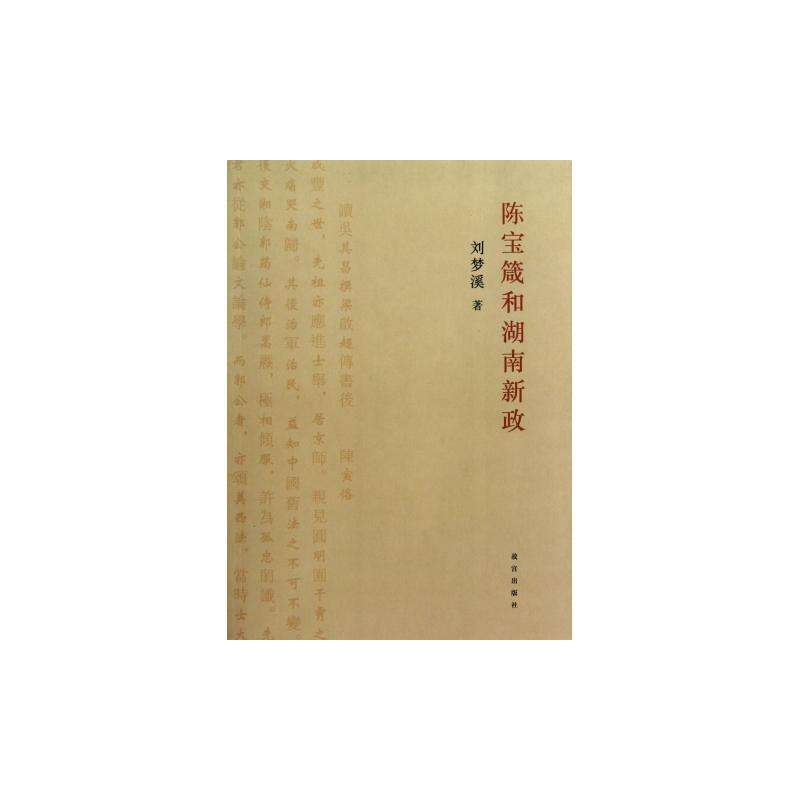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 参考文献: 1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六通,《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78页,按此函末署“受业门人唐才常、谭嗣同仝禀”。 2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二通,《谭嗣同全集》,第475页。 3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上陈中丞书》,载《湘报》第一百十二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下册,第1060〜1061页。又《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78〜79页。 4 邹沅帆:《致汪康年》第六十九通,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7〜2758页。 5 《谭嗣同全集》所收致夫人李闰第一函,戊戌年五月初二日发自长沙,称“正欲起程赴鄂”;第二函六月十三日写于湖北巡抚署中;第三函为七月十一,发自北京,说“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见《谭嗣同全集》第530〜532页。 6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初三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19页。 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五日条,同上,第138页。 8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条,同上,第145页。 9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四日条,同上,第137页。 1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政变前记”,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0页。 11 曾廉:《应诏上封事》,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02〜503页。 12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13 参阅黄彰健:《论曾廉上书导致康党拟武装夺权》,《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书店,2007年,第505〜527页。 14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军](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82页。 15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