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美学: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14 《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 路新生 参加讨论
所谓“历史美学”,具有两重内涵: 其一,用美学视角看待历史,其要义在“以人为本”,将“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歌德谈艺术创作:“我们不认识任何世界,除非它对人有关系;我们也不想要任何艺术,除非它是这种关系的摹仿。”⑩“世界大事对于这人来说,就只因为这些事是符号,可以从而看出人的理念,然后才有意义。”[24](P255)美学以“人”为中心,历史学当然也要以人为中心。关于这一点,史学理论家科林伍德在回答“历史是做什么用的”问题时所给出的答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的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大家都认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就是,他应该认识自己。这里,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其为一个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25](P38)。 人谓“文学即人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人学”?用美学眼光考量历史,是要将历史学还原为“人学”,注重“人”在历史中的主导性地位。这里的“人”,绝非一空洞的概念,而是指有鲜活的心灵活动,有思想语言,有动作,血肉丰满,归根结底具有人性的“人”。历史正是由这样的“人”创造的。史家让这样的人担纲历史的主角,史著才有发自活生生人的心灵活动——黑格尔称之为“情致”;人受“情致”制约采取行动,即黑格尔所说的“动作”;有“动作”才有“情景”;有“情景”才能够形成历史“场景”。 研究历史,不考虑人性问题,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马克思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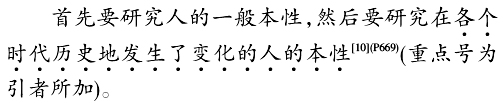 黑格尔说: 尽管各民族之间以及许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各阶段之间有这些复杂的差别,但是作为共同因素而贯穿在这些差别之中的毕竟一方面有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有艺术性,所以这民族和其他时代还是同样可理解,可欣赏的[12](P27)。 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指出: 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他各级存在物只有按照它们暗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11)。 这就是说,“人性”处在高于一切时代性、民族性等因素造成的特殊性、差异性之上——人性处于最高位。“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可以借用董仲舒的这句话改说为“天不变人亦不变”。成千上万年了,人还是人。“人”,人的本质属性——“人性”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皮平研究社会学,他在《现代性是关于自由和自由的实现的故事》中谈艺术史,却涉及一些美学问题,可以拿来作“历史美学”的解读。皮平认为,撰写艺术史不能只是说明“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另一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而是要洞察“在艺术史中人们所经历的是那同一个实现和认识自由的过程”,“该过程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本质性的展开,这种展开对于人们达到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直面现代世界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反思这些问题的真实含义和可能的解决道路”[26]。人们通过艺术作品可以觉悟“自由的自我意识”;人们从以往自身的经历中——从历史中更加能够觉悟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美学”的基本原则“美是生活”时提出的两个命题所言,“美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如此的生活”,“美是使我们想起人以及人类生活的那种生活”(12)。车尔尼雪夫斯的“想起”已经属于“过去时”,因此已经成了“历史”,更不用说车氏这里的“想起”不能不蕴含人类“以往”的全部生活经验即“历史经验”。艺术作品需要“直面现代世界的问题”,人们同样可以通过史学作品,用“历史”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史家经常强调的“经世致用”。所以,早在2000多年以前,孔子作《春秋》时已经认识到了撰史必须以“人”为中心。其弟子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27](P7) 历史并非直接书写现实,却往往能够洞透现实。因为绝大多数现代世界最本质的问题——涉及人和人的本质属性即人性的问题,在历史上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今人与古人能够心心相印“今古相通”;人们可以理解并欣赏隔着时代鸿沟的各民族的历史,其根本原因在此(13)。据此,史家撰史时必须考量“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与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驱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内在力量”[4](P50)等与人性密不可分的内容,它应当成为史家在直面“历史”时需要思考、剖析的主要对象。 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宣判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死刑”,中国传统史学关注人和人性的突出特点亦随之消亡殆尽。发展到现今,已经绝少有史家会去追问如下与“人性”相关联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善乎?恶乎?爱心、诚实、公正、独立、勇敢、自尊、庄严、精神圆满、思想自由、个性鲜明乎?自私、残暴、奴性、邀宠、谄媚、屈辱、脆弱、虚伪、愚昧、仇恨、精神委顿、思想禁锢、个性泯灭乎[28]?而上述“人性”要素,既符合黑格尔所说只有“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到了它的最高职责”[4](P10)的“艺术”和“美”的宗旨,同时也完全应当成为史家关注“历史”的重点。因此,瞩目于“人性”的历史美学认为,历史的价值绝不应仅仅停留在体悟它的“进程”上而需更进一步。历史的价值尤其在于:它“直指人心”,剖析而警策历史,能够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康德语),鉴往知来,引人向善,故其终极目标在于引领人对于其何以为“人”并考量其“类性”而“惩恶扬善”。在与古人进行心灵交会的过程中净化人性提升品位,在获得对历史审美享受的同时论世而知“人”。因此,如果说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那么,历史的真实只有在融入了人性的伟大力量而被史家“重新发现”以后,才能够成为人类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其二,“以美为本”。“艺术性”——美,只要是正常人,又有谁会拒绝她呢?所以,“以美为本”终究也还是人性的表现。历史美学主张用审美眼光审视历史学,注重史家的“思想”、历史叙事的方法、历史书写的格局。人的任何“表达”都从痛感和快感中分泌出来。史家也一样。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指出,决定历史叙述本质上并不取决于史实本身,而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史家出于其职业的敏锐感喟历史,以其独特的视角,采取一种主体审美的意态鉴赏历史,他必会“痛”或者“快”,对此他感慨系之内心躁动不能遏制,“茹之而不能茹”撰为史著。那么,陆机《文赋》所谓的“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也就不仅是文家的,同时也是史家的了。历史既然由“人”创造,这创造便只能在“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是有充分理据的判断。对于个人,我们通过他的具体行为了解他的真精神。同样,我们通过史家撰史这一“历史行为”,可以走进史家的心灵,体会他的“气韵”。傅雷说:“艺术的历史效用,尤在使我们与一个时代的心灵,及时代感觉的背景接触。”[29](P280)史著的历史效用也正是如此。通过阅读史著,我们可以去感悟法国著名史学家、美学家丹纳提出的“精神气候”[30](P17),或钱钟书所说的“舆论气候(climate of opinion)”[22](P367)。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学。亚里斯多德赞美“诗人”时说: 诗人在安排情节、用言词把它写出来的时候……还应竭力用各种语言方式把它传达出来。被情感支配的人最能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具有同样的天然倾向,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13]。 “史”、“诗”相通。诗作能够打动人,需要“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史学作品同样如此。人们览史读史,并不仅仅以知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为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史实寻找今、古之间相似的连接点,沉潜于史家的心灵,求得情感互振和心灵共鸣。例如,《史记》之所以博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就因为太史公受腐刑“发愤著史”,他将最真实的情感,亦即他的“思想”倾注到《史记》之中而发为泣血的咏叹: ……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裂,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锅,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31](《司马迁传》)。 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些在中国星汉灿烂的史学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史家们,我们要表达的敬意与感激是真诚的。正是他们,让那些竭力挣脱“历史现实”的牢笼,为真、善、美受着痛苦和煎熬的“经历者”;或是苟活而延续躯壳的存在,但却灵魂缺失人性泯灭的历史亡灵一个个重新鲜活地挺立起来,告示我们:这就是“人”!这就是作为“类”的人的真实面相!通过撰史,史家实现了其心中的最高理想与人生职责。 当然,史家撰史仅仅有真情即“思想”还不够,还需要用文字和特定的体例将真情及思想表达出来。又因为史诗相通,人们在判断一部史著的文野高下时,便应当以其是否把握并运用了“美学”之相关原理(如钱钟书所创获的史有“诗心”,史“文”与诗文均重“律”;以及诗之“持”与史之“持”等等)为圭臬。例如,我们看《左传》和《史记》。上接左丘明、太史公千古神思,聆听其吐露心声,使我们在充分享受“美”的同时也触摸到了左氏、司马迁的灵魂与史识。《左传》、《史记》体例结构严密规整,遣词用语炉火纯青,运笔行文浑然天成,不矫揉,不造作,自自然然,不露斧凿之痕,不带丝毫的“俗气”和“烟火气”。康德赞美“鲜花盛开的草地,溪水奔泻”等“自然美”可以引起“令人陶醉”的“愉快情感”[14](P13)。读《左传》、《史记》的“赏心悦目”,正像欣赏自然景观一样。左氏、太史公的历史叙事充分调动了视觉、听觉甚至触觉诸要素,这便大大拉近了它与“人”的距离,因此充满了“人趣”。尤其《左传》、《史记》那“言”中有“事”(用对话本身叙“事”即叙史,史家隐身于“后台”,让历史事件本身“发言”);“事”中蕴“言”(历史叙事中采用历史人物的对话)的叙事风格,像一部轰鸣的交响曲大气朗然,将善恶美丑放在一个调色盘内化于笔下,由此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先导性、典范性的影响,而且在理解语言本身也能够撬动“历史”使之跌宕起伏(此为借助美学审视“历史”)方面;在鉴赏性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强烈的美感体验(此为用美学眼光看“历史学”)方面,《左传》、《史记》都能给我们以极其深刻的启迪。这其中便蕴涵着“史”、“诗”相通之理。 “蕴道而不言道”,既是“诗”创作的准则,同时也是“历史书写”之方法。这一点非常吃紧。这里可以借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谈“诗”的体悟加以说明: 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 在“说理”与“叙事”的处理原则上“史”、“诗”一致。以“诗”拟“史”,史家与诗家一样也有他的“纲领性”理念即“史义”。但史义即“道”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单独跳出来表达。歌德的艺术创作论主张从“特殊中显出一般”,他指出:“它(艺术)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象征把现象转化为一个观念,把观念转化为一个形象,结果是这样:观念在形象里总是永无止境地发挥作用而又不可捉摸,纵然用一切语言来表现它,它仍然是不可表现的。”(14)黑格尔提出艺术应当遵循“普遍力量的特殊化”[4](P252)原则,歌德、黑格尔的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他们所说的“一般”,“普遍力量”,可以解喻为史家的“意蕴”、“史义”即“道”;“特殊”、“特殊化”则指具体的史实。史著通过史实来寄寓其史义,历史的内容愈具体,蕴含的方式愈隐蔽,史著的审美容量也就愈大,愈经得起咀嚼回味。所以,黑格尔在谈《荷马史诗》的特点时这样说: 为着显出整部史诗的客观性,诗人作为主体必须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表现出来的是诗作品而不是诗人本人,可是在诗里表现出来的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写成了这部作品,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他这样做,并不露痕迹。例如在《伊利亚特》这部史诗里叙述事迹的有时是一位卡尔克斯,有时是一位涅斯特(重点号均为引者所加),但是真正的叙述者还是诗人自己[12](P113)。 黑氏所说的“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是指作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叙事,透过史实,而非直接表露史作者的“意蕴”即史义。就像傅雷谈赵树理的小说“作者的任务还要把主题融化在故事中间,不露一点痕迹”[29](P76)。小说家的“主题”亦即“意蕴”。赵树理将主题“融化在故事中间,不露一点痕迹”,应用的就是“隐身法”。殊不知,这也是史家撰史应当应用的方法。回视当今史著,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不懂得至少是不甚懂得,历史书写的一般性质是叙事的而不是说理的。叙事须站在“第三方”;说理才是“第一方”,二者立场不同,方法各异,产生的效果便大相径庭。看当今史著,其中并非没有史实,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他有事实而不够“公正”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史家每每急不可耐从“后台”走到“前台”充当“主角”,急于做历史的裁判员,而不是历史叙述者。这有一点像音乐家傅聪口中“不高明的演奏家”,他们“在任何乐曲中总是自己先站在听众前面,把他的声调口吻压倒了或是遮盖了原作者的声调口吻”[29](P387)。而且,他们总想要向读者有选择地“灌输”自己的裁断亦即理念,忘记了把发言权留给史实本身,让理念“化”于史实之中;他们更不让历史人物自己开口。“以言蕴事”的撰史法,历史人物对话这一撰史要点,早已经被现代史家彻底干净地剔除于史著之外!这在1950-1980年代初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传统史学中,不说《史记》、《汉书》,就连学术史(如《明儒学案》等)、典制史(如《通典》、《通志》等)中都有大量情趣盎然的对话。这就是“以事蕴言”、“以言蕴事”的法则。 千百年来,历史学一直很难摆脱政治附庸与工具的地位,这也成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学术界倘若能够摒弃传统的“文以载道”工具意识的束缚,回复人爱美,爱思考的天性,带一种审美的眼光看待业已逝去的历史场景,并以此欣赏史家的作品,这会对历史和历史学的领悟产生一种“回响式”的新体验。将美学引入历史学并提出“历史美学”概念,正如将美学引入文学、戏剧、影视、建筑等等而有“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建筑美学”等等一样,“历史美学”发展成为一个历史学下新二级学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学科或许会因此而拓出一片新天地,也未可知。此举对于史学理论、史学史、史学批评史、史学书写史本身的发展,当大有裨益,则毋庸置疑。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感官史和情感史的开创者阿兰·柯尔班
- 下一篇:吴恩远: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