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鎮鵬書評Dorothy Ko《硯台的社會生命史:中國清初的工匠與士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1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評Dorothy Ko,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330 pp. 詹鎮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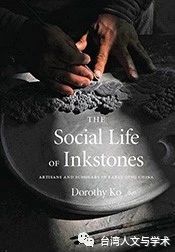 本書作者高彥頤(Dorothy Ko)教授現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系,在其《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和《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兩部早期著作中,她從文化史和婦女性別史視角出發,通過細讀文本,檢視女性的主體性及客體想象,修正以往歷史觀點。[1]近十年,作者的研究對象轉移到工藝和品物,曾於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中國視覺和物質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課程(p. ix),其學術關懷仍一脈相承,只是方法論有所轉移。[2]本書因此可視為高彥頤的研究領域從文獻延伸至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一部轉型之作。[3]她對手工藝者之關注,側重女性,尤其是晚明至民國時期的蘇繡、顧繡女紅等工藝。誠如作者在〈致謝〉和〈導言〉所言,是本書的主人公,即女琢硯家顧二娘,引領她進入硯台的世界,隨後又耗費多年才完成此項研究(p. ix、p. 5)。 作為中、英文學界首部以文房用具之硯台為研究對象的專著,[4]此書處理時段雖集中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間(1680年代至1735年),卻主旨宏大。誠如高彥頤在〈導言〉指出,硯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收藏品,父子、男性友人相贈之禮,鐫字刻銘的紀念信物。透過功能延伸,硯台被賦予「斯文」之意義,成為文人士大夫一類男性菁英主體的物質性象徵。由於硯台總令人聯想起士人形象和菁英文化,作者徵引《孟子》中的「四民」(士農工商)理想制度,指出硯的製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藝者(artisans),總旁落於士人的書寫文獻,希望藉此研究修正儒家傳統「重道輕器」的傾向(p. 5)。作者指出,中國儒家傳統千百年來貶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觀念,是工匠長期在文獻記載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導致學者難以對該群體展開研究。基於上述動機,作者在本書結合傳世實物和文獻史料,重構處於革新期的清初製硯業,並以顧二娘及其福州贊助人作為核心個案,還原當時琢硯工藝及鑑藏市場的歷史面貌。 全書除〈導言〉和〈結語〉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内廷作坊─皇帝及其包衣〉(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運用宮廷造辦處活計檔案,重構康熙、雍正二朝造辦處硯作及其匠人活動。作者特別指出,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二帝在內務府框架內設立、改造養心殿造辦處,開創有別於前代的物質文化,宣示滿族之統治。滿清「物質帝國」(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義(materialist)的統治風格,為宮廷和地方之間在工藝和物質互動奠定基礎。松花石硯則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漢人精英文化和話語的一個案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後,治國方略由軍事轉向文治,隨後他在祭告祖陵期間在滿洲地區「發現」松花石,將其塑造成新式硯材。松花石硯在康熙朝被大量用來賞賜內閣翰林官員,更成為影響雍、乾二朝的工藝遺產。 高彥頤使用「技術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詞,來形容內務府的包衣群體身上有別於常規行政文官的特質。[5]管轄造辦處的內務府作為皇帝的「私人衙門」,行政和財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滿人皇帝信賴的包衣,是該龐大的官僚機器的運作者。作者指出,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雖是皇帝的家僕,卻因享有制度性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清代內廷的各項技術實驗和工藝承作。作者引舉活躍於康熙朝的漢軍旗人劉源,以他設計圖樣的龍德墨、龍光硯為範例,提出民間的工匠力量對內廷工藝的積極影響。清初,因順治帝廢除匠戶制度,從民間召募匠役至雍正朝已成定例,為皇帝透過多種材質構建「內廷恭造之式」創造條件。硯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傳統,重視松花石硯;雍正朝一大特點,則是皇帝同等重視硯盒,時常將硯與盒作統一設計。 廣東省肇慶自唐代以來便以盛產端石這種理想硯材而聞名,晚明以降,肇慶城外的黃崗村民便以端石開採、加工為生計支柱。在第二章〈黃崗村─石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中,作者結合實地田野考察和文獻分析,分別討論開採端石的端州(今屬肇慶)石工和兩類士人掌握的端石及硯坑知識和主體塑造。作者歸納兩類士人的不同寫作動機和方式,解讀視角頗為新穎。第一,是外省或中州士大夫視角的寫作,以北宋蘇易簡(958-996)的《文房四譜》和米芾(1051-1107)《硯史》為例,二書算是硯台品鑑文學的鼻祖。《文房四譜》之體例從屬筆記傳統,作者蘇易簡未曾親自前往端州實地考察,故收錄的內容雜陳,缺乏系統性。高彥頤認為米芾採取不同於前人的寫作策略,強調「眼見為實」,如他自稱「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p. 64)。[6]第二,則是端州本土專家之寫作,以何傳瑤(活躍於1820-1830)的《寶硯堂硯辨》為例,該書用圖文並茂的形式,為端州硯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類體系。 作者在本章試圖申論,石工透過親自實踐及物質工具而世代相傳的本土性知識,雖然與兩類士人的知識書寫方式大相徑庭,但同等重要。她指出米芾和何傳瑤兩類品鑑端坑和端硯的專家,在各自領域掌握著書寫的話語權;相較之下,那些親自開採、加工端石的硯工雖在當地掌握最核心的本土知識,並為士大夫提供一手資料,卻因無法書寫而被歷史湮沒。 第三章〈蘇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重建顧二娘生平及其贊助人網絡。根據時人記載,顧家鋪位於蘇州閶門附近的專諸巷,主要由三代人經營:父親顧德麟,兒子顧啟明,後來二位男性先後離世,遂由啟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鄒)掌舵,並過繼侄子顧公望,授以家傳。作者搜集、重構顧二娘的生平耗費許多功夫,但成效有限,故福州的一群士人藏硯家編撰的硯銘集《硯史》及私人文集,成為作者重構顧氏治硯及其贊助網的核心資料。硯銘是硯主用於題詠硯台的一種詩文體裁,常用刀鐫刻於硯台的背面、側壁,功能猶如書畫作品的題跋。透過硯銘內容可回溯該硯的形制、母題、製作者。 其他文獻罕見顧氏的生平記載,敕製《古今圖書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對顧家治硯的條目偏重男性傳承譜系,身為女性的顧二娘的重要性下降。高彥頤指出,相對於蘇州時人黃中堅(1648-1717之後)和朱象賢,福州的藏硯圈子多是顧二娘的忠實主顧,他們與顧氏有私交,並且看重她的過人技藝。作者將《硯史》明確出自顧二娘之手的硯,與傳世實物相比對,發現兩者無法吻合,表明現存傳顧二娘的作品絕大多數是贗品。 第四章〈蘇州以外─顧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結合傳世實物和圖像,分析傳顧二娘製的硯樣及其工藝特徵。作者受到語義學的「超符號」(super-sign)概念的啟發,[7]新創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詞去形容顧二娘在十八世紀以降的品牌效應。在她看來,超品牌除指名牌之外,它不只是一種獨立的風格,而是像超符號那樣,乃「異質文化間產生的意義鏈」(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橫跨兩個或更多的媒介和地域的語義場(p. 123)。簡言之,顧二娘在當時市場上產生名牌效應,隨之出現多種跨地域、跨媒介的風格變體。她的原作經後世不斷仿製,「原樣」已經難以追溯。作者開宗明義指出,與其徒勞地尋找出自顧二娘之手的「真跡」,倒不如轉換角度提出新問題:為何如此多硯會繫於她名下呢?清人造偽,又如何結合硯樣、款識和硯銘這三種形式,將作品歸入顧氏的名下? 由此,高彥頤在第四章重點挑選傳顧二娘創製的數種硯樣(杏花春燕圖、鳳硯、竹節硯),與謝汝奇製的雲月硯、王岫君的山水硯作比較,大致歸納蘇州、福州、廣東工匠琢硯的地域風格和工藝手法。作者認為蘇州琢硯運用減地壓印技法,製造出如畫效果,或受蘇繡、顧繡的施針技法影響。福州琢硯的鏤空、高浮雕手法深受當地雕印鈕傳統所影響。藝術史界對文房用具的研究受文人品味及話語影響甚深,有待開拓視野,作者的跨媒材比較有助彌補此不足。 第五章〈福州─藏硯家〉(Fuzhou: The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硯史》為核心資料,深入探討顧氏福州主顧的硯台收藏和交際網。作者將《硯史》的貢獻者分為三個梯次,核心成員包括林佶(1660-約1725)、余甸(1655-1733)、黃任(1683-1768)等,次級成員由前者的親屬、友人組成,而邊緣成員是曾為《硯史》撰寫題跋的各式人等。《硯史》是收錄核心成員各自私藏的硯銘集,濃縮了他們的硯藏狀況和「石交」情誼。作者指出,米芾、何薳(1077-1145)等宋人之間雖出現零散的私人硯藏,但是彼時市場未成體系,硯台尚未轉化成一種商品。石硯要一直到清初才真正成為一種收藏門類,這不僅需要孕育成熟的商業市場去配合,更與當時製硯的工藝革新相互呼應。 作者在〈結語〉提煉前面數章,提出清初工匠和士人身份出現一定程度的重疊,福州的士人藏硯家代表了清初「士人型工匠」(scholar-artisan)新文人團體。他們關注工藝知識,對匠人持有敬意,除工於書法,亦會親自動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搨等。作者認為,士人型工匠與藝術家金農(1687-1763)、高鳳翰(1683-1749)代表的「工匠型士人」(artisan-scholar)之間的差異,在於福州士人並未放棄科舉仕途及儒學,而金、高二人不僅無科舉履歷,更缺乏經營士人身份所需的社會身段、姿態(social posturing)和經濟條件(pp. 199-200)。最後,作者更提出大膽猜想:福州士人展現的上述「文之技」(craft of wen)是否可能是乾嘉時期考據學思潮的一股先聲潛流,或至少對後者有一定推動作用呢? 全書的方法論具跨領域、多學科的視野,結合對傳世品的工藝及圖像分析、田野調查訪談和細讀文本。作者多次在北京、臺北、天津、廣東等地的公私收藏機構,親自目鑑或上手逾百方硯台,對作品的真偽鑑別,以及形制、石質之翔實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作者曾在廣東肇慶、福州、北京等地展開田野調查,更與當代製硯手工藝者、收藏家進行深入訪談。全書亦不難見其從工匠的角度出發、兼顧多方視角的良苦用意。根據作者實地調查,至遲晚明,廣東黃崗的許多家庭將雕琢、打磨石硯的精細活交給妻女,而開採和切割原石、製盒、銷售或批發業務則留給男性,形成獨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產業(p. 49)。不過,全書著重於描述男性石工的開採、前期加工環節,即鍛造工具、採石、探礦和維料製璞的知識(詳見第二章)。[8][新史學1] 當地女琢硯工的技藝和經營手法,與清初顧二娘是否具有可比性?前者是否能夠補充後者資料之不足?未見作者就此申論,頗為可惜。 文獻史料方面,全書運用的材料分三類:第一,《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清檔》,採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全本、朱家溍選輯本相互對照。[9]第二,福州藏硯家核心成員的《硯史》,藉此重構顧二娘及閩中士人圈的交際網絡。第三,兩宋和清代的品硯鑑賞文學,如蘇易簡的《文房四譜》、米芾的《硯史》、何傳瑤《寶硯堂硯辨》等。作者不輕信文獻的謹慎態度,及其早年在版本整理和細讀文本的扎實功底,在此有著充分體現。作者針對稀見的《硯史》,[10]在附錄中整理出流傳版本系統,在引註明示各早晚版本在引言、後跋、詩文的增刪和異同之處,根據多人題跋建構出整個閩中士人圈與周邊各式人等的交際網(參見Appendix 3、4),便於讀者理解和進一步利用,著力頗深。 本書另一層參考意義,應該在物質文化的寫作框架內進一步理解。全書呈現不同地區的多組個案,看似零散,實由宏觀至局部,結合層層遞進之敘事,勾勒出一小片與眾不同的物質文化網絡。過去二十年,「物質文化」研究作為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等多學科交叉形成的分支領域,注重由物見人。高彥頤借用Igor Kopytoff (1930-2013)物品商業化的理論框架,[11]試圖追索硯台歷經製作、消費、收藏、修復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社會生命歷程,展現它由單一功能(文房用具)轉變為多重意涵(「斯文」之象徵)的過程。藝術史和文化史學界對晚明和盛清的關注和相關研究汗牛充棟,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對乏善可陳。[12]本書有助於填補該缺環。 透過作者的書寫,石硯的物質生命交織著各式小人物的生動身影,折射出他們的一段生命史。例見清初福州藏硯家圈子自小培養的「總角石交」,以及黃任的妻子寄詩及她的「生春紅」硯的故事(第五章)。但另一方面,高彥頤不忘提醒我們,後世對顧二娘神話的塑造,包括由清人袁枚(1716-1797)訛傳出「顧氏小腳」能試硯石之優劣的軼聞(pp. 144-147),都包裹著時人對女性的身體想象和形象重塑。這不只是發生在顧二娘身上,亦是當今社會的消費文化中的共通現象,故本書所展示的物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讀者去管窺物質世界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古今之變。 毋庸諱言,本書同樣存在瑕疵。除不影響觀點的文字勘誤(參見附表1)外,作者在實物和文獻證據均存不足,且缺乏顧氏硯的真跡去重構其風格原貌,似有以偏概全之嫌。高彥頤在書中不止一次因資料零散闕如,論證停留在假設階段,如對顧氏父子和顧二娘的生平、作坊環境之重建,證據較為薄弱。然而,這恐怕亦印證著作者指出因工匠地位低下,在古今中國乏人關注和書寫的觀點。學界對工匠的專門研究,早期中國可參考李安敦(Anthony J.Barbieri-Low)。[13]明清時期,相關研究則集中於名家留款作品和宮廷匠役,尤以嵇若昕的研究為代表。[14]本書應可以為未來對該群體的文化史研究提供新視角及啟示。 高彥頤引述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明清時期「理學向樸學」轉型的思想史背景,[15]指出十八世紀考據學思潮是對米芾《硯史》「實事求是」的客觀性的一種回歸。在此,作者恐怕誇大了米芾《硯史》這部小書在北宋時期的影響力,也未將之與同時期興起的金石譜錄傳統進行橫向比較,分析兩者著錄藏品的態度、方法的異同,頗有遺憾。[16]無論是北宋還是清代乾嘉時期,關注古器物學、金石學的兩次思潮背後,一定程度上摻雜政治因素。北宋徽宗(1100-1126在位)及上層士大夫,以及乾嘉時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綱(1733-1818)都扮演過重要推手。單憑一項個案研究,顯然不足以回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題。不過,迥異於學界對乾嘉的金石學運動,偏重社會上層菁英為主體的「由上至下」的考察視角,作者藉由物質文化個案,試圖提供「由下至上」的一種另類視角,是否可為未來重新省思考據學等乾嘉學術思潮的龐雜源流提供新的參考?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於2017年9月18日收稿;2018年7月4日通過刊登。 編案:本期原訂2018年9月出刊,因故延至2018年10月出刊。) *本文蒙匿名審查人評閱並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特申謝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現為香港海事博物館研究員。 [1]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譯本參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新北:左岸文化,2007)。 [2]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he Treaty Ports to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漢學研究》,30:2(臺北,2012),頁265-296。 [3] 詳見高彥頤,〈走出文本,轉向品物─談一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8(臺北,2016),頁i-vi。 [4] 據筆者目力所見,英文學界已有李啟樂(Kristina Kleutghen)、劉禮紅、王海城的三篇書評,對此書加以評介:Kristina Kleutghen, “The Social Life of Instones: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byDorothy Ko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22:3&4 (2015): 207-210 (published in 2017); Lihong Liu, “The Social Life of In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ByDorothy Ko (BookReview),” Th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1 (2018): 235-238; Haicheng Wang,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byDorothy Ko (FeaturedReview),” Journalof Chinese History 2:1 (2018): 211-237. [5] 作者使用該詞,受陳愷俊對包衣唐英的研究所啟發。參見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 D. diss., Columbia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7。 [7] 劉禾引入「超符號」,是指甲方語言經翻譯成為乙方語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個別詞語,而是翻譯在異質文化所引發的意義鏈。參見Lydia H. Liu et al., The Birth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itional Theo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13. Lydia H. Liu,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13. David Turnbull,“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275. [8] 採石工從端坑礦洞中採鑿出的原石,稱之為「石料」,需要經過維料師傅的加工,即結合熟練經驗,透過觀察石料表面的紋理走向,確定其質量及石品花紋,再用錘和鑿子將可利用的「璞」從不可利用的廢石中剖離出來。剩下的璞料才是用於琢硯的原料。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1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硯家圈子核心成員的硯銘集《硯史》,由林涪雲為首的林氏族人編輯,傳世有多種鈔稿本,至民國才刊刻出版。作者全書主要引用兩種: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最早(A 本),上海圖書館藏乾隆鈔本(C 本,書中引作「長林山莊本」)次之。作者對該文本組織和版本系統分析,詳見原書附錄四(Appendix 4)。 [11]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Commod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r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4-91. [12] 晚明時期的物質文化研究,例見Craig Clunas, The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Polity Press,1991);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為代表的盛清研究趨勢及其轉變,參見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宮學術季刊》,21:1(臺北,2003),頁1-30。 [13] 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4] 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吳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臺北,1991),頁59-104;〈從嘉定朱氏論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昇〉,《故宮學術季刊》,9:3(臺北,1992),頁19-44;〈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3:1(臺北,2005),頁467-530;〈從《活計檔》看雍乾兩朝的內廷器物藝術顧問〉,《東吳歷史學報》,16(臺北,2006),頁53-105;〈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收入陳捷先、成崇德、李紀詳編,《清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19-575。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學界已指出討論宋古器物學的興起及宋仿古銅器,是士大夫與朝廷相互激盪下,為「再現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復古運動的物質表現及學術成果。參見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23:1(臺北,2005),頁267-332;《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 2012); Wu Hung ed.,Reinventing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Resources, 2010). [17] 茲就筆者所見臚列,僅供作者、讀者斟酌參考。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書評。 著作封面鏈接:http://www.washington.edu/uwpress/search/books/KODSOC.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