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刘志伟著2019年6月出版426页,68.00元━━━━
文︱赵思渊
有一种学问始终夹在两个性格如同冰火的学科之间,这就是经济史。这几年里,刘志伟教授好几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说,经济史是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他新近出版的论文集《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相当能体现这一层意思。
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史的核心议题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刘志伟教授的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研究之时间跨度也差不多经历了这个历程。他的研究更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如果明清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日渐活跃,那么这样的市场,是由怎样的力量催生出来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制度”对前现代中国的市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提问,使得“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脉络中开掘出来的那些题目与材料,可以引申到经济史源流上作重新的思考。1967年,希克斯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发表一个演讲,1969年整理为一个小册子出版,这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经济史理论》。这个小册子框定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议题。这本书中,希克斯对人类社会交换行为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习俗经济、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通常所说的买卖交易,都可以归入市场经济;很多政府行为则可归入指令经济,例如税收或者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中,这两者是相互分离的。当然,相互分离并不是说两者各行其是。事实上,在任何现代政治治理中,以指令调节市场都是普遍而频繁的。但两者的相互影响正是建立在两者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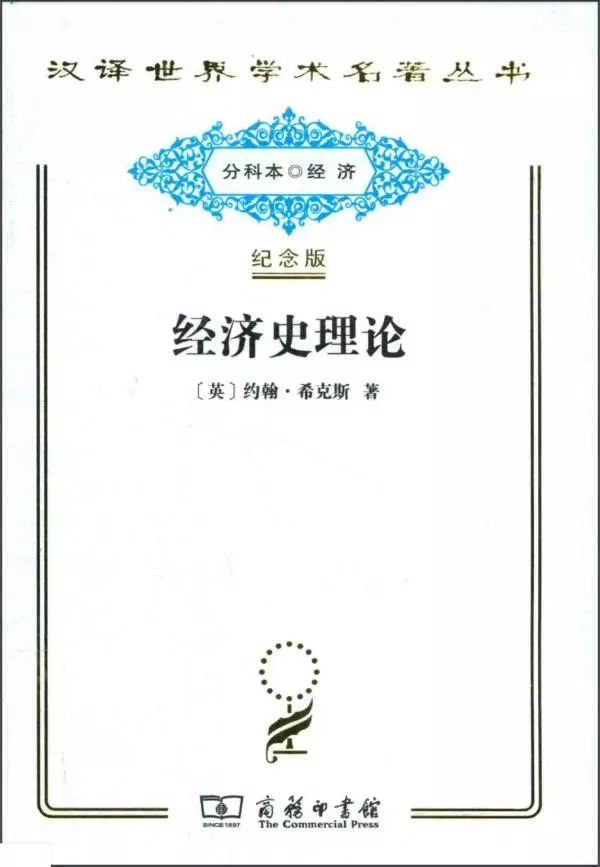
希克斯著《经济史理论》
如果观察明清社会中的市场构造,似乎也能观察到类似情形,但是,观察明清时代的经济形态与市场发展,无法将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拆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体系。有很多证据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盐法。明初为了供应北方防御蒙古的军事力量,将盐的专卖特许权作为交换,换取商人运输军事物资前往北方边境。明代中后期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大型商人集团,都与这套体制关系密切。
又比如徭役。徭役是政府征发人民义务付出劳动,这看起来是最远离市场的一种资源调配手段。但是由于徭役征发,刺激了乡村中的人民进行长距离的跨区域流动,这种流动又带来了政府管控之外的商品与资本流动。刘永华教授最近有一个研究,专门谈这个问题(《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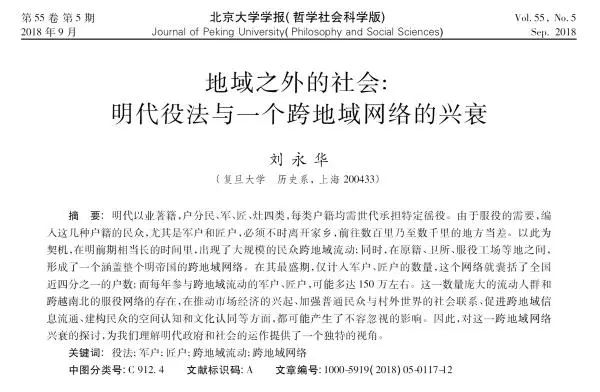
刘永华文《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
如果要解释这些问题,刘志伟教授的研究就非常重要,他用贡赋体制作为关键词,将明清时代王朝制度、市场形态、社会结构三者的演变趋势串联起来,提供了一个对明清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性解释。
刘志伟教授所提出的这个解释视角,以《汉书·食货志》作为思想的源头。《食货志》是历代正史中必备的一个志书类别,但这一体例始于《汉书》而非《史记》。《汉书·食货志》开篇说:
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仁曰位,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仁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汉书·食货志》
刘志伟教授特别强调,作为中国正史中的第一个《食货志》,《汉书·食货志》表达了这样一种财富观念:所谓财富,是天地生出的自然物,食货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占有和分配这些自然物。这样的财富观念与现代的“经济”概念有所不同,“经济”的概念是生产专业化分工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财富增加(第8页)。
如果我们将《汉书·食货志》所表达的观念视作中国历史上帝制初期的政治理念的总结,那么,此后历代王朝的“食货”之制都可以在这样的思想源流中观察。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框架中,中央王朝所面对的社会总财富是相对固定的,人的劳动是将自然财富(天地之大德)转化为社会财富,而非创造财富。因此,传统中央王朝的赋役制度,其基本意图是如何面对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总财富,基于帝王(也就是《易》中所说的“圣人”)的需要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进行调节。因此,《汉书·食货志》才会将“均”与“贫”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贫”是“不均”的结果,而非生产力不足的结果。
如果说《汉书·食货志》距离刘志伟教授这本论著所主要论述的明清时代太远的话,翻开《明史·食货志》,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句话就是:
《记》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
这样的观念与《汉书·食货志》一脉相承,与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的理念则存在显著的分歧。现代经济学中,人的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基本的预设。因此,财政是调解资源配置的工具之一,通过财政制度设计的引导,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扩增。
这样的差异意味着,我们观察传统中央王朝中的商品经济与市场形态时,必须更为谨慎。《汉书·食货志》在谈到作为政治理想模型的“尧舜禹”时代时写道,大禹在治理洪水、划定九州之后,曾经“各因其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乂”。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食货”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这很显然不是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只是自然资源的控制和获取的一种机制”(12页)。“懋迁有无”显然是市场交换,而“赋入贡棐”当然属于贡赋,也即希克斯所说的“岁入经济”之一种。在现代经济学中属于两个体系的交换行为,在传统中国中央王朝,同属食货之制。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讨论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运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家权力,而是由贡赋出发去拉动市场”(19页)。
“食货经济”是明清时代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市场是嵌入于贡赋体制之中的。在我理解,这应该是多年来刘志伟教授的系列研究一直试图表达的意思。因此,这本论著中,有三篇文章最值得读者注意。其一是1990年发表的《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其二是2010年发表的《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其三是2017年发表的,作为本书《代序》的《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的经济史》。
《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发表之时,“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议题。在这个研究中,刘志伟与陈春声强调与清代市场机制相关的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第二个是“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
所谓“非市场导向性”,是强调清代的小农在制定生产策略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以及相应的成本核算为导向。这与当时小农深深地涉入商品经济、市场极为活跃的现象正成为鲜明的对照。这种说法与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小农的研究有相通之处。斯科特也极为强调,在繁荣的商品经济的表面下,小农的生产经营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要考虑到各种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从而有所谓“道义经济”。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志伟教授他们应当已经了解斯科特的研究。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
农户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和群体和谐为终极目的,同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是互为因果的。在这种以伦理关系维系的组织内,个人的经济角色往往随其亲属角色而定,而亲属关系中的角色期望又常常使个人注重人伦关系,把经济利益置于从属的位置,因而抑制着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并在一切经济关系中以特殊性原则取代普遍性原则。故此,集组织生产与消费职能于一身的家庭经济体本能地否定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排斥市场导向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群体内部,还潜在地否定独立的个人权利,故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内部关系也就不是一种基于个人独立经济利益的契约和交换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以道德价值维系的人伦关系。(172页)

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至于此文所说的第二个现象,则显示出刘志伟教授对明清经济形态的一贯思考。虽则表述不同,但与他在2017年围绕《汉书·食货志》所讨论的问题相通。他们认为:
这里所谓的经济导向性,是指一种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的价值取向。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重要差别之一,在于近代社会以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活动中超越个人感官享乐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成为价值观体系和物质活动的基点。
具体的市场交易活动,对于每个具体商人来说,当然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机会,但就整体而言,市场活动只被视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途径,而不是实现国民财富增殖的必要手段。……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价值取向,反而为这种选择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是商品经济发达、商业资本雄厚的地区,捐纳捐输的数量也越多。(174页)
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史中影响最大的学术争论显然是“大分流”以及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所以2010年刘志伟教授与陈春声教授的合作研究对这个学术浪潮做了回应,也就是《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美洲白银是中国经济史中的老问题,也是《白银资本》的讨论重心。从十六到十八世纪,数以千万计的美洲白银输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史最为显著的一个经济发展指标。在近代经济学的逻辑中,如此巨量的白银输入,不仅将显著改变商业、消费、城市经济,也应当深刻影响生产部门中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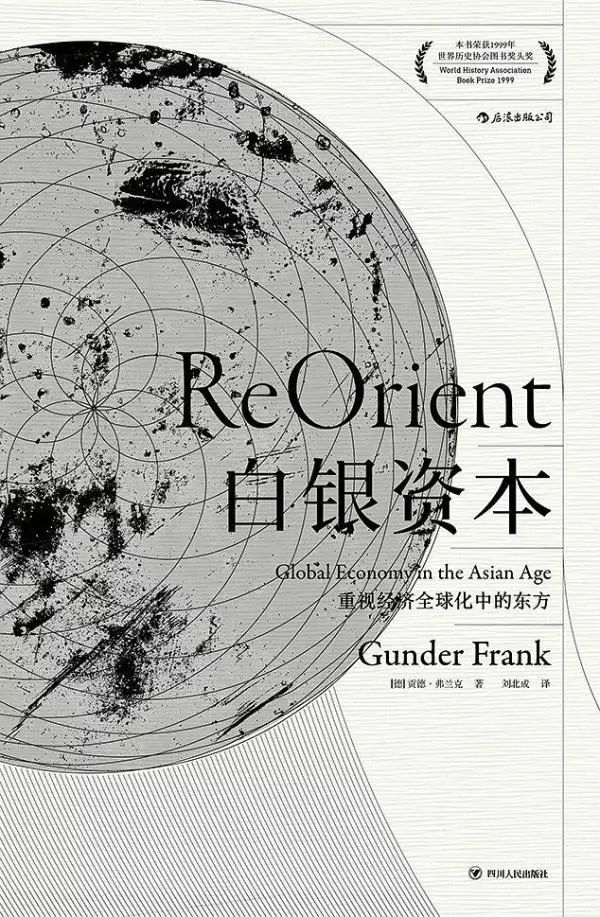
弗兰克著《白银资本》
《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中,两位教授面对经济学的逻辑提问道:为何如此巨量的白银输入没有造成清代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解释这个疑问的重要线索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朝廷、地方政府、百姓之间的关系,都以白银为中介运作。这意味着,明后期直到整个清代的国家机器与官僚体制,都要依赖来自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才能正常运转。“这些白银通过市场流通,被吸纳到财政运作体系中,又通过财政支出和国家与官僚队伍的消费,再进入市场流通,成为拉动市场的一种重要力量。”(291页)“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地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所以,十八世纪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299页)
到2017年,刘志伟教授的提问更为明确,中国王朝时期的贡赋体制经济,应当视作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阶段还是一种经济类型?(第4页)这个提问将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些长期争论同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勾连了起来,我在开篇已经引述,不再赘论了。
明清时代有着显著的市场发展、规模庞大的货币流通,以及勃兴的市镇经济。这些都曾经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也相当程度改变了叙事中国历史的方式,但是也许也形成了某些遮蔽。2008年葛兆光教授与王汎森教授的一个对谈中曾经提到:
比如说“资本主义萌芽”,看起来完全是照套欧洲历史。但是,它一方面又发掘了很多历史资料,比如在这个聚光灯下,一大批原来不被注意的史料,诸如契约、文书、乡村的东西,开始被发掘出来。另一方面是遮蔽了很多历史现象,把很多旧时代的历史资料给压抑或者消耗掉了,让我们只注意到江南、城市、商业,但是那些后世看来不能“与时俱进”的地区、现象、历史就被忽略掉了。(《重访历史:寻找“执拗的低音”》)
家范师曾经针对“大分流”的讨论有过一个评论,也有类似的意思:“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为‘二兰’(弗兰克、彭慕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帮过倒忙。”(王家范:《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

王家范著《史家与史学》
如何将市场放回明清社会经济的历史情景中?如何重新描绘嵌入于贡赋体制中的市场或者说“食货经济”?最近几年在盐业与徭役方面的几个新研究,也许可以启发我们打开新的思路,对刘志伟教授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也是有裨益的检验。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话题应该是明清时代的盐法。盐专卖制度与商人资本积累的关系向来是明清史中引人注目的现象。黄国信教授最近的著作中由此引申,明代中叶的纲法改革之后,盐商在盐的生产与盐课征收中都事实上具有代理人的身份,市场也由此繁荣扩大。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运作又嵌入于市场,对市场的运作具有控制力。黄国信教授将此关联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再分配型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中,国家充当中心重新分配国民财富(《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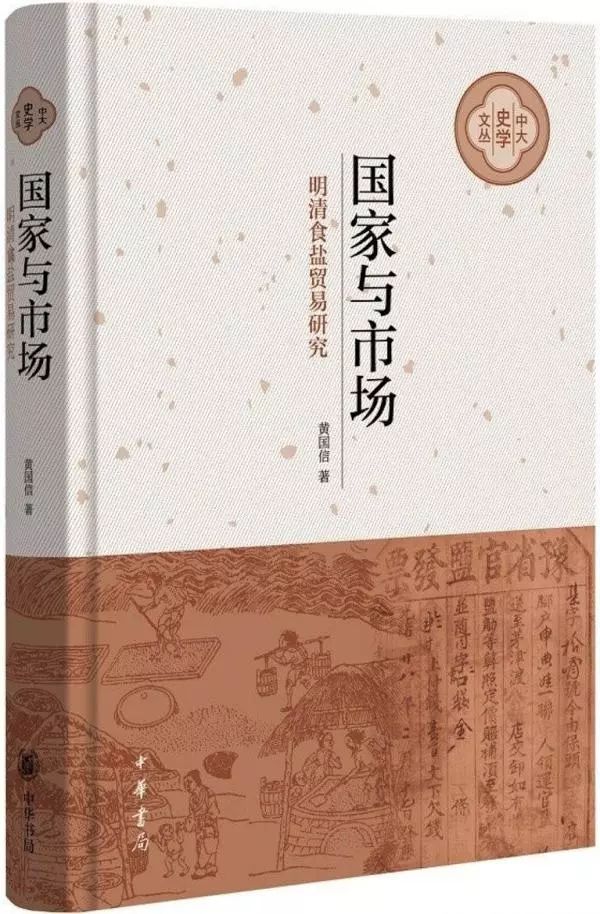
黄国信著《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研究是刘永华教授所提出的对明初役法流动空间的假设。刘永华教授指出,明初所制定的军户、匠户应役制度使得大量人口在一个非常广大的空间尺度中流动。这虽然是被迫的流动,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为了提供后勤供应形成的人员与物资流动,其中人员流动可能高达上百万人次。由于明初实行“画地为牢”的里甲制度,这样庞大的人员流动规模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其实有很深的冲击力。这也意味着,由于徭役制度的拉动,看似封闭的十五世纪乡村实际上有着活跃而空间尺度广大的人员与物资流动网络(刘永华:《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
赋役制度还可能影响了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集聚与商品交换。吴滔教授对明代嘉定棉布折纳漕粮的研究显示,不同区域的赋役负担类型的差异,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的商品交换,明代嘉定地区的一批棉布专业生产市镇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兴起的(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十四至二十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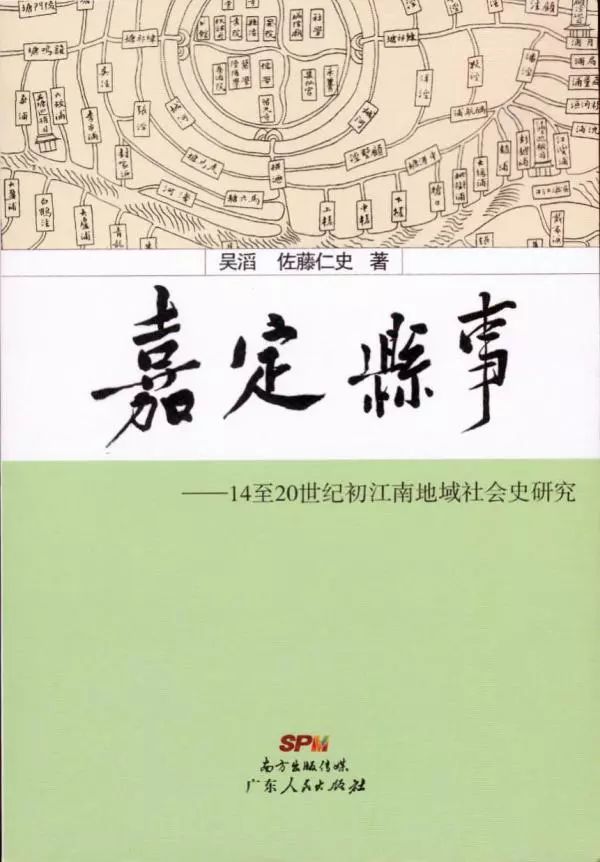
吴滔、佐藤仁史著《嘉定县事——十四至二十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
回到本文开篇的话题:经济史是沟通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现代经济学精密复杂的研究,仰赖于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行动模式的一些基本预设,如同数学定理推导中的公理。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中,恐怕并不存在永恒的公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社会科学重新检视作为研究前提的一些基本预设和基本概念,比如何为市场?又如何理解货币与资本?
回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创始阶段,那些最重要的学者往往都具有经济学或社会科学背景,这不是偶然的。当那一代经济学家面对中国社会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经验,经济学的解释力及其理论的“射程”也都将受到限制。
刘志伟教授的这本论著所收录的论文写作时段跨越近四十年。这四十年中,不论中国的经济学或经济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都经历了面目焕然的变化。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不同世代,甚至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社群来说,学术术语体系可能是大相径庭的。这也是为何我认为前述的三篇论文是理解这本论著的一条关键线索。这三篇论文曾经面对不同世代、不同学术脉络的议题与术语体系,但我们能从中感觉到连贯的提问,这个提问总是在检验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
从这条线索发散出去,也就有可能将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同时代背景、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学术脉络的研究勾连起来,将其视作一个累积性的学术领域,而非割裂的、各自异质的研究题材的拼合。刘志伟教授在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经济史前辈百年诞辰时曾经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老一代学者的研究在过去一段时间,被贴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标签掩蔽着其学术上真实的价值。”(404页)在刘教授看来,这些研究尽管也使用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历史概念,但留下了坚实的实证研究,为此后经济史提出新的问题与方法奠定了基础。因此,刘志伟教授认为“在这个方面,经济所老一辈学者的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当时有着引导我们走出教条主义史学的意义,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对今后的研究有启发价值的思路。”(406页)
经济史始终身处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经济学理论迭代如传舍积薪,后来者居上;历史学则始终对任何抽象理论都抱持怀疑警惕的态度。经济史的修习者,总是能感受到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刘志伟教授的这本新著提供的是一个经济史学者近四十年的探索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许是,经济史需要不断回到经济学的上游,回到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的内部,以历史的眼光提出检验与修正。这也许是经济史这个学科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所作出的智识贡献,也是她的根基。
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