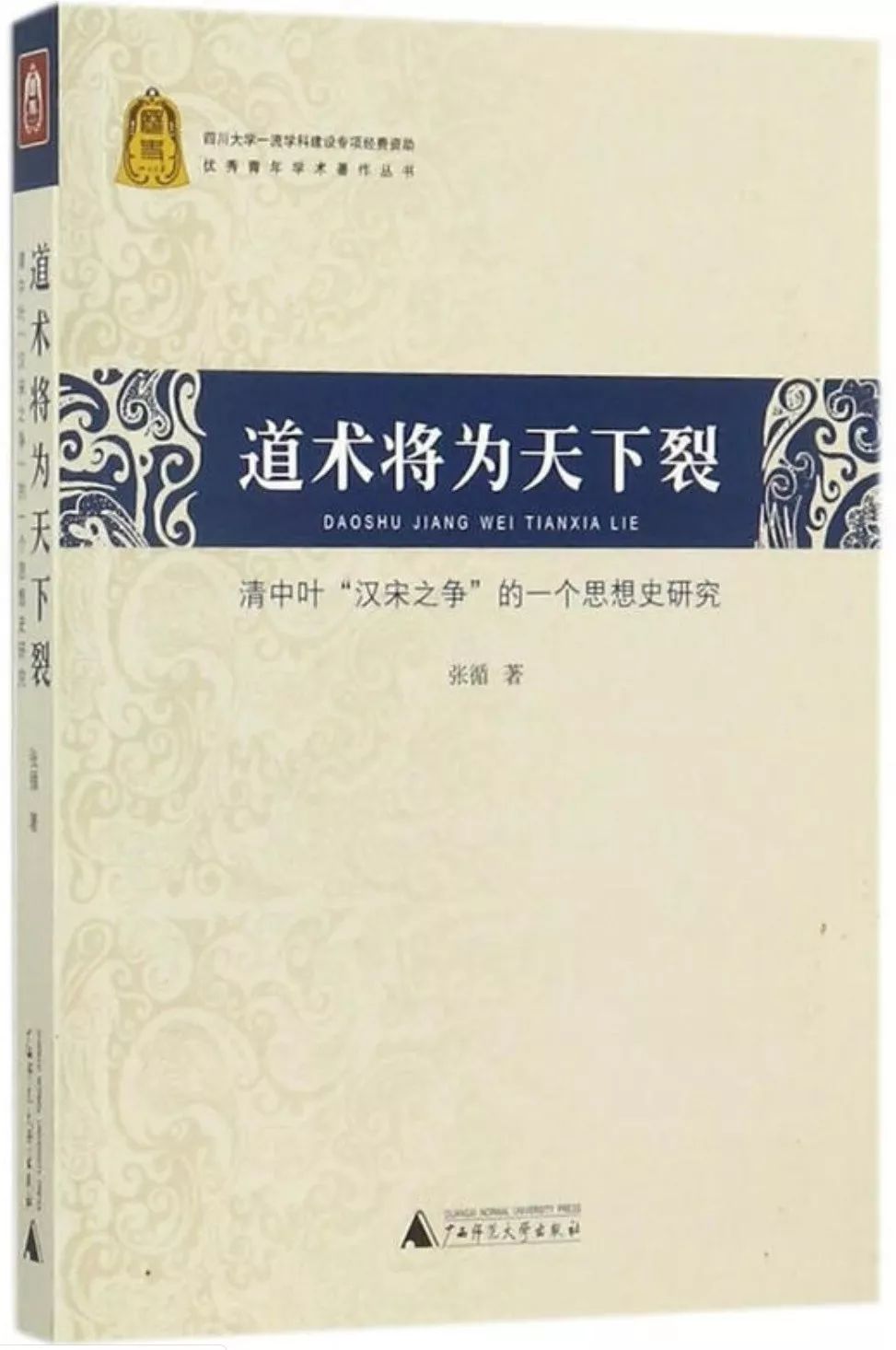
道术将为天下裂
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
张循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出版
304页,32.00元
━━━━
文︱钱 煦
在过往以人物和学说为中心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中,“谱系”总显得过于清晰、整齐,好像提到宋代就不得不说理学、朱陆之辨,提到清代就不得不说“汉学”与“宋学”,自然也就绕不过“汉宋之争”。
从上世纪初梁启超讲汉学兴于“反理学”,到世纪末余英时用“道问学”、“尊德性”重述汉学与宋学,“汉宋之争”似乎贯穿了数百年,争论纷纭。应该说,“汉宋之争”一面成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常识,一面也成了历史学家不断试图建立、打破、汰换的对象。只是,大多数对“汉宋之争”的叙述大多是解释,为何有“汉宋之争”,汉学、宋学所“争”为何。
但是,各位读者只需要翻读所谓的清代“反宋学”之最高代表著作——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恐怕都会对“汉学”与“宋学”泾渭分明的印象感到疑惑。就像葛兆光说的,所谓的“戴震印象”实际上是后人藉由前人层层论说,在眼睛上戴眼镜,又在眼镜上蒙上有色玻璃纸而形成的。换句话说,当时人的汉宋之别未见得如后世所见,区隔分明。可是“争”的印象何以产生?清代的“汉宋之争”到底是什么?这恐怕不能仅仅停留在溯源地去寻找汉学、宋学的差别,更需要考察汉、宋学倾向出现以后,层层印象如何叠加。
王汎森在《思想史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提醒说,讨论思想史应当留意了解“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避免将“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当作“历史的现实”。确实,在当世有影响力的思想,从来不是瞬间即逝的,相反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引起或正或负的反复回响。回到清代中叶,如果说汉学的兴起、与宋学的对峙,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那么反过来,“汉宋之争”对汉学与宋学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张循在《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张循说“汉宋之争”是“弥漫一世的风气”。就像清人汪士铎说的,“无汉宋之意见难”。这股如同漩涡一般的“风气”一旦形成,一般的读书人也好,专业的学人也罢,都不免被卷入其中,难以挣脱。这股风气有如龚自珍说的“万形而无形”,又像刘咸炘讲的“时风”,成为一种社会中的氛围、时髦,同时也成为了问题。怎么能捕捉这股“风”?张循从最普通的读书人谈起。
对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举业”,毕竟科举意味着个人与家族的生存和希望。但书中就说,即便“乾嘉时的读书界仍是举业的世界”,却依然阻挡不了“汉宋之争”成为“广泛流播于读书阶层的一个时髦话题”,无论对于“汉学”或“宋学”的学理有无高见,人人都热衷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因为科举对于所有的知识人,都是必经的历练。
以现代目光回望,科举代表着理学的价值,似乎与汉学/考据学格格不入。所以,在不少人的眼中,这种追逐“时髦”的背后,多少带有逃避的影子,就像钱穆等论说“汉学”之兴起,常说是因为科举以《四书》取士,读书人“久则厌而思遁”。但是这种观点,实在是后世“倒放电影”地由果求因,好像当日的读书人早已厌倦了科举、理学。这种人虽然不少,可是张循在书中就指出,实际上久习程朱之学,并不必然会味如嚼蜡,也有人甘之如饴,甚至不少人因埋首其中而成为了“宋学”的同盟。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之争”之所以在读书人圈中流行成“风”,正是因为科举本身。书中已经提到,清代的科举考试,从秀才到进士,一般都有三场。虽然头场必考“四书”,但二三场则有五经义与策论,“答题中体现出汉学色彩成为一种时髦”。所以,多数读书人的科举经验,让他们得以接触汉宋之学,又知晓汉宋之争。有些人因此而产生了对汉学和宋学的明确态度,但更多人是实用的态度,所谓“当宋则宋、当汉则汉”。这样一来,“汉宋之争”的风气,就展现出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在“不入流”的读书人之中,他们需要的是与科举相关的汉学与宋学;一个层次则是在专业学人之中,他们研读的则是学术意义上的汉学与宋学。
虽然笔者不免好奇这两种层次的“汉宋之争”又有着怎样的融汇流转,就好像不同层次的酒精会叠加出何种鸡尾酒。但是,张循却直接转向了专业学人的研究,很显然是因他所使用的“思想”,乃是取其狭义,更具体来说就是儒学的理论,而将氛围、时髦看成是社会文化史的问题。所以,他接下来的考察,不再将“街头混战”纳入视野,而要从“高手过招”中考察“儒学最新的发展与特性”。
二
如果说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汉宋之争”是时髦,对于专业的学人来说,“汉宋之争”恐怕是一个严肃的、现实的学术问题。因此,若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不少宋学家正是做此选择),那么这股“汉宋之争”的风气多少会扰动心智、影响思想。张循就提到“汉宋之风”席卷下的专业学人圈中的三种变化。
以所谓的“汉学家”来说,清朝的“汉学”指的并不是“汉儒(代)之学”,而是借助汉儒所擅长的训诂方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清代特色的考据学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汉学家来说,师法“汉学”并不代表必然贬斥程朱。应当说,于当时人来说“尊崇宋儒”与“师法汉儒”这两者,本身并不感到矛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循特别希望指出的地方:近代以来将清代的“考据学”视作为理性的求知,实际上忽略了“经学”的实质,仍然是“道德”的学问。
所以,对于汉学家们来说,所谓的训诂与考据,本义是由考据而通义理,但是汉学家们对“穷经”的追求和“旁搜博览靡所不通”的风格,使得以“穷经”为旗帜的汉学,并且在此道路上愈行愈远。最后所导致的是,“汉学之争”不仅流行于外,形成“考据”与“义理”的对峙,在汉学的内部也形成了“穷经”与“进德”的相对力量。
相应的,作为“宋学家”亦不可能总以旧的套路,来坚守、维护程朱理学,就在汉学愈加强烈地转向汉学的同时,试图维护程朱理学的“宋学家”,不得不参与到“汉宋之争”中去,他们的学术理念不断接近考据学,而与原本的“宋儒(代)之学”越来越分立。这一点也是好理解的,就是胡适所讲的“凡攻击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响最大的人”,正因为要与汉学家争胜,所以这些宋学家在技术、理念上都得到了发展,恰如文中着重分析的方东树一样。
透过书中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汉宋之争”的双方,随着“斗争”之风的弥漫,不断将自身的立场清晰化,也受到对手的影响而出现新的理论发展。但不论如何,“汉宋之争”的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汉学的“技术优势”显然高于宋学,所以即便提出汉宋调和的陈澧,也并不是在考据和义理中无所偏执,而是偏向于考据,只是认为义理亦应追求。
或许,重新来看这股“弥漫一世的风气”,与其说是“汉宋之争”,倒不如说是“汉学之风”。当这股新的学术风气弥散开来,身处其中的个体无论赞成抑或是反对,只要无处可逃,都无力阻止这股“风”,只能随之而动。
三
张循在整本书的设定与写作中,大有“截断众流”之意。他似乎有意避开“汉宋之争”如何兴起的问题,只是援引了龚自珍说的“其运实为道问学”,说明当时正是汉学兴盛之际、当运之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跳脱出“汉学兴起”问题的泥潭,而将关注点紧紧地固定于“汉学之争”与具有清代学术特点的“汉学”与“宋学”之上。可是避开了“汉学”兴起的背景与诉求,似乎又使得“清代特性”不能得到充分的阐明,而使一些细节中似有未尽之意。
比如在文中他举例说,“清代学人常常控诉宋明尤其是明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由此说明以“德性”为目的与归宿,发展到极致所带来的流弊。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人批评中前期的人“束书不管”的例子颇多,这与明代的学术发展显然颇有关系。更早的,宋代的苏轼就曾说当时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过苏轼抨击的是热衷科举的时人罢了。换而言之,何以是清代形成了弥漫性的“汉学之风”?这背后所代表的学术、政治与社会,与清代的儒学思想发展,真的可以截然分开吗?
张循在开篇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即《四库全书》的编纂,意味着清朝官方对汉学的默许乃至鼓励。章学诚也曾经欣喜地说过,“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所以,今人借助《四库》很容易就可以“闻见广于前人”。《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情。可是闻见广于前人会直接鼓励“汉学”的兴起,却并不一定。这可能还是要回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学术转型中,也就是“风起之时”,再重新加以考察。
这里我们举一个史学上观察到的现象。明代前期以来大多人认为史书应当力求简要,不能因繁冗的史实记载而影响对“理”的阐述,可到了汤显祖就认为,前人多认为杂芜而他恰认为太过简单,史事不必担心记载过多,而要避免记载不足。所以在明代的后期,对于史实、知识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转换,而这种知识观念的转化,又如何融汇到时代的风气之中,似又与经学的发展有共伴的关系。
总的来说,在众多的有关“汉宋之争”的研究之后,《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著作。张循在书中试图捕捉出这股将不同阶层纳入的“风气”,也正是透过对思想史中的主音与低音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知识人实际上都难免被卷入这股时代的漩涡。而书中环环相扣的论证,则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紧张、焦虑、关注、挣扎,尤其是其中多重张力的分析,也无疑会给今天的读者提供新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