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2015年12月中旬,筆者應邀到上海參加由華東政法大學主辦的《第五屆〈出土文獻和法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會期12月12日)。會前的12月10日由王沛教授主持,在華政交谊楼圆桌会议室與華政和上海其他高校的學者進行了一場題爲《西周的政治制度》的全開放式座談。[1]作爲這個講座的引導,作者就西周琱生諸器及西周金文中的稱名原則作了一個20分鐘的簡短講演。這個講演后經華政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黃海先生整理,以《西周宗族制度下的“稱名區別原則”》為題(下簡稱《稱名原則》),發表于2016年2月19日上海《文匯報》。[2] 2017年5月經由巴黎至北京,受徐少華、陳偉兩位教授好友之邀赴武漢大學訪問,遂于5月10日由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主辦,發表《周代金文称名制度再议:论楚地青铜器上所见妇女称谓》的專題講演。這次講演中,筆者用較充實的資料進一步討論上述的“稱名區別原則”,並重點討論了周代南方一些小國之間以青銅器同媵和隨嫁的現象,我稱之爲“金文稱名區別原則III”。[3]2016年6月7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刊出了吳鎮烽先生題爲《也談周代女性稱名的方式》一文,對筆者倡導的西周金文女性稱名原則提出了質疑。[4]當然,吳先生並不知道筆者後來在武漢大學和吉林大學就此問題作的詳細論述,而筆者也至今夏(2017年)9月回到紐約也才偶爾看到吳先生的大作。拜讀之後,感到吳先生所擧資料翔實,拓寬了這個問題研究的視野,值得讚賞。同時,吳先生對我早先的論述有不少誤解,或者說對一些銘文的理解也有偏差之處。但更重要的是吳先生文在論證邏輯上有一些很明顯的問題,這導致我們對同樣資料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鑒于《文匯報》發表的短文只是20分鐘講演的整理稿(談到女性稱名的部分約2000字),其中只能選擇最典型的例子來説明金文稱名原則,也有感于這個問題對理解西周社會制度的重要性,故謹草成此文,作爲對吳鎮烽先生的答復,也希望促進學術界對這個議題的進一步討論。 媵器中父親對女兒的稱名: 筆者在《稱名原則》中提出的西周女子稱名原則是基於“姬姓”和“姜姓”為兩大婚姻集團的設定(這符合西周社會的現實)。每個集團包括若干個宗族(姬姓包括宗族A、C、D;姜姓包括宗族包括B、E、F等),不同姓的宗族之間分別相互通婚。姬姓女子从A宗族嫁入了姜姓的B宗族,她的父母为她作媵器時应该称呼她为B姬,即称她夫家的氏名(即宗族名)和自己的姓;同理,嫁入E宗族的女儿称E姬,嫁入F宗族的女儿称F姬。這樣可以把嫁入不同宗族的女兒相區別(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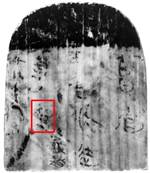 圖一 吳鎮烽先生文中首先全面羅列了金文中有關父親對女兒稱呼的各種形式,然後據此來質疑我在《稱名原則》中所主張的上述原則。他的分類的方法是,只要是某些稱名形式在因素或因素的排列順序上略有差別,就算一類。根據這樣的分類方法,他將西周金文中父母為女兒鑄造媵器對女兒的稱名方式分爲如下10種: 1、婿家國氏+自家的姓(如蔡侯鼎等); 2、婿家國氏+自家的姓+女兒名字(如魯伯愈父鬲); 3、婿家國氏+女兒姊妹間排行+自家的姓(如曹伯盤); 4、婿家國氏+女兒姊妹間排行+自家的姓+女兒名字(如楚王鼎); 5、(缺,文中4下面直接是6;不知吳先生說的第5種在哪裏?); 6、僅稱其姓(如楚季苟盤); 7、僅稱其名或字(如夔膚簠); 8、姓名連稱(如魯伯愈父簠); 9、姊妹間排行+自家姓(如蔡侯簠); 10、姊妹間排行+自家的姓+女兒名或字(如曹公簠)。 基於上述排比,吳先生作出了如下論斷: 據統計,《銘圖》與《銘圖續》中父母所作媵器中對女兒的稱名共230條,[5]除去情況不明者25條外,其中列舉婿家族氏者93例,不列舉婿家族氏者112例。不列舉婿家族氏者佔到總數的一半還多。李教授說“如果有一姬姓女子從姬姓的A宗族嫁入了姜姓的B宗族,她的父親爲她作器的話應該稱呼她爲B姬,即稱她丈夫的氏名(即宗族名)和自己的姓,因爲這個父親可能有其他女兒同時嫁入了別的姜姓宗族,如此稱呼方便父親區分。若以自己(也就是女兒母家)的氏名稱之,則可能會有許多A姬,無法區分,故應以其丈夫的氏名稱之。”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固然可以如上所述第1—4種方式,用丈夫的族氏和自家的姓(包括帶有排行和女兒私名)來稱呼出嫁的女兒,但也可以像第6種和第7種方式,只稱呼女兒的名或字,或者只用自家的姓和女兒私名,同樣也可以區別,不論有幾位女兒,不論她嫁到哪個國家或宗族,都不會造成混亂。同理,第8種和第9種方式也一樣。如是姬姓,用孟姬、仲姬、叔姬、季姬也就區別了∙∙∙∙∙∙ 所以,不應把加載女兒丈夫家族氏名看作是宗法制度下女子稱名的一條原則。 吳先生對資料的一一排比對於我們摸清金文中父親對女兒稱名的變異幅度當然有所幫助。特別是吳先生窮一生精力搜集和整理周代金文和青銅器,對有關的資料可以說如數家珍,這點應該敬佩。但是,問題是這樣的排比對解決目前的問題究竟有什麽意義,或者說它能否成爲質疑筆者倡導的“稱名原則”的真正“證據”? 我們先說比率的問題。吳先生認爲金文中列舉“婿家族氏”(即筆者言“夫家氏名”)者93例,不列舉者112例,不列舉者中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稱名形式,因此以夫家氏名稱名的原則不存在。這裡,我們可以先擧一個英語世界大家熟知的例子:半杯子的水放在那裏,到底它是“半滿”還是“半空”?兩者都對,但是兩相抵消,他既不能説明杯子是滿的,也不能説明杯子是空的(圖二)。換言之,吳先生所給出的比率是一個在邏輯上不能成立的“證據”。他既不能證明列舉“婿家族氏”是一個規律,也不能説明不列舉“婿家族氏”是一個規律。所以,他提出的這個比率對論證此問題完全沒有意義。但是,吳先生上述論證的真正問題還並不至於此,而在於這“空”的半杯究竟裝的是什麽?  图二 如吳先生所言,他所講的父親對女兒的10种稱名形式,可以以並不存在的第5條為界分爲兩組:第一組第1-4种有繁有簡,但是万變不離其中,即在筆者主張的“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的基本結構之上增加了女子的私名或排行。這當然是可以允許的更複雜的一種稱法,吳鎮烽先生也認爲他們和筆者主張的原則一致。這當然不能被用來否定“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的基本原則。就像西周晚期金文中有類似“鄭井叔康”的男性稱名,包括地點+氏名+排行+私名的四個因素,稱“康”並不能否定鄭井叔的存在,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相對于第1-4种的“繁”,第6-10种或只用女子私名,或用排行,則是幾種簡化的稱名形式;特別是第6、9、10种形式仍保留“自家的姓”,只是簡略去了“夫家氏名”,這些都是允許的,與稱名原則並不矛盾。就像我們現代社會中人或單位都可以有簡稱或暱稱,但我們不能因爲簡稱或暱稱的存在而否定正式名稱的意義。關鍵是應該用正式稱名時究竟怎樣稱,這才是要點所在。西周社會中貴族嫁女根據自己或女兒夫家的經濟或社會地位乃至親疏程度等社會因素,作爲父母當然有權決定是否用一種比較簡單的稱法,或是採用一種正式的或更複雜的稱法。[6] 但是,我們不應該將這些簡稱形式的存在當作否定“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的稱名原則的證據,因爲他們並不能構成真正的反證(見下)。 但是,吳鎮烽先生論述中最大的問題是他提出了一種不符合邏輯的比較:即列舉“婿家族氏”的金文數量vs.不列舉“宗族氏名”的金文數量(儘管他文中說的是“不列舉婿家族氏者”,檢查他文后注[5]所列的比率就知道,這實際指所有“不列舉宗族氏名者”。[7] 雖然“不列舉宗族氏名者”的概念可以包含“不列舉婿家族氏者”,但如果把前者作爲比較的基準和“列舉婿家族氏”者相比,那相差就大了。從分類學上講,這就類似把“屬”的概念和屬於“屬”之下的某個“种”的概念相比較或並列,這是典型的邏輯錯誤。符合邏輯的比較必需是同質或同級的兩件事物的比較。在這個問題上有效的比較只能有兩個:1)不列舉宗族氏名者vs.列舉宗族氏名者; 2)不列舉婿家族氏者vs.列舉婿家族氏者。也就是說第2個比較必需是在列舉了宗族氏名的所有金文的範圍之内作高一個層次的比較,這才是符合邏輯的同級比較原則。在這樣符合邏輯的比較中來看,吳先生列舉了93例“列舉婿家族氏者”,而且93例中均包括了“夫家氏名”和“自家的姓”兩個基本要素;相反,他卻提不出一例父母為女兒作媵器稱“宗族氏名”但卻不是“婿家族氏”的。換言之,在現有230條父母為女兒作媵器稱名的例子中,有93條之多包括“宗族氏名”,而稱女兒“夫家族氏”(即吳先生所說“胥家”)和“自家的姓”的比率是百分之百。這怎麽能說“夫家氏名”+“自家的姓”不是一個原則呢?[8] 究竟有沒有原則? 如上所述,吳鎮烽先生的論述並不能推翻父母嫁女作媵器稱“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的稱名原則。相反地,他所提出的資料在正確分析的情況下反倒證明了這個原則的存在。所謂“原則”就是形成某种現象按一定的形式重復出現的規則,而“原則”的存在往往是以“原理”為基礎的,也就是說是與對某事物的一個整體的符合邏輯的解釋聯係在一起的。筆者對於西周金文中各種稱名原則的研究正是這樣的一個實踐,它以理解西周社會宗族制度為目的。原則的真正意義,不在于它在每個實例中被每個人提到或墨守,而在於原則不能存在反証,也就是說只有足夠的反証才能推翻原則。具體到父母作媵器對女兒的稱名問題而言,他們當然可以選擇不用宗族“氏名”,甚至也不用“姓”的簡單稱名形式,也可以採用加上私名、排行乃至身份的更爲複雜和繁瑣的方式,這些變化都在允許的範圍以内。但是,只要他們提到“氏名”,那就必須用女子夫家的氏名,在提到女子“姓”的時候必須是“自家的姓”,這就是原則。要想推翻這個原則,吳先生必須找到一定數量的反証,譬如父母做的媵器中對女兒用如“父家氏名+父家的姓”的稱名實例。遺憾的是,吳先生並沒有找到一個這樣的例子。 下面我們看看吳鎮烽先生對筆者提倡的其他幾個稱名原則的質疑,在這些論述中他均採用了與上節相同的論述方法,即簡單羅列各類稱名的種種形式,再以此繁簡變化幅度為依据來質疑筆者提出的相關稱名原則。因此,這些論述的邏輯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此筆者不再一一指出。下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有關銘文的解釋及其意義方面。 首先,我们看丈夫對妻子的稱名,筆者提出的主要稱名原則是:丈夫對妻子的稱名與上述父親對女兒的稱名正好相反,用妻子“父家宗族的氏名”和“父家宗族的姓”。即把來自姬姓A宗族的妻子成A姬,來自C宗族的稱C姬,來自D宗族的稱D姬,依此進行區別。吳先生則是把丈夫對妻子的稱名分爲六种,認爲其中的1-2种稱名形式符合筆者講的原則,3-4則和筆者提出的原則相反。至於5-6种屬於只稱妻子姓或姓加排行的簡稱(類似上節父母對女兒稱名的第6、9种);如上所述,這不能構成任何證據。關於第3种,吳先生擧了虢仲鬲,銘“虢仲作虢妀尊鬲”,應為虢仲為嫁到虢國的妀姓女子所作。與此同銘的實際上還有出自三門峽2009號墓的“虢仲作虢妀寳盨”。該墓出土的四十餘件銅器為虢仲自作自用之器,唯有“虢仲作虢妀寳盨”體型較大,顯然不屬一套。關於“虢妀”與墓主虢仲的關係過去在學者閒一直有爭議,有人認爲她可能是虢仲的兒媳,也有人認爲她更可能是虢仲之母;虢仲作祭祀母親之器帶入自己墓中也屬於自然。總之,沒有證據表明它一定是丈夫為妻子作器。用這件本來就不確定的銘文來質疑常見的丈夫對妻子的稱名原則,它作爲證據的資格首先是應該受到懷疑的。關於第4种,吳先生擧1983年河南光山縣寶相寺上官崗磚瓦廠墓葬出土“黃子作黃孟姬行器”,見於盤、匜和罐三件器物。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同墓出土的另外十二件銅器銘文為:“黃子作黃夫人行器”或“黃子作黃夫人孟姬行器”,這是墓中的絕大多數。很顯然,“黃孟姬”實際上是“黃夫人孟姬”的簡略。在這12篇銘文中一致強調的是“孟姬”作爲夫人的身份,這才是關鍵。因爲要説明這個身份,所以纔有“黃夫人”的稱法。也就是說“黃”在這裡修飾的是“夫人”,而不是“孟姬”。因此,這也是一個不恰當的特例,它不足以推翻丈夫為妻子作器稱其“父家氏名+父家的姓”的原則。 筆者提出的兒子作祭器中對母親的稱名原則是:如果是姬姓的女子嫁入E宗族的话,他的儿子称呼她便是E姬,儿子和丈夫对她的称法是完全不同的。吳先生則排列了八种形式。這乍看起來資料翔實,但實際上和本論題有關的只有第1、2种;其他均不包括“宗族氏名”,絕大多數也不包括母親的“姓”,因此與本議題沒有直接關係。第1种形式為“自家國氏+母家的姓”,這正是筆者《稱名原則》中所主張的兒子對母親的稱名原則。第2种形式是“母家國氏+母家的姓”,這和筆者主張的兒子對母親的稱名原則相矛盾。吳先生給了兩個實例:1)伯 關於女性作器中的自稱,和她儿子一样,称她丈夫家的氏名和自己的姓。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吳先生排列了共計20种稱名形式,認爲其中只有第1)“夫家國氏+父家的姓”和2)“夫家國氏+姐妹閒排行+父家的姓”兩种形式符合筆者講的女性作器中的自我稱名的原則。因此,他下結論說這不是必須遵守的原則。其實,與筆者提出的原則符合的尚有第6、7、8、18幾種形式,這些均是在稱“夫家氏名+父家的姓”的基礎上再加上“父家的氏名”,實例如“蘇衛妀作旅鼎”和“邾秦妊作羞鬲”等。如前文已述,這些例子具備了女子自作器稱名原則的兩項基本因素,和第2种形式一樣,應該被看作遵循稱名原則的較複雜形式。第3、4、5种形式中女子同時稱“父家國氏”和“父家的姓”,是真正的反證資料,下文將作專門討論。另有如第13、16、17三种或只是稱“某國夫人”,或簡單給出作器者所在國名。如上所述,這些國名並不是我們所說女性的稱名的組成部分,不應列在文中(儘管它們和筆者講的女性稱“夫家氏名”的原則一致)。之外還有如第10-15种形式是單稱其名或姓,或單稱其排行或官職;如前文所述,這些均是隨機的簡稱,不能成爲我們研究稱名原則的證據。總之,吳先生排列的資料雖然貌似龐大,但這實際上是不能嚴格甄別史料的結果。 關於“反證” 吳鎮烽先生整篇文章中真正可能談得上是“反證”者只有女性自己作器的第3、4、5种稱名形式。我們下面就這幾例“反證”進行重點討論: 3、父家國氏+父家的姓(包括齊姜鼎:“齊姜作寶尊鼎”;魯姬鬲:“魯姬作尊鬲”;吳姬簋:“吳姬旅簋”;祭姬爵“祭姬作彝”); 4、父家國氏+姊妹間排行+父家的姓(曾仲姬壺:“曾仲姬之醬壺”); 5、父家國氏+女子名字+父家的姓(齊巫姜簋:“齊巫姜作尊簋”)。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第4种形式曾仲姬壺的作器者並不能確定。此器只有“曾仲姬之醬壺”共五字。這種以領有格為語法結構的銘文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認爲“之”前的名字就是器主,但是究竟它是器主自己作的,還是別人為她(特別是在女子的情況下)作的祭器或用器,這從銘文本身是不看不出來的。由於我們不能確定銘文中的“曾仲姬”是否屬於自稱,這類銘文是不應該列入女子作器自稱類的。因此,第4种的稱名形式實際並不存在。第3种的“吳姬旅簋”情況類似,即我們無法確定銘文中的“吳姬”是否自稱,因此它也不是一條合格的“反証”。關於第5种“齊巫姜作尊簋”,吳先生的解釋是“巫”是該女子的私名,因此這是一個“父家國氏+女子名字+父家的姓”的形式。但是金文中如果女子同時稱私名和姓,其常態是名在姓之後的,名在姓前的例子是極少的。因此,我們並不能排除“巫”是國名或族名乃至女子丈夫私名的可能性。如果那樣,它就可能於上節第6种形式相同,所以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反證”。 因此,在上述銘文中真正是反證的只有“齊姜作寶尊鼎”、“魯姬作尊鬲”、“祭姬作彝”。他們均是“父家國氏+父家的姓”的形式,也均明顯是女子自己作器自稱。有趣的是他們中的兩件出自西周都城豐京範圍:齊姜鼎出自張家坡墓地,祭姬爵則出自馬王村。它們確實可能是從齊、魯等諸侯國出嫁到陝西王畿地區的貴族宗族的女子自己所作的器物。但是,相對于符合西周金文稱名原則的上百件青銅器銘文的存在,這僅僅三件器物是極小的少數,而且它們僅限於女子作器自己稱名的範圍。因此,我們不能因爲它們的出現就否定金文稱名的常見的規律和原則。 誤讀或誤解之處 仔細閲讀吳鎮烽先生的文章,我們會發現他對金文稱名原則的質疑有時是基於他對筆者《稱名原則》一文的誤讀或誤解。下面擧兩個典型的例子。在關於丈夫為妻子作器稱名的一節,吳先生說: 李教授所謂“若他有兩位妻子都來自姬姓的A宗族怎麽辦?這在金文當中也是有例可循的,可以稱爲A(按:指族氏)孟姬,A仲姬”的說法也不正確。在金文和文獻中,伯(孟)、仲、叔、季是兄弟姊妹間的排行。《白虎通·姓名》云:“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已婚女子稱名中,不論是自稱還是他稱,也表示的是她在姊妹間的排行,沒有例外。至於丈夫對來自同姓國族的幾位妻子的稱名區分,不使用孟、仲……,而是用國名來區別,如果來自同一個國家,那就用長、幼來區別。如:《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齊侯三位夫人,兩位是姬姓。一位是來自周王室,一位來自蔡國,分別稱爲王姬、蔡姬。如夫人六人,四位姬姓,來自衛、鄭、密三國,分別以國名區別。來自衛國的兩位如夫人,再以長幼區分,大的稱長衞姬,小的稱少衞姬。 初讀這段文字,筆者不能理解爲什麽吳先生要批評我,因爲他論述的觀點和我主張的稱名原則是完全一樣的。仔細拜讀后才發現吳先生原來誤讀了他批評的筆者這段話,把邏輯上的兩個層次的問題混淆成了一個問題,這讓人感到很意外。在《稱名原則》一文中,筆者已經用圖表(本文圖一)和文字形式說得很清楚,在同屬於姬姓的A、C、D三個宗族均有女嫁到屬於姜姓的B宗族的情況下,那麽這位姜姓的B宗族的丈夫就要按照她們所來自的不同宗族的氏名(即“父家氏名”)(或國名)來分別稱她們為A姬、C姬、D姬。[9] 這不正是吳先生引用大段文獻想説明的原則嗎?即:“齊侯三位夫人,兩位是姬姓。一位是來自周王室,一位來自蔡國,分別稱爲王姬、蔡姬。如夫人六人,四位姬姓,來自衛、鄭、密三國,分別以國名區別。”但是,吳先生所批評的筆者這段話說的是“兩位妻子都來自姬姓的A宗族”,是來自同一宗族的姐妹,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她們不正是應該按吳先生說的按兄弟姊妹間的排行稱爲“A孟姬”、“A仲姬”(A代表她們所來的宗族),錯在哪裏?這和文獻中提到齊侯來自于衛國的兩位姬姓夫人分別稱“長衞姬”和“少衞姬”完全是一樣的道理。 在關於女性為丈夫作器一節中,吳先生說: 李教授說女性爲丈夫作器,自稱的原則是“稱她所來的宗族的氏名,以及她所來的宗族的姓”,即女子父家的族氏和父家的姓。據不完全統計,以這種方式的自稱,在金文中並不佔多數。因爲她的作器勒名和自稱,其使用範圍就是自己家族,一般情況下是可以區別的。 吳先生引用的這段在筆者《稱名原則》文中的原話是:“反過來看,當該女子的丈夫為她作器時,就不會這樣(指上段)稱呼了。這時,她的稱呼應該是A姬,即稱她所來的宗族的氏名(正好與女子父親對她的稱呼相反),以及她所來的宗族的姓。”不幸的是,吳先生將這裡的“女子的丈夫為她作器”讀成了“女性爲丈夫作器”。筆者在整篇文章中,從來沒有談到女子為丈夫作器的問題,但吳先生卻基於自己的誤解,並結合不完全統計來質疑筆者關於所謂“女性為丈夫作器”的自稱原則。作爲一個資深學者而犯這樣的錯誤,實在讓人遺憾。 關於一器媵多人的現象 吳鎮烽先生文中也談到媵器中父母對所謂隨嫁媵女的稱名問題。筆者認爲,青銅器銘文中這種一器媵二女的現象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隋嫁問題,而是反映東周時期複雜的地域政治關係。而且,這種一器媵二女的現象主要發生在南方以楚為中心的江淮地區,他們與南方特別的政治環境有關。筆者在2017年5月武漢大學和2017年6月吉林大學的講演中已經就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討論,稱其為“金文稱名原則III”。[10] 今就其内容簡述如下。到目前爲止,我們所看到的比較明確的一器媵二女的周代金文有三個例子: 曾侯作叔姬簠:“叔姬霝乍(作)黃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將彞。其子子孫孫其永用之。”這裡的“作”過去一般都讀為“適”,往也。這是曾侯為叔姬、邛嬭兩人作的媵器,本身説明曾為姬姓。黃囯是嬴姓,見黃君簋(銘:“黃君作季嬴稻媵簋”)。 鄦子妝簠:“唯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簠,用媵孟姜、秦嬴,其子子孫孫羕保用之。” 許國國君為孟姜、秦嬴作媵器。許為姜姓,故稱孟姜(參考鄦姬鬲:“許姬作姜虎旅鬲”;此為嫁入許國的姬姓女子為許國某人所作)。 上鄀公簠:“唯正月初吉丁亥,上鄀公擇其吉金,鑄叔嬭、番妀媵簠,其眉壽萬年無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上鄀公為叔嬭、番妀作賸器。叔嬭可能是楚國出嫁的女子。番妀為番國出嫁的女子,番國妀姓,參考番匊生壺(銘曰:“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鑄媵壺,用媵厥元子孟妀”)。 筆者的分析方法是首先將這三篇金文進行排比,找出其中的規律,作爲稱名原則的基礎(表一):
我們可以看到以上三器有如下共同特點:首先,前兩器(曾侯作叔姬霝簠、鄦子妝簠)中第一位女子均和作器人有密切的血緣關係;也就是說,她們是從作器人國出嫁的女子,並且應該是國君的女兒。即曾侯之女為叔姬,許子之女為孟姜,這一點可以首先確定。其次,銘文中的第二位女子則和作器人沒有任何關係。譬如,曾侯作叔姬霝簠中的邛嬭與曾國無涉(不管她嫁自邛或楚),鄦子妝簠中的秦嬴(明顯嫁自秦國)與許國無關。而第三器(上鄀公簠)中的兩位女子叔嬭、番妀可能都與鄀國無關係。第三,雖然第二位女子與作器者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至少在第二、三器中作器者均選擇其嫁入國(夫國)的立場以“父家氏名+父家的姓”的形式稱第二位女子:“秦嬴”、“番妀”(秦為嬴姓,番為妀姓)。這説明作器者(國)實際上與這些女子嫁入之國(夫國)關係更爲密切。至於第一器中的第二位女子“邛嬭”,如果邛是嬭姓(見下),也是從其夫國立場對她的稱謂。 這裡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兩位女子同時嫁入一國,故作器者為兩位女子(但主要是本國女子)作媵器。稱本國女子時採取了本國(父國)的立場,也就是遵照父親稱女兒的原則,用“夫家氏名+自家的姓”來稱呼她。但是,作器者與第二位女子是通過本國女子夫家產生聯係,也就是說,這位女子要和自家的女子一起在夫家生活,故作器者採取了其夫國立場,即“父家氏名+自家的姓”的形式來稱她們(圖三)。他們的地位可能正相當於文獻中屢屢提到的“媵女”或“媵人”身份。[11] 但是文獻講只有同姓才能相媵,這顯然不符合金文中的情況,因此我們不能拘泥于文獻中的信息,而是首先要在金文的範圍内闡明金文中的稱名原則。  圖三 具體來説,曾侯作叔姬霝簠(第一器)是曾侯為將嫁入黃國的曾國姬姓女子孟姬所作。由於邛國的嬭姓女子同時也嫁入黃國,[12] 故曾侯為孟姬、邛嬭同時作器,但主要是為自己的女兒孟姬作器。第二器(鄦子妝簠)是許子為將出嫁的女兒孟姜所作,由於秦國嬴姓女子也嫁入了同一國,故許子在名義上為孟姜、秦嬴同時作器。第三器(上鄀公簠)為叔嬭所作。叔嬭和上鄀可能沒有聯係,但叔嬭應該是楚國出嫁的嬭姓女子,上鄀公作爲楚國的附庸作媵器隨嫁,他的稱名應該是採取了楚國的立場。由於番國妀姓女子同時也嫁入此國,故上鄀公在名義上為楚國女子叔嬭(採取楚國立場)和番國女子番妀同時作媵器,但對後者採取叔嬭夫國的立場來稱呼。重要的是,在一器媵兩位女子的情況下,對第一位女從其父國(圖三中A)的立場,以“夫家氏名+自家的姓”形式來稱呼;對第二位女子則從其夫國(B國)的立場,以“父家氏名+自家的姓”的形式來稱呼。 了解了上述一器媵多人和隨嫁媵器的称名原则,特別是同媵的兩位女子稱名換位的原則,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別的例子,都可迎刃而解。如近年湖北棗陽郭家廟出土的曾侯作季汤芈鼎銘:“曾侯作季…湯彌(羋)媵…其永用。”曾侯所作之媵器,但所媵女子卻是羋姓,可能是楚國女。這是曾侯(處於D的立場)為楚國嫁女所作的隨嫁媵器,對象國可能是離隨縣不遠的湯(唐)國(B的立場),為曾之鄰國。銘文從楚國的角度(A的立場)稱其出嫁湯國的女子為“湯彌(羋)”。 另一個例子是 結語: 綜上所述,周代金文中對女性的稱謂雖然是複雜多樣,但只要我們能夠基於對周代宗族社會的理解,從整體視野來仔細分析這種現象,就能夠發現這些銘文後面隱藏的原則,從而得出一個整體的和符合邏輯的看法。吳鎮烽先生雖然羅列了金文中女性稱名的種種形式,可謂全面,但他由於缺乏真正的反證資料,所以並不能推翻這些原則。他所提出的僅有的三條反證數量太少,涉及範圍又狹小,更不足于影響大局。吳先生希望以媵器中女性稱名大多數並不帶有宗族氏名來否定父親對女兒用“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等稱名原則,但是因爲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命題,他的論證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他對筆者《稱名原則》一文的誤讀、誤解之處更是讓人遺憾。另一方面,吳鎮烽先生雖然極力想否定筆者提出的各項稱名原則,但他在對具體銘文的解讀中卻不自覺地在自己也用了這些原則。譬如,吳先生說:“從中伯壺‘中伯作辛姬孌人媵壺’銘文可知‘中’宗族姬姓。‘中’是該婦女的父家氏名,‘姬’是其姓…… ‘辛’則是夫家的氏名。”如果吳先生心目中沒有媵器中父親稱女兒用“夫家氏名+自家的姓”的認知,他是不會得出這樣的解讀的。遺憾的是他自己並沒有能把這些原則系統總結出來。如果否定了這些原則,那就是説金文中對女子稱什麽都可以,西周貴族可以任意所為,不顧宗族原則。我想,這並不是吳鎮烽先生想要的結論,也不是大家能夠接受的結論。 2017年9月29日紐約森林小丘家中 [1] 這場座談(包括講演)的内容后經整理發表在,王沛:《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五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第26-59頁。 [2] 李峰:《西周宗族制度下的“稱名區別原則”》,《文匯報》(文匯學人)2016年2月19日14-15版。這個簡短講演中有關“稱名區別原則”的内容,此前2015年12月1日在北京由芝加哥大學和陝西考古研究院主辦的《石鼓山、戴家灣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範學術研究會》中已經作了簡單介紹(報告題目為《西周青銅器製作中的另類傳統》),為此學説最早公諸學界的時間。也應提到,2016年11月2日,在陝西周原舉行的《周原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筆者也曾利用會議允許的15分鐘就此觀點作了簡短介紹。 [3] 2017年6月6日,筆者就同樣内容在吉林大學作了題爲《金文稱名原則和西周的宗族婚姻制度》的講演。 [4] 吳鎮烽:《也談周代女性稱名的方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頁2016年6月7日發表: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22。2017年9月3日訪問(本文討論的吳鎮烽先生文章均以當日該網頁所刊載内容為准)。 [5] 《銘圖》指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銘圖續》指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6] 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媵器要隨女兒帶到夫家,並且可能被其他並不了解其父家乃至夫家情況的人看到, 採用正式的稱法更爲必要。關於青銅器及其銘文在西周社會不同場合的出現,筆者有專題論述,見Li Feng,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Contexts of Writing in the Western Zhou,” in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Studies from the Columbia Early China Seminar, edited by Li Feng and David Prager Brann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 271-302. 另見Li Fe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in Early China: With the Nature and Us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Context, and More,” University of Zurich, forthcoming. [7] 包括僅稱姓者2條,僅稱私名者4條,姓名連稱者19條,姊妹排行+自家的姓者53條,姊妹的排行+自家的姓+女兒私名者34條。總數112條,即含所有不包括“宗族氏名”者。 [8] 在這一節,吳先生還列出了另外三件銅器,作爲他論述的補充: [9] 更不用説,來自不同姓的不同宗族的女子,他們共同嫁的丈夫要以她們的來自的宗族氏名(或國名)來區別她們。 [10] “金文稱名原則II”指金文中“某生”(如琱生、虢生等)的稱名原則;相關論述見李峰:《西周宗族制度下的“稱名區別原則”》,《文匯報》(文匯學人)2016年2月19日第15版。 [11] 關於文獻中“媵女”或“媵人”的梳理,見陳昭容:《兩周婚姻關係中的“媵”和“媵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二分冊(2006年),193-278頁。 [12] 這裡也需要説明一下,關於第一器(曾侯作叔姬簠)中的“邛嬭”,我們認爲應該是從叔姬夫國即黃國的角度稱邛國同時出嫁到黃國女子。但這似乎與另一件銅器楚王鐘矛盾。楚王鐘銘曰:“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邛仲嬭南龢鐘,其眉壽無疆,子孫永保用之。”從字面理解,由於楚王為“邛仲嬭”作媵器,邛應該是她的夫國。但是,邛國文獻有姬姓和嬴姓的不同説法,學者之間過去一直有人主張邛國可能是楚國的同姓即嬭姓。因此,金文中所見的邛究竟是一國還是兩國,或者邛和江究竟是否一國,我們現在還無法確定。關於邛的問題,參考李仲操:《两周金文中的妇女称谓》,《寶鷄文博》 1991年1期, 35-39頁;白川静:《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志;神戶,1966-83年),第40輯552頁。 [13] 劉麗:《一器媵二女現象補說》,《古文字研究》31(2016),199-204頁。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