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读书、行路、思考与突破瓶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2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曾江 参加讨论
编者按:区域史研究近年势头强劲,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学术平台也在陆续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前沿。区域史已取得哪些主要成果?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如何促进区域史研究走向深入?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采访请教各地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分享动态,交流思想,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本期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请教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赵世瑜教授长期致力于明清以来社会史与民俗学史研究,近年学术专著有《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2002)、《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2006)、《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2017)、《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2018)、《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2019)等,主编《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民众生活》(2010)、《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2016)等。 区域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取得长足进步,引起相关学界很多关注和讨论。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在区域史领域与“华北”“华南”“江南”等研究领域学者都有深入的学术合作和思想砥砺。区域史当前面临什么瓶颈?如何进一步促进区域史研究?近期主要推进哪些学术工作?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近日采访请教了赵世瑜教授。  赵世瑜教授在晋祠访碑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区域史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接下来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在您看来,当前区域史研究主要存在哪些不足。 赵世瑜:关于区域史研究,最近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在《区域史研究》2019年创刊号上有一个长篇的访谈,讲得很全面了。的确,在最近三十年里,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第一,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像北京、上海这样集中大量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城市中,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力量还极为薄弱,地方高校的学者比较而言对此更为重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也要比历史学的同行对此更为关注,所以我们的平台还很小。第二,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已经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的区域还很少,像华南地区那样具有比较系统的认识的区域还没有几个,因此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具体的表现是,比较经典的区域史研究作品很少,还远远无法与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相比。第三,注重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是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一项看家本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需要我们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但作为学者来说,新材料固然重要,新思想却更为重要。几年前陈春声教授和我都专门说过这一点,最近王学典教授也撰文谈到理论的重要性,但情况还没有明显改善,这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是不利的。 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是做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一方面要系统地接受传统的历史学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做田野工作——这并不仅指到乡村去搜集民间文献;一是要系统掌握历史学的必备知识和方法,同时要比较准确地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理论。无论是读书还是行路,都会更加艰辛,还要考验智商。现在地方民间文献整理出版的很多了,假如用研究简牍那种做法,大概用几辈子都用不完,但为什么还是没有经典作品出来?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读书读得不够,就是没能从五六岁的时候就从《诗经》、古希腊罗马神话或者《罗摩衍那》开始读书,即使上了大学知道要读点人类学,也没几个人愿意从《金枝》开始系统读下来。所以,虽然学界的主流对这种研究依然存在一些误解,但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我们的研究者愿不愿意吃这种苦,愿不愿意不停地阅读、思考、观察、体验,最后是不停地写作? 这样的研究方式对国外的中国史研究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长期脚踏实地地在中国的基层工作,在田野中理解包括地方民间文献在内的各种历史材料,在实践中理解历史上不同人群的实践,所以我们最有希望提出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理论。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但如果不经历那些艰辛,苦中作乐,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过10年,如果不能出现几部可以紧随顾颉刚、费孝通脚步的比较经典的作品,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埋怨客观困难了。  赵世瑜教授近年部分学术专著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论文《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近日刊发后,引起关注和讨论。其中您还提到,“珠三角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史的认识和把握。这一对‘华南研究’本体论意义上的认知,是以往主要从方法论意义上的评价所忽视的。”可否进一步展开谈谈您对此的相关思考。 赵世瑜:我还没有来得及关注学界对拙文的讨论,我特别希望听到学者们的批评意见,帮助我完善和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思考。 可以说,这篇文章不是一个区域个案,而毋宁说是通过4个案例来表达的一些理论思考。显然,这4个案例如果展开,可以是4本书,其中关于苏州东山的书正在写,太原晋祠的书也许在5-8年后可以完成,当然并不只限于那里的社——社庙只不过是我们观察区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珠海淇澳岛或者中山是华南研究的范围,也有年轻学者有关于东南海岛研究的计划;浙江遂昌的研究是肯定有人做的,因为已有至少3-4支团队在那里进行调查和搜集民间文献。那么,通过这4个区域性案例,我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我想尝试一下费孝通说的社区研究的第二步,就是社区比较;第二,我想尝试一下以前说过的理想:通过区域史研究可以达致对中国历史整体的重新认识,避免人们对区域史研究产生“碎片化”的误解。无论这种尝试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我的观点有理还是无理,这种尝试都必须做。 必须指出,在我自己没有多次田野和专门研究的地方,极大地得益于研究那里的学者们的指教和频繁的讨论。我去过多次广东和福建,没有刘志伟、科大卫、郑振满等人的耐心解释,我甚至连他们的书和文章都读不懂。这绝不夸张,也不是说他们的文字晦涩,而是说,除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不强外,不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你没法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这就是我们这个行当的特点。因此,我时常怀疑许多读过他们的书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读懂了他们的书。甚至,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也不能让我对华北和江南的理解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所以,我非常郑重地建议,我们的研究者在有机会跟随研究某处的朋友一起跑的时候,不要把这当作别人的事,觉得与自己的研究无关,而要像对自己的研究那样去阅读那里的材料,一起讨论,甚至写出心得,这样才会引发对更大的空间观照和假说。 关于“华南研究”的本体论意义,过去似乎没有人提到过。过去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评价华南研究或历史人类学,比如如何与人类学者共享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平台,比如技术上如何将文献工作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等等,但是,对华南研究揭示出的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莆仙平原或者韩江流域的社会历史的结构过程,也即历史本体,几乎没有评论。那么,他们说的对吗?事情是那个样子吗?如果说的对,那么这些区域在整个中国史中的意义和地位是什么?没人评说,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的专家。这很可悲。在传统的中国史领域,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对某个墓葬如何认识?对某片简牍如何解读?对某个事件或制度如何评价?可以有很多位学者参与争论,但我们这里没有。没有读过那里的民间文献,没有去那里做过访谈,怎么在事实的层面上进行评价?这就造成了区域史研究向前发展的巨大瓶颈。 当然,我在文章中只是通过具体的例子,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能全部看到4种形态的社,经历了明清至今650年的时间,其原因在于,这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过程,在其开发过程中遭遇到世界性的和中国本土的剧烈变化,于是经历了异常迅速的社会变动,某些老的东西还未消失或变身,新的东西就冒了出来,于是新旧杂陈,“死的”和“活的”相互拖拽。许多古老的族群及其传统依然可以在很晚近看到活生生的踪迹,而“北族”,哪怕是女真和蒙古,在今天华北的生活世界中也难以窥其面貌了。因此,一部漫长的历史在这里看似被“折叠”起来,也许华北的历史就是这部历史的“拉伸”。“拉伸”之后,许多细节或原型在今天的生活中就看不到了,而珠三角不同。这就是我所谓的华南研究的本体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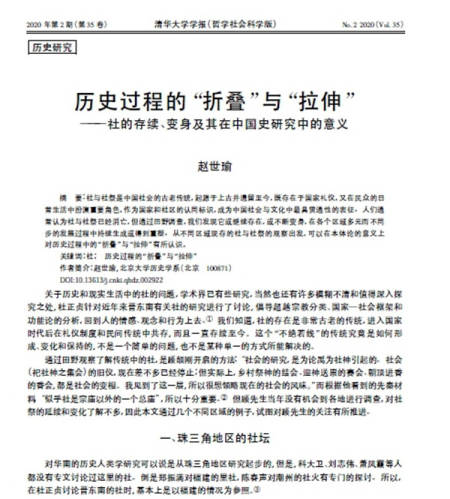 赵世瑜教授《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资料图片  赵世瑜教授在苏州东山对渔民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于“成都平原”或者“华西”的区域研究,与其他一些区域相比,似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展开。您对其他区域研究都很了解,作为原籍成都的学者,对于推进“成都平原”或“华西”区域研究有什么建议。 赵世瑜:正如前面所说,不仅是西部地区,无论西北还是西南,除了华南的若干地区外,基本上工作都是刚刚开始。比如关于南岭山区和东南山区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在着手进行。但是必须分清“区域研究”这个概念所指,因为对西南的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就做了不少研究;对江南的区域史研究,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农史、水利史,都有很出色的研究,我这里是仅就历史人类学的区域史研究而言的。 对自己的家乡,我当然希望能够研究好,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了。四川的资料很丰富,无论是成都平原、川东、川北还是川西,都有非常不同的文化传统;一条长江,从“右三江”的“江谷”到出川前的“江峡”,在四川境内可以分成好几个段落。我希望年轻的学者把四川研究好,多年前我曾说,一个都江堰,就是一部中国通史。其实,在全国各地,都不是值不值得研究和如何研究的问题,都是愿不愿意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生活比较安逸的地方。  赵世瑜教授在福建永泰读碑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方志,您是新一届也就是第六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可否简要谈谈您近来在研究中对方志的相关思考。 赵世瑜:这个话题,三言两语说不完。我们做区域研究的,地方志是了解一个地方的入门指南,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材料。我指导学生做学位论文时,一开始就是读方志,这个认识和做法与是否担任地方志领导小组成员关系不大。 当然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我对新编方志的关注就更多一些,特别是乡镇和村的志书,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把苏州各区在20世纪90年代编的村镇志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项工作特别重要,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乡村都消失了,不要说建筑、实物,就是老的地名都变了,这个变化我认为是秦统一以来对基层社会的一次较大的扰动。所以,村镇志编不编,编得好不好,也就是“存史”的功能实现得好不好,责任极其重大。否则对后人来说,他们的故乡的历史就可能有一段成为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由于疫情,学术工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可否介绍下您近期在做哪些工作。 赵世瑜:疫情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不能做田野。辩证地看待问题是很正确的态度。疫情时待在家里,减少了很多会议和应酬,难得地回到了读书人最向往的读书和写作的生活节奏。读了许多师友及年轻学者关于江南历史的书和论文,同时关于江南的小书的总体架构也搭起来了。为了调节情绪,在疫情发生初期,将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的中译本审校完成,现在又在审校《剑桥清史》第2卷的中译本。前者英文版出版时,我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后者英文版出版时,我的学术道路已进入后期。两相对比,我的感觉是,同样是研究中国,我今天读前一部书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一代学者的睿智;而我读后一部书时,我的感受是,中国的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水平在总体上已经不弱于、甚至强于欧美的学者了。  赵世瑜教授在山东泰安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曾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