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专访】接续传统与全球视野:张国刚谈中外关系史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41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曾江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出版后引起学界关注,许多学者给予中肯的学术评价。马克垚先生在“序”中对您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评价认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升到理论高度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可否分享下您在这部专著里的一些理论探索。 张国刚:马克垚先生,还有一些书评,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非常感激。不敢说拙作有什么理论高度,只能说有一些想讲清楚的问题意识。比如,中西关系的“西”,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与许多文化都发生过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特别要强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呢?为什么这个“西”从中亚、南亚、西亚,延续到欧西呢?从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蒋梦麟的《西潮》,到西学东渐的“西”,地理与文化内涵都很宽广。这个“西”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伴随着中国人对异域世界认识的脚步而不断拓展,最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比历史上所接触之地更靠西,则“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 第二,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它们都是真正的“他者”。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宗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部。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学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从波希战争、希腊化时代,到十字军东征等,造就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过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宗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至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以至公元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因此欧洲的中世纪其实是近东文化与希腊罗马的混合物。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然而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来重新显现。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 与以上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西”。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佛教传入之时就闹过“老子化胡经”的笑话;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因为在东亚世界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为主的主导性地位。 我认为这种对于“西”的定位,可以更加凸显中西文化关系的特色,同时也使得中西关系与中国与东亚邻国(如日本韩国)地区的中外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有利于中外关系史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其次,也更能理解和揭示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此外,在胡化与汉化、文明对话、误读与创造方面,我也力图有所突破。  张国刚教授在柏林联邦档案馆查阅搜集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是一部通史性研究著作,撰述这类打通古今之作非常有挑战难度。可否介绍下哪些前辈学者对您的研究方法有较大影响,您在治学过程中注重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这些对青年学者应该很有启发意义。 张国刚:断代史的专题研究与专史型的通史编纂很不一样。但是,后者一定得有前者的训练。在我敬仰的大家中,以清华大学的前辈学者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冯友兰先生从一卷本、二卷本到多卷本的不同篇幅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的《中国通史讲义》都是贯通性作品。在我的师友圈中,有许多在中外关系史学某一断代或者某一细分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专家,他们的论著对我启发很大。但是,我觉得用打通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中西文化关系史”,应该也是学术研究中需要的内容。我对中古佛教、明清耶稣会士、欧洲汉学都做过一点研究,也跑过欧洲各大图书馆。我给自己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定位是,在力所能及的专题研究之外,要主要打通传统西域南海的中西交通史与大航海之后中欧(真正的西)关系史。类似这样的“中西关系史”我写了好几种,现在这本是第四本,也是篇幅最大的一本。 我没有什么治学方法值得谈,要谈就是比较勤奋,我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像我这样愿意在专业之外通读“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含《续资治通鉴》)之类的通史型经典,恐怕不是太多。我的读书、教书、写书,既是职业,也是兴趣,乐此不疲,构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再就是读书比较杂,从上大学卖饭票买书,到现在做到了买书上的财务自由,大约有一万几千册书吧,家里到处是书架,大约七、八十个书架吧。此外,可能与年龄有关,也可能与兴趣有关,现在思考通论性的问题似乎更多一些。 但是,我对自己的研究生一再说,要从微观入手,要有宏观视野,我很推崇严耕望的《治史经验谈》,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好。 中国社会科学网:除物质文化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交流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请谈谈您对中西文明的理解。 张国刚:中国文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世界各国文明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有共性,这是文明交流与互鉴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中国文明的特色是什么呢?从制度层面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职业官僚制度即从军功爵、察举征辟到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土地买卖在内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经济上与政治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流动的,所谓“贵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爱拼才能赢”,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活力充沛的社会,需要一种思想的约束,于是,主流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家国天下,即所谓儒家社群主义(Confucian Communitarianism)。 但是,西方中世纪历史与中国完全相反,马克思称之为凝固化的政治结构、硬化了的地产结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人的身份固化,宗教意识禁锢人心,社会缺少活力。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逐次登场,资产阶级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随着走出中世纪的步伐逐渐深入,西方政治上的等级制、经济上的庄园制以及教会神权对思想的垄断,也逐渐瓦解,于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被西方提升为普世价值。但是,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群”的利益和权利则无形中受到了漠视,进而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情况,如果说此前尚不明朗,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化、地球村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则将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也终将损害每一个个体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为贵、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论,也需要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发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  张国刚教授应邀在日本唐代研究会演讲,与气贺泽保规教授、砺波护教授合影  张国刚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谈“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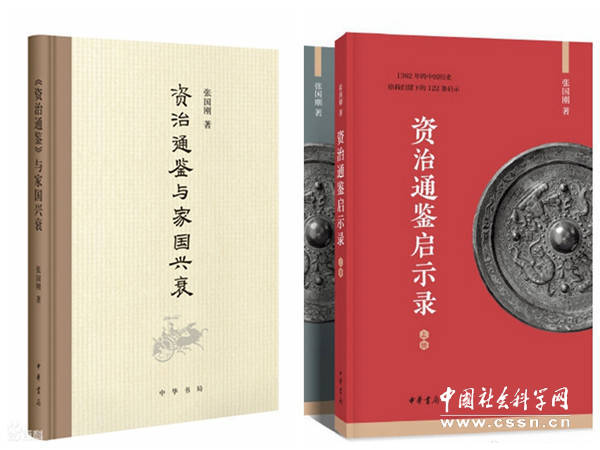 张国刚教授《资治通鉴》研究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问您近期在推进哪些学术工作? 张国刚:接下来将要出版的书有几种,有我的唐史研究论文集《大唐气象:制度、家庭与社会新论》,还有面向大众的《千年治国:〈资治通鉴〉与治世得失》《丝路交流二十讲》《〈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智慧》等书。当下在阅读基本史料和著作,并作一些笔记,修订早年出版的几本唐史著作,计划撰写一部大部头的《隋唐五代史》。 至于中外关系史方面,想修订《德国的汉学研究》,同时追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新成果,定期修订增补《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
- 下一篇:以史育人 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