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习惯的力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54 《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 陆建德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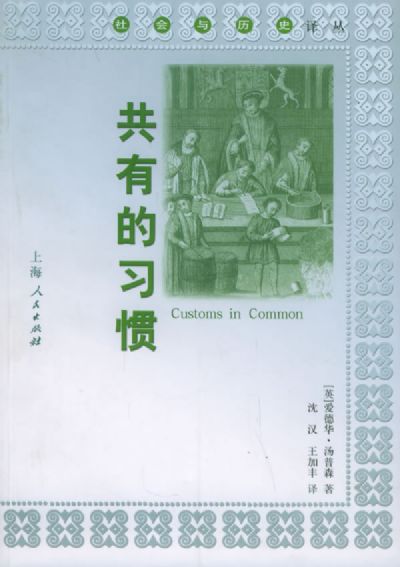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是先天的,普遍的;“习”是后天的,特殊的。两者孰轻孰重?这大概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性”和“习”不能完全割裂开来讨论。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起于对立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属“习”的范畴),但也是人的贪婪本性使然。现今强调“认同”或“文化身份”的论者可能相信,“习”不仅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保证,甚至还是“性”的决定因素。有常言为证:“习惯成自然”,“习久成性”。确实,“习”的力量深入而持久,人们往往深处其中而不自知。 然而,也有人轻视习惯的力量。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写道,某些18世纪思想家“迷于空华,醉于噩梦”。他们有舍我其谁的气概,“视国家为器械,吾欲制之则制之,欲改之则改之,吾凭吾心之规矩,以正其方圆”。这类人物尊崇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理性,抱负远大。在他们设计完美的鸿图里,不见社会习俗的踪迹,于是行之于甲地的制度必然可以移植于乙地。上世纪20年代,马寅初先生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中批评那些不顾中国习惯的归国留学生,他们“遇时不好时,就要改革,卒至改革不行,必至失败灰心”,颇类似于《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的薛奎:“性刚毅,既与政,遂欲绳天下一入于规矩;往往不可其意,则归臣于家,叹息忧愧辄不食。”接着他拿出英国人来做对比。他说,英国人素能固守习惯,对习俗移人的道理认识透彻。他们治理上海租界华人聚居区的污秽,不求速效。“英国人能顾全居民之习惯,因势而利导之,其步骤虽缓,其成绩甚大。”[1]也就是说,英国人知道,移风易俗必须行之以渐。 (一) 英国人重习惯,这是举世皆知的。英国是宪政的摇篮,但是居然拿不出一部让人读了一目了然的宪法。所谓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在历史进程中有机形成,无数杂乱无章的文书和习惯构成其主要内容,很多做法和规矩都是不成文的。英语中的“不成文”(unwritten)一词有“依照惯例和习俗为人所接受、承袭”之意,因而不成文法往往有保守因循的特点,有时会被冠之以“传统”之名。英国史学界多左翼人士,他们会考查“传统”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制造出来,而“习惯”(custom)一说可能被用来维护不公正的现状(见霍布斯鲍姆编于1983年的《发明传统》一书)。虽然习惯在英国的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雷蒙·威廉斯却没有在《关键词》一书中收入关于“习惯”的辞条,此举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威廉斯在“传统”的辞条末尾补充道,“传统主义”是一个贬义词,“似乎用来专指妨碍任何改革的习惯或信念”。可见“习惯”一词有维护特权之嫌。其实不尽然,不成文的习惯也可能是普通民众寻求某种社会保护的依据。 就政治谱系而言,杰出的英国史学家爱·帕·汤普森与威廉斯同出一源,两人同为英国“新左派”的元老。与威廉斯不同的是,汤普森更注重历史细节,更愿意发掘习惯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汤普森对民间习惯产生学术兴趣,也许是因为他深深怀疑“文化”这种笼统提法是否能真正推进历史研究。他的这本《共有的习惯》向读者展示了“习惯”在18世纪英国社会中的丰富体现。 习惯无时无刻地以极为复杂的方式约束着社会生活。人类学家赛德尔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纽芬兰地区渔村时对“习惯”作了一番界说,它可以概括汤普森在书中描述的群体行为:“习惯可以保持对集体行动的需要,调整集体的利益,并在以往一直共同参与的领域和范围内,集体表达感情和情绪,提供一种排斥局外人的边界。”汤普森指出,与17世纪、19世纪相比,18世纪的英格兰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当时的平民并不是无助的失败者,他们以集体行动维护习惯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以确保相应的利益。在荒年,他们推翻磨坊主和面包师的房屋,提倡博爱和仁慈的精神,要求扩大都铎王朝(1485—1603)最后几年制定的济贫法的施用范围,从而使得饥荒不至于升级为生存危机。他们还享有其他一些自行其是的自由:在圈地的围墙上打开缺口,一拥而入;在街上横冲直撞,用锅罐瓢盆发出喧闹之声,从而表明集体的情绪和道德伦理立场。凡此种种,都令外国来客震惊。尽管当时的平民与乡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是习惯的力量使得两者相互需求,有一条互惠的脉络清晰可辨。 英文中有“快活的英格兰”(Merry England)的短语,系英格兰(尤其是伊丽莎白时期)传统的爱称。自从上世纪中期以来,史学家更关注英国历史上残暴混乱的一面,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里的某些场景对此有所反映。但也难以否认这一事实: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度确为穷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到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时期,王室和枢密院(内阁前身)为保护平民基本权益,维持社会稳定,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汤普森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揭示,接近18世纪末,当英国劳工慢慢脱离对乡绅的直接依附、不受庄园和教区控制时,那就到了工人阶级开始出现的阶段。然而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政府自比一家之长,对经济活动多加干涉,实行家长式统治(paternalism,也可译为父权制)。《共有的习惯》以18世纪的英格兰和残存的家长式统治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篇。 史学家屈维廉在《英格兰社会史》中追溯板球运动的起源时描绘了18世纪英格兰的贵族、乡绅和普通百姓在乡村的草地上一同参与比赛的场景,他接着感叹:“如果法国贵族能与农民一同游戏,那么他们的庄园就不会[在大革命期间]被焚毁了。”[2]屈维廉的史笔时常受到“怀旧”、“浪漫化”之讥,但是他对英格兰18世纪社会关系的描述也不都是过分之辞。我们很难想像,艾迪生在该世纪初的《旁观者》杂志上刻画的乡绅罗杰·德·柯夫雷爵士会苛待他的下人和教区里的平民,或者用我们中国传统小说里的话来说“独霸一方”。汤普森在本书第二章“贵族与平民”里把当时的社会比为戏台与反戏台的互相映照。戏台上表演的当然是贵族和乡绅,而反戏台则是平民借以表明态度的场所。两个戏台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理智的妥协和良性互动。如果戏台上的贵族缺少自检自律,迫害平民过甚,那么反戏台上就会出现激烈的情绪和极端的举动;要是贵族和乡绅为反戏台上的某种危险端倪所震惊,他们会调节自己的举动,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反戏台上的平民回避过激手段。汤普森称这种现象为“家长制—服从的均衡”:“存在着一种统治者和群众的相互需要,互相监视,在彼此的观众席前面履行戏台和反戏台的作用,缓和着彼此的政治行为。英国统治者尽管不能容忍自由劳动者的反抗,在实践中,却对民众的狂暴表现出使人感到意外的认可。” 显然,汤普森在考察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时跳出了我们十分熟悉的模式:不同的阶级利益互相冲突,水火不容。贵族乡绅与平民之间的“家长制—服从的均衡”有点像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尊上亲下”。如果“上失其位”,那么“下逾其节”。皇帝发“罪己诏”也是“戏台”上的象征性行为。可惜这种“家长制—服从的均衡”在中国极易被打破,因而社会屡屡经受毁灭性打击。英国在18世纪时国家机器相对虚弱,但是平民的某些反叛行为并不纯以破坏为目的,他们发出不平之鸣,是想维护他们在家长制统治下世代因袭的权利,“惯例”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汤普森注意到,在平民争取自身权益的行动中,激进与保守的成分兼而有之:“他们时常回顾一个更加独裁的家长制社会的规章,例如粮食骚动的参加者求助于过去的《政令手册》(指1630年颁发的Book of Orders,也译作《敕令册》),由此诉诸立法来反对囤积者,工匠则求助于都铎时期的法典。”习惯(法)在社会转型期反而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某种安全网。 多年来,为了渲染“苦大仇深”,我们喜爱夸大权力的绝对性和任意性。从英国的例子来看,习惯使权力收敛,这似乎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在18世纪的英国,践踏或不尊重习惯所赋予的权利可能会导致政权的动摇。汤普森在第三章“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讲述的一件事是开我们眼界的。伦敦的王家园林圣詹姆斯公园历史悠久,长期对民众开放,英王乔治二世(1727—1760在位)的王后卡罗琳试图收回王室独用权,为此她问首相罗伯特·沃尔浦尔,安抚民众需要多少费用。沃尔浦尔冷冷地回答:“只要一顶王冠。” 自从大宪章(1215年)签署以后,英国国王也需服从法律,“朕即国家”之类的语言在英国是无法想像的。沃尔浦尔上述的警告也说明,英国普通百姓不会轻易放弃习惯上得到认可的权利。沃尔浦尔在任时权重一时,他对民怨也惧怕三分。伦敦西南的里奇蒙猎园有几条公共步行道,它们存在已久。王室一度把这王家猎园圈围起来,造成步行道无法使用。公众很感不便,就通过“反戏台”发泄情绪,屡屡在猎园围墙上砸出缺口,担任御林监管员的沃尔浦尔只得不时派工人修补。后来沃尔浦尔的这一职务由阿米莉亚公主继任,猎园附近的百姓要求恢复穿越权的呼声越来越高。1755年,一位叫约翰·刘易斯的酿酒人强行进园未果,他就起诉看门人,理由是猎园的围墙阻断了公共的通道,法庭判刘易斯胜诉。刘易斯也适可而止,他选择用梯子越过围墙的方式重获过路权。猎园管理方把梯子建好后,居民又抱怨横档间隔太大,儿童和年长者使用不便。于是法官立即下令改建,务使老太太攀爬也不致吃力。这桩讼案的真正被告是阿米莉亚公主,而刘易斯的胜利是平民对王室的胜利。它一则说明英国王室不会用强,随时准备体面地妥协,[3]从而维护亲民的形象;二则告诉我们英国民间把通行权(rights of way)看得很重,一些公共小道年代久远,任何步行者都有权使用,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类小道至今仍有不少,地图上一一标出,有的路段穿越私人的地产和牧场,对公众而言也畅通无阻。1935年英国还成立了漫游者协会,其任务就是保护乡村环境,监督这些小路的公共通行权是否得到尊重。习惯的力量在这种事例上又得到印证。 从通行权的概念可以推知,英国的圈地运动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说到圈地时一般会强调它的残酷性和彻底性,其实圈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必要性(如人口压力),但它一直受到来自民间的抵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乡村诗人约翰·克莱尔在《荒地》一诗里谴责了经议院许可的“无法无天的法律”(lawless law),在他的眼睛里,公有的荒地是自由的象征: 无边的自由支配着漫游的景致, 没有标示所有权的栅篱在潜伸, 隔断远望中呈现出来的景色, 它惟一的束缚就是环绕的天空。 克莱尔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受欢迎的诗人,他在诗中表达的态度在民间是有代表性的,这本身就对无节制的圈地形成一种制约。汤普森提醒读者,18世纪的英国百姓会成群结队地肩扛斧头、铁锹和鹤嘴锄,拆掉圈地的围栏和各种“违章建筑”。正是这类受传统共有观念鼓舞但被史家忽略的集体抗议行动使得许多公地得以保存。(英格兰各地还有不少大片的草地有“Common”之名。)汤普森举例说,伯克郡纽伯里镇的格林纳姆公地就是在19世纪经当地民众抗争而未被侵占,可是这大片土地却在冷战期间被北约(美国)用作部署核武器的军事基地。汤普森是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核裁军运动(简称“CND”)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在建于格林纳姆公地的军事机场旁,常有和平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核讹诈和动辄诉诸武力的恶习。汤普森生前经常站在这类反战示威游行的最前列,他书写历史,也参与并创造历史,这是他与那些只以“理论实践”见长的阿尔都塞们最大的差别。[4]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王馗]戏曲理论体系的学术拓展
- 下一篇:[刘锡诚]象征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