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中国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55 搜狐历史 闵凡祥 参加讨论
 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 作者 | 闵凡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陈衡哲是中国的第一位西洋史教授,在西洋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对当时乃至今日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的史学著述虽不多,但却倾注着她多年来对西洋史教学与研究的认识、思考和由此而形成的具有较大开创性的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它们共同构成了她的史学思想。本文在对陈衡哲的生平与主要著述及其影响作简单介绍的基础上,重点对她的史学思想――包括她对历史教科书编写与历史教学的认识、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目的、史料选择所应遵循的原则、研究历史的态度及其对西洋史分期的见解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与介绍,并对陈衡哲的史学贡献给以简单评价。 关键词:陈衡哲《西洋史》史学思想 一 陈衡哲(1890-1976),女,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和西洋史教授,原名陈燕,字乙睇,笔名沙菲,英文名“Sophia Hung-Che Chen”(即莎菲·陈衡哲),祖籍湖南衡山,1890年生于江苏武进。早年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13岁时(1903年)到上海打算进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学习,但由于蔡元培因《苏报》案离开上海而不得,遂于1904年春进入一家新办学校――中英女子医学院学医至1907年。离开中英女子医学院后到四川(时她父亲在那里任职)与家人团聚,其间经历抗婚风波。一年后再次离家,到常熟与其姑母同住。其间,“自学古籍”,并为生计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1914年夏考取清华学校(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赴美公费留学资格,成为清华第一批留美女生(共10名,陈衡哲是第二名)之一。到美国后,陈衡哲先在纽约的一家女子中学“朴南堂”(Pufnam Hall)读大学预科,次年秋入美国最负盛名的瓦莎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史学系跟随Lucy M.Salmon和 EloiseEllery两位教授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兼修西洋文学。1919年在瓦莎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获赠“金钥匙”奖学金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研修历史、文学。1920年从芝加哥大学获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同年接受上海商务印书馆要求其回国为之编写复兴高中西洋史教科书的函请回国。回国后,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文系教授,开设西洋史课程——“西洋近百年小史”,兼教英文课,“为北大女教授之第一人”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洋史女教授。后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22年,应邀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编辑;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西洋史讲师半年;1930年又回北大执教西洋史一年;1932年同他人共同发起创办《独立评论》杂志;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1935年9月随丈夫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该校西洋史教授一年。1927~1933年间,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学会学术会议。抗战全面爆发后,辗转于武汉、香港、昆明、重庆等地。此间,“因生病不能常任教学工作,曾经作过历史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抗战胜利后,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之聘,任指导研究员一年,期满后返回上海。解放后到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在1955年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她被看作胡适派世界史学科的代表人物,成为重要的批判对象。此后,一直情绪消极,没再做学术研究工作。1976年1月7日因肺病逝世于上海,享年86岁。 陈衡哲的主业是西洋史,代表作有商务印书馆1924、1926年出版的作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的《西洋史》上下两册、1926年出版的《文艺复兴小史》和193O年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和《欧洲文学复兴小史》等。此外,她在历史方面的著作还有曾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上的《来因女士传》(该文记述了孟河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与瓦莎学院齐名的另一家美国女子大学的创建人来因女士[Mary Lyons]的生平事迹)和《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即冯进女士所译的《陈衡哲早年自传》。陈衡哲将该书说成是“再现历史风云的一面镜子”。在该书中,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另外她还记载了诸如1911年辛亥革命等晚近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历史分析)等。文学创作虽只是她治史之外的“余事”,但却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和声誉,以致现在人们只知有文学上的陈衡哲,而不知有史学上的陈衡哲,对她的史学思想及成就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则更是不多见。这同陈衡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西洋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在对其史学成就作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以使其为今天的读者所了解。  二 在陈衡哲的上述史学著作中,尤以《西洋史》最具代表性。胡适在为该书写的书评中对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在下册的编写中,她“把六百年的近世史并作十个大题目,每一题目,她都注重史实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在纷繁的事实里面忘不了一个大运动或大趋势的线索。有时候,她自己还造作许多图表,帮助文字的叙述。”这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其中“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表现出“作者的见解和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叙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它的出版,改变了同当时的中国史研究相比,研究西洋史的中国学者“没有什么贡献”和研究中“不曾有多么重要的作品”的局面,使中国学者关于西洋史的研究开始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同时,这套《西洋史》的出版还改变了“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用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宗教史只是基督教某派的信徒的西洋宗教史;哲学史只是某一学派的哲学家做的西洋哲学史”的做法,“秉着公心”,“用公平的眼光,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叙述西洋的史实”,“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表现出中国学者在西洋史研究方面有着更多“驰骋的余地”和以事实证明了在西洋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着更多“创作的机会”。再有,该书以很有文学意味和“叙述夹议论的文字”进行历史叙述,这在当时的“白话文里还不多见”,从而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如果说胡适因与陈衡哲素有交情,其评价之中难免有溢美之词话。那么,其后学者的研究或评论当更为公允、更具客观性了。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曾对国民以来编写出版的西洋史或外国史中学教科书进行过一次调查和对比研究(由蔡维藩先生负责)。研究的结论是:“还是商务复兴教科书,陈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册最好,是消化以后的创作,不是拿英文教科书片断的翻译”。我国当代著名欧洲学学者陈乐民先生则在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开设的《欧洲文明史论》课程中,向学生特别推荐陈衡哲的《西洋史》说:“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好好看。我说句大话,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的更好。……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文笔非常流利、细腻。”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冀骧先生在论及在我国早期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上做出突出贡献者时,也是首推陈衡哲。他说:“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写过关于世界史的介绍性文章,但不系统。要使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各国历史,必须有较好的系统性教科书。陈衡哲《西洋史》是流传广、影响大的教科书……这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洋通史,陈衡哲是近现代第一位女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在世界史方面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西洋史》出版后,作为高中的教科书,连用了十余年,本书具备明显的特点和优点,一是见解精到,是作者精心研究后写成,不仅叙述史事,而且揭示、分析其意义和影响,许多大学在教学中也采用她的学术观点,不少大学教师对此书亦极其佩服,例如(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在讲授西洋通史时,常常引述‘陈先生’认为如何如何,充满崇敬之意。二是深入浅出,文字生动,内容深刻丰富的同时又不艰涩难懂。”虽然后来何炳松编写的《外国史》(上下两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是根据美国已有的课本用中文编写,适于中学教学,一直使用到解放”)在被采用的规模上“有所过之”,但“由于是半译半编,著作的价值远不如陈衡哲的《西洋史》”。何兆武先生对陈衡哲本人及其《西洋史》也褒奖有加。他说“陈先生似乎一直是以‘女作家’而不是以‘女学者’的声名为当世所知的。其实陈先生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二十年代即任北京大学的西洋史教授,是北京大学第一位(或至少是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女教授,曾为商务印书馆撰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上下两册,风行一时。此书现在看来,自然不免浅薄,但内容浅显、文笔清通、叙事清楚,在当时是一部优秀的教科书,尤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是颇为难得的。”何成刚等人则在其评论文章中如此评论说:“在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史上,陈衡哲绝对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人。不仅仅因为她是惟一的一位为中学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女性作者,其实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她著述的《西洋史》有鲜明的特色。”“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陈衡哲著述的《西洋史》教科书是一部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历史教科书。” 此外,陈衡哲所写的《文艺复兴小史》也很有特点,她夹叙夹议,全书贯穿作者的分析和评说,写得栩栩如生,而不落俗套。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关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陈衡哲认为主要有三:第一,“是欧洲人民对于中古文化的反动”。这是其兴起的最基本原因;第二,“是因为到了第十四世纪时,中古开化的日耳曼民族的事业,差不多已经成功”;第三,则是人的“个性的复活”。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不再是编译外国学者的著作,而是由中国学者自己来撰写,这是十分有益的”。 陈衡哲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加之其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她成为一名当时“名满中外的女学者”。程靖宇先生在其为陈衡哲写的传记中即曾如此写道,“在当年除了国际闻名的胡博士(适之)外,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第一出名的中国女学者,便是这位Prof. Mrs. Sophia H. Chen Zen了”。 陈衡哲的《西洋史》之所以为胡适等大家所看重,之所以被看作是“一部开山的作品”,其论断之所以被认为是“独断之学”,能成一家之言。除部分原因在陈氏在西洋史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造诣和史学基础外,更与其有着非西洋人的眼光,论断皆出自其深思熟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源自于陈衡哲与众不同的历史教学和治史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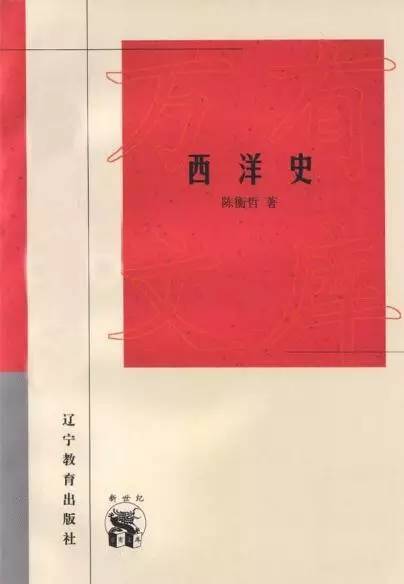 三 陈衡哲从事历史教学的时间先后不过几年,史学方面的著述也太不多。但她对西洋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却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与思考,形成了在当时具有较大开创性的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陈衡哲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是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延续,但她又同人们常常提及的中国新史学代表人物胡适等人的观点略有不同。同时,她对史学的认识也已超越何炳松在其《通史新意·自序》中所说的“吾国近年来史学界……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是对当时的西洋史学思想消化吸收或创造性接收的产物。同时,她在史学著述的编写上也超越了中国学者在西洋史研究方面只能翻译或编译外国学者著作的阶段,是最早以个人对西洋历史的见解及史识著书立说的中国学者。这带表着到20世纪的20、30年代,尽管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中国的西洋史研究已日渐走向成熟,开始从对西方史学的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中国的学者日渐用自己的眼光、自己语言、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来教授和写作西方人的历史;开始从致力于破坏“陈腐”的中国旧史学走向“建设”中国自己的新史学。在这一过程中,陈衡哲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1)史书(特别是教科书)的编纂与历史教学 陈衡哲认为,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应根据史实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章目,万不可刻意追求整齐,做“削足适履”的事情,“因为一书的章节,是各有各的个性的;我们决不能为求整齐的缘故,去把史迹的个性牺牲,或把史流的衔续截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应尽量体现最新的学说和最近的发现以及以“最近的眼光”来增删资料与解释。因为“在上古和中古史中,近事的变迁,似乎是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了;但实际上却也不尽然。比如一九二一年‘北京人’的发现,一九二二年埃及的成为独立国,都是不容我们古代史的作者和读者不注意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应有两个注重:“一为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一为史迹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以求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若不求因果,但缕述某国某人,于某年征服某地,或其他类此的事实,那有什么意思呢?”“帐目式的胪举事实,或是献典式的颂扬战绩”都是不应和不可取的,“即于人名地名,本书亦力求少用,俾免枉费学生的脑力。”同时,教科书中还应适当地运用一些图表,以使学生养成看图读书的习惯。因为“表和地图,是历史的两只眼目。”各种历史表(非帝王年表,乃系著者自己所作)的适当运用“最能帮助读者得到明确的历史观念。”这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写世界史教科书所应注意的事情。如若要翻译或编译外国学者的著作教学之用,陈衡哲则认为译者或编译者必须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和“世界眼光”,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以东方人的世界眼光,不可食洋不化,因为“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 历史教学的目的是要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了解一点历史的真意义,以帮助青年们“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从而减少人类发生误解的可能,实现“人类的谅解和同情”。那种注入式的教育,在历史教学上“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它。“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要的标鹄,便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的心中。我既不敢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为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奴隶。或者因此之故,我将不能见好于许多的专门历史家及专门文学家,但我若能籍此引起少年姊妹兄弟们对于历史的一点兴味,若能帮助我们了解一点历史的真意义,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引发学生对历史学习兴趣的一种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去自己搜索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教师授课的演讲之用。 教科书固然在教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但教师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教科书减去了教师,便是一本白纸黑字的死书。”著述者的著书目的,只有依赖于教师才能真正实现。因此,陈氏“深望采用此书的教师们,能了解我编书的原旨,……我尤希望他们能帮助青年们,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的谅解和同情,也可以日增一日。这个巨大的责任,历史的著者不过能尽百分之一,其余的九十九分,却都在一般引导青年们的教师身上。” 在学习史学方面,陈衡哲特别强调要读名著。如她在指导年轻时的程靖宇先生(他与陈衡哲一家素有交情,通信频繁,并曾借住陈家很长一段时间)读书时即特别强调“西洋史古典名著一定要读,特别指定:吉朋――罗马帝国兴亡史;和时贤所写之西方‘科学史’”。不但要读名著,而且还“必须摘记大纲(out line),方才实受其惠”。 由上述可见,陈衡哲不但是一位史学家,也是一位史学教育家。  吉朋,即吉本(Gibbon,1737-1794) (2)历史学的功能 研究或学习历史有什么用?陈衡哲认为,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它在开化民智和维持世界和平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初国际国内的战乱频乃,使陈衡哲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她将之视为“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又坚信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确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运用这个方面的工具,当以历史为最有功效了”。因为历史能够通过对各种史迹的背景、史迹的因果及其彼此的相互影响的说明,“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历史学还能够帮助青年人“去发达他们的国际观念,俾人类误解的机会可以减少,人类的谅解和同情,可以日增一日,”从而可以进一步减少国际间的冲突。 同时,研究历史还有助于人们对所生活的世界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西洋历史的人,……至少应该……知道,国际的混乱状态,不但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并且是他的一个大缺点。”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起来尽一点解释的责任”,向那些“正大有人在”的、“把这个状态当作西洋文明的要素的”人解释说明,使他们消除这种错误的认识。此外,研究西洋人的历史,不但可以对西洋人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西洋人历史的了解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无论哪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特别的性质,是某种人,某国人,所专有的;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 (3)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史料的选择 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不但要学习和研究“各种史迹的背景”,而且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因为“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它“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人,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为,和于他有关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工业,农业,文学,美术,科学,哲学,以及凡曾帮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种种势力。我们不但要研究这些势力,而且还要了解他们的原因和效果”,并借此培养人们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这便是我们要研究历史的目的。” 既然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是“人类何以能从那个无尽无边的空间里,无始无终的时间里,发育生长,以至于达到他现在的地位”的历史,那么它的内容就非常的广泛了,以致人们“决不能把所有人类在空间里和时间里的一切思想事业,都当作历史看待。我们须在那漫无限制的历史材料里,整理出一个历史来”。而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人们是受到他的“历史的观念”的影响的。历史观念的不同,导致史家对史材取舍的标准不同,对史材取舍标准的不同,必然导致史书叙述的重点和对历史事件解释的不同。比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已往的政治,从而在取材上就会集中于政府的文牍公案。又比如有些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徒,他们在编写特洛伊城的历史时,就会坚定地认为,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和特洛伊城陷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特洛伊王子拐走了希腊美人——海伦,而是因为特洛伊城与希腊在商业上产生的竞争和嫉妒。“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历史的材料是无限的,“任凭你用哪一个观念,都可以得到一点材料来做凭证”。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取舍史料呢?陈衡哲指出,“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的编撰与研究中,史家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与解释应当是多纬度的。对于当时所备受推崇和倡导的唯物主义史学观,陈衡哲有着不同于众人的认识和看法,她坚称尽管她自己曾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但却不“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不认为唯物史观是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唯一工具”,也“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唯物史观有它的流弊,唯心史观也有它的缺陷,但二者决不是根本对立的,二者“实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 陈衡哲的史学观念是一种进化史观,这也体现于其《西洋史》的编纂之中。《西洋史》的写作主线是人类文化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该书的整体写作上按照时序论述了希腊文化的精神(和谐与审美的态度,及中庸的人生观);中古的三种基本精神(出世观念、一尊观念和个人主义);近代的文化精神中心(个性的表现);最后分析了科学发达的影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冲突)。而且还表现在其各章各节的写作之中。如陈衡哲在该书的导言中即明确提出:“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在描述“先史时代”的部分,这种史观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先叙述了地球和生物的起源,其次简述了人类的始祖人猿分布和进化,最后是石器时代——西洋文明的萌芽,她的结论是:“人类的文化是他的需要和环境交迫出来的。”  海伦与特洛伊之战 (4)研究历史的态度 历史的研究应将之放入其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行研究,不可以近人的眼光来认识古人的行为。“我们研究历史时,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成人的行为,决计不能与小儿一样;我们不曾因为成人不吸乳,便讥笑小儿的吸乳。历史也是如此,上古人和中古人的行为,在今人眼光中,有许多是奇怪可笑的,有许多是可骇的。比如中古人的焚烧异教徒,确是一件极残酷的行为;但我们若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他,便能明白为什么有许多慈悲诚恳的教士,也不惜以这个惨刑施于异教徒的身上。因为历史家的态度,是要求了解一切过去和现在的现象的。比如他一方面不妨批评和责咎十字军的混乱乌合;一方面却应该明白那时群众的心理,给他们以相当的同情。”“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他的。”这种明白是以上述研究历史的历史态度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对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宗教革命的叙述中,更是体现了这一历史的研究态度。 “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他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高飞深蹈,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他的范围来。但这个张网的特权,也自有他的代价。教会所以能获到如此大权,实是由于中古初年时,他能保护人民,维持秩序,和继续燃烧那将息未息的一星古文化。换句话说,教会的大权,乃是他的功绩换来的;但此时他却忘了他的责任,但知暖衣美食,去享他的供给快乐幸福。这已在无形中取消了他那张网的权利了。而适在这个时候,从前因蛮族入寇而消灭的几个权府,却又重兴起来,向教皇索取那久假不归的种种权势。于是新兴的列国国君,便向他要回法庭独立权,要回敕封主教权,要回国家在教会产业上的收税权;人民也举起手来,向他要回思想自由权,读书自由权,判断善恶的自由权,生的权和死的权;一般贫苦的农民,更是额皮流血的叩求教会,去减少他们的担负。可怜那个气焰熏天,不可一世的教会,此时竟是四面受敌了。” 但这又何足奇呢?教会的实力,本只是一个基督教义。他如小小的一颗明珠,本来是应该让他自由发光的。可恨此时他已是不但重锦袭裹,被他的收藏家埋藏起来;并且那个收藏家,又是匣外加匣,造巨屋,筑围城的去把他看守着,致使一般人士不见明珠的光华,但见一个围城重重,厚壁坚墙的巨堡;堡外所见的,是守卒卫兵的横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 各方面对于教会,虽因上述的种种原因,而发生不满,但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尚无反叛之心,他们的态度,都是倾向于和平的。无奈一方面则有教会的怙恶不悛,他不但不知改悔,反以严刑酷罚来箝制反对者之口;他方面又因教会的复杂性质,遂至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欲改良他的一部分者,有欲止不得之感。于是除去少数忠于教会之人,仍主张以缓进之法,去改良教会外,大多数的人,便铤而走险,如悬崖转石,欲罢不能,终于演成那个世界无有,欧洲少见的惨剧,宗教革命了。”  (5)历史的分期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本着“自人类学明,而西洋历史不从埃及始;自生物学明,而人类的历史不从造物抟土为人始”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认识,将一战之前的西洋历史分为古代史(又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个历史时段。其中,上古史起于先史时代,终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中古史上承上古史,下逮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近代史起于文艺复兴,终于1914年的欧洲大战。 为什么要进行历史分期,陈衡哲指出,这完全是出于“便利的缘故”,而实际上“历史的性质,是贯一的,是继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联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而如果一定要进行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个历史分段的地方,大约总是有一个,或是数个,较为重要的史迹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些界线都是人造的,我们决不能说,在××××年以前,欧洲的事事物物都是中古式的,到了××××年正月初一日的子时,人们忽然从中古的梦中醒过来,来过他们的现代生活。“历史上的分期,正如昼夜的分期一样:中午确是白天,半夜确是夜间,但在那暮色苍茫,或是晨光曦微中,谁能执定哪一分钟属于夜间,哪一分钟属于白天呢?但这个模糊不明的苍灰天色,却又是划分昼夜的最好界线呵!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应用历史上的分期”。 对于一直存有较大分歧的近代史起始界线的划分,陈衡哲自己有着明确的认识与划分标准。在《西洋史》中她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陈衡哲指出,欧洲的上古历史和中古历史的分期是较为简单的,因为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中古史开始的时期的,“我们现在也不妨沿用他”。但中古与近代的分界线就不是如此清楚明了了。已有的“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灭东罗马帝国)说”和“1492年(哥伦布于该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说”,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文艺复兴和它的两个“化态”——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时期归属问题。因此,“我便把中古和近代的界线,提早了一二百年,把他放在第十四纪的初年。那时文艺复兴的花,即已在意大利含苞待放,而近代的国家形势,社会制度,也适于这个时期间,长成羽翼,渐取中古的重要制度而代之了”。至于为什么要把十四世纪初期作为欧洲近代史的起点,陈衡哲认为第十四世纪初年的欧洲产生了许多表示中古末日的史迹: “第一,因为一三二一年,是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死亡的年岁;而一二0四(原文如此,若参照下文,当为一三0四年——引者注)年,又是依洛司马(Erasmus)出世的一年。但丁是中古文化的结晶,同时也是近代文化的一个先锋,而依洛司马又是文艺复兴上升期的最好代表。所以用这个时期来结束中古的文化史,是最为切当的。第二,因为这个时候,适是教会的权力全盛将衰,国王的权力起而代之之际,而教皇的迁居法境,也是在一三0五开始的。教皇制度是中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子,他的衰落,自然就是中古文化衰落的表征。第三,因为第十四世纪开始,西欧的列国,已经成立,已经能代替中古的封建制度,来维持适合的秩序了。而列国的对立,却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十四世纪中叶,英法百年大战的开始,是日耳曼各民族建国以来第一个国际大战,也是近代国际混乱史的一个小影。第四,因为宗教改革,和大发见的两件事,虽然要到了第十六世纪初年,才大显著;但在第十四世纪时,已东现一芽,西抽一苗,随事随地,都可以找到他们势力的存在了。而孕育文艺复兴的各大学,到了第十四世纪初年,也是质量与程度,双方并进,势力日盛一日。第五,因为城市的发达,以此时为最盛,而平民的参政权,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的。第六,各国方言的成为文学,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件大事,而但丁即是第一个能运用方言,作为优美文学之人。十四世纪初年,《神曲》(Divine Comedy)的出现,实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纪yuan。因此种种原因,所以我把第十四纪的初年,作为中古和近代的分界。我们若还必要找一个确定的日子,那么,一三0四年依洛司马之生,一三0五年教会的迁入法境,一三二一年但丁之死,一三四六年英法大战的开始,都是几个重要的日子。但其中尤以但丁之死,为最能结束中古的文化史。” 陈衡哲在世界中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这种见解(上限始于476年,下限为14世纪),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 P.S.因微信平台排版限制,原文注释等内容无法显示。需要请参考原文—— 闵凡祥:《陈衡哲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章开沅:我的文革岁月
- 下一篇:向荣:让世界史教学激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