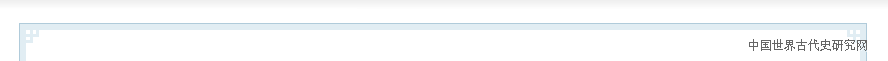 |
 |
怀旧如今已经是一种时尚,我辈虽然垂垂老矣,更应该竞起效尤。何况,当年授业于诸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离题千里
古代汉语,恐怕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最头痛的课程之一,不仅枯燥,而且难学。但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却深得人心,极少有人逃课。因为我们幸运地拥有一位优秀的师长——许炳離教授。
许炳離是名满全校的硕儒,用今日的话语界定,当属于“资深教授”。他的课,学生最喜欢听,究其原因,不在严谨,而在渊博且随意。教材上规定的内容,他常常略去不讲,而课本以外的一些鲜活的内容、生僻的典故和野史所录的传闻,特别是属于他自己的若干体悟与感受,则每每脱口而出、语惊四座。
有一天,许先生上得堂来,首先开题:“今天讲《陈涉世家》,开头是‘陈涉者,阳城人也’。”立马便从“阳城”生发开去,洋洋洒洒,越说越远,与课文的关联越来越稀疏,内容却越来越精彩,学生们听得自然也越来越起劲。不知不觉,两节课讲完,下课的电铃声响起,讲课的和听课的才从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忘我境界中惊醒过来。许先生一愣,说:“噢,打铃了!今天讲‘陈涉者,阳城人也’。”两节课里,唯有这两句,算是符合“教学大纲”的规定。
汗流浃背
1983年春夏之交,薛绥之教授来信命我随同进京,为的是商议编撰《鲁迅大辞典》的有关事宜。那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拜访他的老师,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教授,求教关于辞典编纂体例、热点词条、组成人员、编写经费等大事。按照李先生的习惯,有关问题,薛师事前早已书面请示,当面商谈,为的是解决一些非常琐碎但又不可忽略的“细枝末节”。
那天上午,我们到达史家胡同,已经十点左右。在敲门前,薛师居然问我他的纽扣是否系得对头——薛师的衣扣,往往是上下错位,或者并未扣好,虚掩而已。进得大门,只见李先生正站在台阶上,一身干干净净的毛氏制服,深蓝的;里面的衬衣,雪白的;脚上的圆口布鞋,深黑的;鞋沿上露出的袜子,又是雪白的。全身上下,干净而又得体,庄重而不板滞。李先生也许正在工作一段后稍事休息,所以我见到的第一印象,是他在仔细地掸去肘间、袖头的浮尘,那么专注,那么气定神闲。
薛师一进门,就怯生生地喊“李先生”,同时恭恭敬敬地站在台阶下面,低眉顺眼,双手垂立,简直像一个打碎了教室玻璃的一年级小学生!我从未见过我的老师如此神态,好奇极了。只见李先生未下台阶,就扬起手来指着薛师说:“薛绥之!你寄来的两封信,我早收到了。里面提的问题,我都详细做了回答,挂号寄到聊城去了。”说着,话头一转,开始批评:“我说过多少次了,你写字还是马马虎虎,那么潦草!做老师的人,这样写字,怎么给学生做榜样?字写得好坏莫论,但总得一笔一划,写得让人家辨认……”话音未落,李先生注意到薛师身边还有一个年轻人,连忙招呼进屋,倒水——白开水,吃水果——好几样,待我比对我的老师热情多了!
谈完问题,李先生就送我们出门。走出大门,薛师长出一口气,大有如释重负的模样。我见他拽起衣袖,拿下眼镜,擦着不断从白白胖胖的面颊上流下的硕大的滴滴汗珠——薛师大概从来不用手绢之类“奢侈品”,擦汗,就随手撩起,就近解决问题——方便。我问薛师:“你的老师,常常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你吗?”薛师笑笑说:“随时随地!因为写字潦草,随时随地呵!”
赋诗“下岗”
1963年,我从山东师院毕业,分配到泰安师专教书。那时的泰安师专,有一种长幼有序、以老带新的风气。青年教师可以自由地向老教师请教,而老教师也大都乐于传授教学经验和解答疑难问题。李震远先生,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之一。
听说李先生出身鲁西南巨富之家,先世以盐商为业,富甲一方。到得先生,却无意经营,偏好学问。同时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极度不满,乃出走到北京中国大学就读。20世纪50年代,先生在山东菏泽一中执教,成绩突出,从而被“上调”到泰安师专任教。
我曾经随李先生听课学习多次,每次均有收获。印象最深者,则是他讲解《战国策·赵策·触龙说赵太后》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关于“老妇”,先生操浓重的鲁西南乡音解释:“那个老嬷嬷,说她非得吐你一脸唾沫!”古语而用现代的话语“链接”,自然惹得堂下笑声一片,故至今不忘也。
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成果”,多年执教成绩不菲的李先生就只能带着“讲师”的头衔退出教师生涯。退休那天,正值中文系召开全体会议。在有关领导宣布李先生退休决定后,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凡是好人,都说我教得好;凡是说我教得好的,都是好人!”说罢,口吟五绝一首,其末两句为“教书四十年,白头老讲师”,随即拂袖飘然而去。
|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