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革命”等译名演变是文化变局的产物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35 澎湃新闻 聂长顺 参加讨论
【编者按】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追根溯源一个词的产生机制,详尽考证一个词的发展演变,不光可以认识词的本身含义,更可借此窥探词汇背后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近日,冯天瑜教授主持的“近代术语”课题顺利结项,专著成果《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出版,是为概念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那么,什么是概念史?概念史有着怎样的研究范式?澎湃新闻邀请该课题负责人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聂长顺教授,分享其概念史研究的成果与心得。 聂长顺教授 何为概念史? 澎湃新闻:请介绍下您的学术经历? 聂长顺:我本科学的是教育学,硕士读的是外国教育史,毕业以后分配到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做日本教育研究,按学科来说属于比较教育领域。其实我对历史感兴趣,师兄经常复印一些好的历史文章给我看,其中大部分是南开老师写的,因为南开日本史研究水平很高。后来考博士,南开老师提前招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了南开大学历史所。我就在历史所日本史教研室老师组建的日本研究中心里,现在叫日本研究院。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经人介绍来到武汉大学跟着冯天瑜先生做博后,一下又跳到中国文化史领域来了。冯先生接收我,可能是考虑到我有日本研究和留日经历,具备做概念史研究的功底吧。博后出站后,我留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一直从事概念史研究。 澎湃新闻:您在概念史研究方面有很多成果,可否介绍下您的研究历程?冯天瑜先生对您有何影响? 聂长顺:2004年我来到武汉大学跟着冯先生做概念史研究,重点探究西学东渐背景下出现的术语译名的厘定问题。近代以降,中华汉字文化遭遇一场古今转换、中西碰撞相交织的文化大变局,而汉字新术语的生成与演变则是这一大变局的产物与表征。近代厘定的名词、术语,许多至今仍在使用。对它们的形成过程予以探究,是文化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非常有限,许多重要史料尤其是中国史料难得一见。我首先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日本,因为日本是中国近代术语的重要来源地,而大部分史料可以通过网络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查到。我的博后出站报告《近代汉字教育术语生成研究》就是这么形成的。 我博后刚一进站,冯先生就应聘到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日文研”)主持“东亚二字概念形成”研究的“代表者”去了,许多概念史的重要研究者参加了这个研究团队(日本称“冯班”)。这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使我一下子接触到了核心研究群体,并和日文研结下不解之缘。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的研究都和参与日文研的学术活动是分不开的。 从2007年开始,冯先生主持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当初申报时,课题组的阵容很强大,有日文研的刘建辉、铃木贞美二位老师,在德国工作的方维规、梁镛二位老师,北外大的朱京伟老师、华中师大的刘伟、周光庆老师等。我是跟着冯先生做这个课题成长起来的——不仅我一个,包括参与项目执行的许多年轻人。到2014年结项,发表论文成果近百篇,限于篇幅,最后纳入结题报告的仅是其中一部分。通过交流得知,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一直受到国内外同行关注,并获得好评。相信已经出版的结项报告《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也是对概念史研究有所贡献的一部大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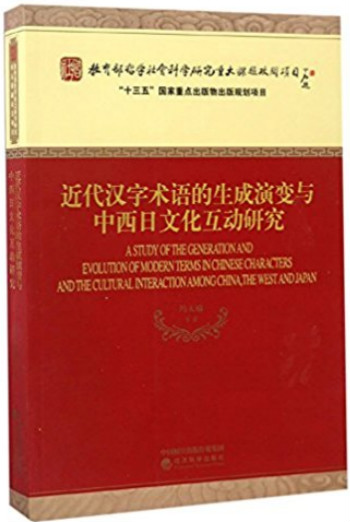 《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 澎湃新闻:近些年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史、观念史等研究受到很多学家关注,可是这些名词在使用上似乎有些混乱,导致部分读者对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认知模糊,您能否帮大家厘清一下? 聂长顺:确实各种名称都有。其实,概念史并不是新近之物。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樊炳清《哲学辞典》即有“概念史(英History of concepts,德Geschichte derBegriffe)”一条。其释义称:“就特殊之事实的认识,而叙述其变迁发达之迹者,谓之概念史。所以补哲学史及特殊科学史之不足。此德国学者特伦对伦布(Trendelenbury)所始命名,后有米勒(Muller)、倭铿(Eucken)、何辉尔(Whewell)、文得尔班(Windelband)诸家咸承其说而沿袭之。”1893年初版的文德尓班《哲学史教程》堪称以概念史补哲学史之不足的杰作。当然,这时的概念史还只是作为一种方法的概念史。就当下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实践来看,概念史既是一种方法,似乎又将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或相对独立的学问。 我第一次听到“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个名词是在2006年12月,当时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文研合办学术会议,冯先生拟定“历史文化语义学”作为主题。其宗旨是:使近代术语的研究提升、延展至文化史、思想史层面;使文化史(包括文化交流史)精确到词,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其理路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时空坐标上,对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且透过语义的窗口,探寻语义变迁中的历史文化蕴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状貌。 冯先生的《“封建”考论》便是这一学术范式的代表作;《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也属于此类。当初冯先生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表面上看,是在“历史语义学”里加入“文化”一词,实则有其学理考虑:德国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是在西方语境进行,基本只有古今问题;而东方人做概念史则不仅考虑古今问题,还要考虑东西问题,是跨文化的。所以加入“文化”,很精妙。 以我个人的看法,在名词使用上有些混乱,这主要是一般读者的印象,就学界的研究实践来讲,并没有混乱。研究者以何自名,乃是出于他对自身学术实践的体认。无论以何作为“共名”,实际上都包括着以其他名词命名的研究。大家所做的基本工作是:考察一个词汇、术语、概念的历史变迁过程,探究其古今间隔的成因。 从我自己来讲,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称为“译词文化史”。因为就我们的学术实践而言,研究重要的节点在于东西文化交会,我们研究概念的翻译历程,是在追索“译词”的轨迹过程中讲述东西交会、古今演绎的文化故事。 “封建”“教育”“革命”的译词形成过程 澎湃新闻:您对“伦理学”“教育”“元素”“封建”等许多概念进行了考辨。这些概念对人们认识近代社会、文化、教育的演变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聂长顺:还是那句老话: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词汇是重要的文化事象,可谓一词一世界。我相信,追寻每一个译词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在讲述一个文化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很有趣。比如:中国古典词“封建”经与西方feudalism(feudal system/the feudal)对译,演变为剪裁历史的近代概念。我经过检阅史料发现:林则徐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以“封建”指称西政,露密士等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以“feudal”指称周制,只是这一过程的序曲。真正在名、实两层面使“封建”与feudalism达成对译通约的是丁韪良撰、汪凤藻译《中国古世公法论略》(1884年)。近代中国新名“封建”谱系也含有与日制“封建”相互叠加混同的部分。新名“封建”的严复首创说、独创说及日源说均不能成立。但就译词本身的故事来说,讲起来就很有趣。 当然,每个词的思想文化含量不尽相同,有趣的程度也不一样。讲述它们的故事,会在纵向上为人们提供认知的景深,甚至可能刷新人们头脑中的已有的世界图景。每一个概念,在译词确立之前,都经历了一个译词多样化阶段。把这个阶段呈现出来,很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译词确定之后引起的认知固化。 比如西方的education概念,在定译为“教育”之前,曾被译作“文学”、“学问”、“学术”和“学”等。就是说,education的翻译史中很可能隐含着对education的认知从“学”到“教”的转换过程,很可能有助于人们从“学”的侧面对education进行再认识。再比如“伦理”“道德”,我们现在是区别使用的,通过译词史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区分其实是近代译者造成的,而在近代英语文本中ethics、moral philosophy和moral science 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弄清这一点,有助于保持跨文化对话间的信息对称。 我所涉及的译词,以学名为多。因为我认为,知识或学问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捋清了近代学名的成立过程,也就同时捋清了一门学科的成立的轨迹,至少是掌握了学科史的文本脉络。至于中国的分科学术史,则是近代学人将近代概念投射到本土的历史空间之后“再发现”出来的谱系。译词的文化故事如果这么讲下去,应该更有趣。 澎湃新闻:您长久以来一直关注“革命”这一概念,相关文章也在日本发表,可否谈一下您的见解? 聂长顺:“革命”概念,早有学者研究过。但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做概念史,注重起源、转折及定着这三点。不搞清楚这三点,就算没有完成任务。我着手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revolution的翻译历程,依时序胪列出了revolution诸多译名,写成『中日間におけるRevolution翻訳の一考察』一文,日本创价大学『創大中国論集』第18号(2015年3月)。继而我又以“革命”为着眼点,考察其意涵的古今演绎、东西对接的历程。其中近代部分已经成文,名曰《近代“革命”再考察》,在《人文论丛》2017年第二辑发表。 就迄今的研究来讲,可以说稍有新得。比如:第一,就中国古代“革命”而言,我发掘了中国“革命”背后连带的权力正当性理论,即“顺天应人”,而“民心”是“天意”的实际来源与内容;为“君”者须是“四有人才”,即有命,有德、有土、有群。 第二,就日本古代“革命”而言,我发掘了日本“辛酉革命”这一千年惯习,发现在这惯习下,日本人以“改元”替“革命”以“应天道”,即中国古典“革命”背后的“天命”观念为“天道”所替换,从而演变成无“命”之“革”。 第三,近代新名“革命”的诞生,日本学界确认为1864年出版的村上英俊编著的法日对译词典《佛语明要》。我经过资料调查,发现1836年出版的日本兰学家宇田川榕庵《舍密开宗序例》中有“西土中兴革命”一语;1845年刊刻的日本儒学者羽仓简堂所撰汉文著作《通鉴评》有“郡县天下,始于祖龙;匹夫僭称,始于陈胜。秦季二十余年,实为一大革命。”从而把新名“革命”的起源往前推进了近三十年,也为《佛语明要》译名“革命”的厘定找到了历史依据。 第四,关于日制“革命”在中国的用例,陈建华认为以王韬的《重订法国史略》(1890年)为最早;金观涛认为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为最早;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则在“孙中山等中国近代革命者对‘革命’的认同与改造”题名之下,探讨了“‘革命’一词何时成为孙中山等人的中坚语汇”这一问题,认为“孙中山以‘革命’自任,形成于1895年底至1898年两次逗留日本期间”。而我把这一点前移到了1879年5月15日《申报》(上海版)第2167号载《译日本人论亚细亚东部形势》中的“戊辰革命”。 第五,运用“历史文化语用学”范式,发掘了近代国人将近代“革命”建构成中国固有之物的案例。如:欧榘甲将“民主”“革命”建构成中华“道统”,且赋予它以时空普适性;汪精卫则编制出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谱系。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我还要继续努力。 概念史研究现状 澎湃新闻:现在日本学界有关概念史的研究现状如何? 聂长顺:日本这方面研究,历史长,学者众,成果丰,最为可观的是集团作业局面的形成。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日文研这一学术大平台。其中,刘建辉和铃木贞美二先生居功至伟。冯先生2004年去日文研组织“冯班”时,合作教授便是刘建辉。“冯班”聚集的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学术前辈有飞田良文、柳父章等;中坚力量有铃木贞美、沈国威、陈力卫、黄兴涛等。此后连续数年,刘和铃木二位依托日文研,召集各国代表学者,举办概念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铃木先生说的那样,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运动。后来,会议论文集由铃木贞美和刘建辉主编,陆续在日文研出版,如:《东亚知识体系的近代再编》(2008)、《东亚近代概念与知识的再编成》(2010)、《东亚近代诸概念的成立》(2012)、《为了东亚学艺史综合研究的持续发展》(2013)。2006年12月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则由冯先生、刘建辉和我主编,在国内出版。就最近几年而言,“汉字文化圈近代语研究会”堪称重镇,其主要成员也是日文研概念史研究运动的参加者,旅日学者沈国威、陈力卫二位老师居核心地位。  《语义的文化变迁》 澎湃新闻:与孙江、黄兴涛、李里峰等学者的研究相比,您的研究理路有何异同? 聂长顺:从基本面上来看没什么区别。作为概念史来讲,离不开词。方维规先生曾说,概念史不光是词的问题,涉及到没有形成词的时候,它的概念隐藏在一句话的表述当中。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我还以为,既然是概念史研究,就必须抓住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扎实的史料。做中国的概念史,尤其近代部分,必然涉及到西学东渐及翻译,即所谓“语言的接触”,必然需要多语种的资料做支撑。简言之就是纯考证,即史料的排比铺陈,这是最基本的。 曾经有位老师说我是抓住词汇这一点,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文化史的周游。我想,这一说法也算客观吧。至少有些词的考察,中—西—日这个环,我依据史料画得比较完整。另外,在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新名词与传统重构》的研究中,我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历史文化语用学”的学术范式。即如前述,在弄清新名词的来龙去脉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近代学人是怎样用的,是如何把它们投射到中国的历史空间,再建中国的“现代传统”的。 澎湃新闻:金观涛、刘青峰的著作《观念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一部作品,通过数据库统计关键词频率来研究近代重要政治术语的起源和演变,很有新意,读来也饶有趣味。不过也有学者质疑其统计方法在解释思想文化方面的真正效果,对此您怎么看? 聂长顺:先说“观念”这个词的运用,其实不太好。从心理学上说,观念不是一种很明确的概念,当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或一句明确的话来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这种状态的意识叫做观念。金观涛选择用观念而不用概念,这是值得推敲的。 至于他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当然有其便利,但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本书很注意词频的作用,但是一个词对人们的影响不能拿它出现的频率来证明。有些话的影响大小还得看谁说,人厉害,说一遍就够;不厉害,天天说也不管用。统计方法无法说明影响与接受层面的东西,因此是比较平面的呈现,无法反映“人云亦云”这一传递的过程,也无法说明每一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研究当初预设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性的想法是可取的,自有其价值,但无法代替个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历史研究须处理好古今关系
- 下一篇:历史研究须处理好古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