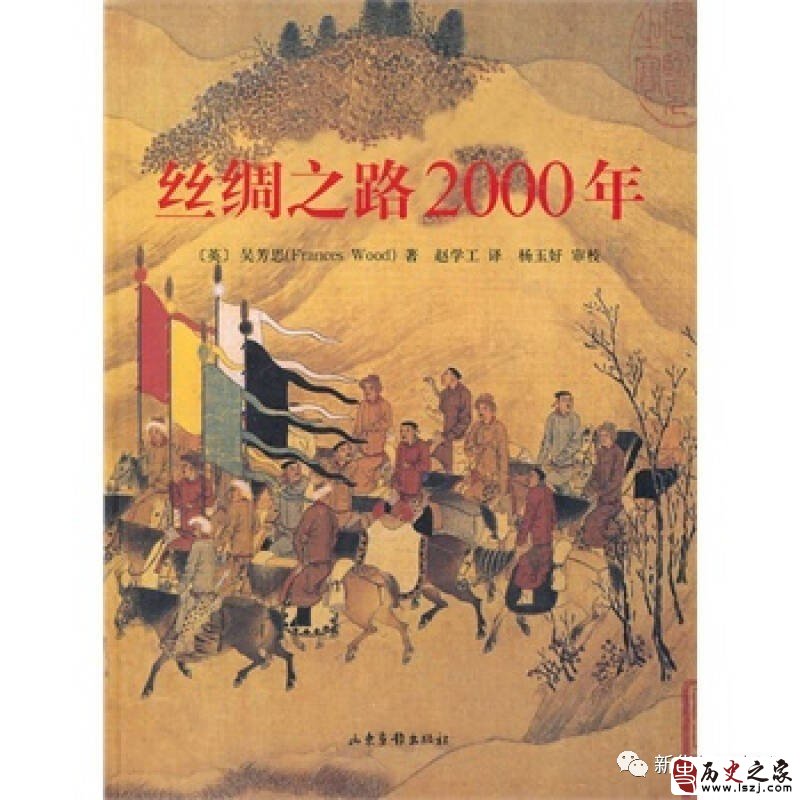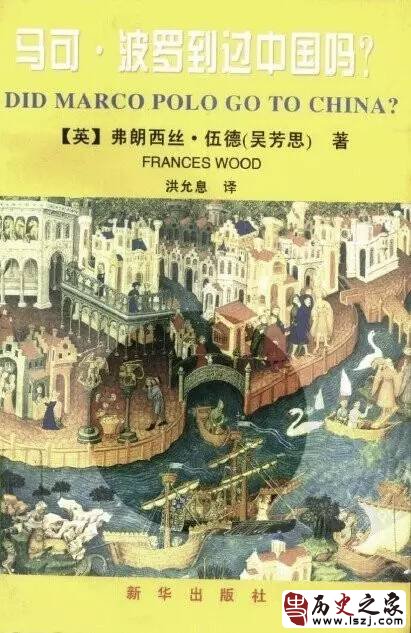【导读】在英国,吴芳思(Frances
Wood)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质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守护并表示“不会舍不得归还”敦煌经卷
大英图书馆“掌管中国历史”的老太太
首发:7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桂涛
吴芳思的家很好找,门前有一小片竹林,门头挂着一条红纸做的游龙——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伊斯灵顿显得颇有些特立独行。
竹子是林语堂的女儿住在伦敦时从家里拿来的,龙是吴芳思儿子的属相。69岁的吴芳思延续着她和中国40多年的缘分。
在英国,吴芳思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挑战者”吴芳思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认为孔子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反对“有组织的宗教”,从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退休后第一天就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
退休后的吴芳思独居,她的家比想象的要“寒酸”。沙发、桌椅都旧了,厨房里杂物堆得满满的,小客厅四壁全是书,白天不开灯就显得昏暗压抑。
她喜欢猫,书架上除了各种木头玩具外,还摆着好几只从中国买回来的瓷猫。采访中,一只常来她家的猫也按时到访。吴芳思摸着它的脑袋,介绍这只被她用邻居家小男孩的名字命名的流浪猫。
在英国学术界,吴芳思显得有些“另类”,是个不折不扣的“挑战者”: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她质疑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17年的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一个证据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她坦言自己不喜欢孔子,认为这位儒教的圣人在礼仪方面太挑剔;
她反对“有组织的宗教”,认为宗教仇恨与隔阂是西方历史上无数重大冲突的源头;她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是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位阶最高的职员之一,但却在退休后的第一天,就在媒体上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吴芳思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理论再看看、再想想。
“用‘挑战者’这个词形容我似乎有点重了。”吴芳思说,“但我确实是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对历史和现实问题重新思考,他们不一定非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
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吴芳思给人的感觉是,爱扮鬼脸,有点调皮,语速很快,句句斩钉截铁,总让人觉得,她的内心还是个小姑娘。追溯她的众多“挑战”行为,也许正来源于当年那个爱瞒着老师、往口袋里藏东西的小姑娘。
幼儿园时的吴芳思总是在午餐时偷偷把不爱吃的羊肝藏在口袋里,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在“安安静静地反抗老师”。后来稍大一些,别的小姑娘在学校都选择学吹笛子,吴芳思却选了少有人选的双簧。“当你的选择和别人不同时,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也许也为她之后选择学当时少有人学的中文埋下了伏笔。  吴芳思
爱读书,是“终极热情”
“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吴芳思从小爱读书,这和她后来展现出的语言天赋一样,都是受父母的影响。她父亲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专业是中世纪法语《圣经》研究,毕业后以法语专家的身份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工作,是编排图书目录的好手;母亲是个中学法语老师,“喜欢干活儿,整天闲不下来”。
在吴芳思的记忆里,父亲很聪明,常有人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维。他是个坚定的无宗教信仰者,这导致吴芳思后来对宗教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她认为“有组织的宗教”会让人变得盲目、让人行为受限、会导致宗教仇恨与杀戮,这一观点也许正是发端于此。
后来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保管中国佛教经卷时,曾和一个日本老师学习打坐冥想,但也没有成功,因为她“没办法什么也不想”。
吴芳思认为,有些中国人虽然信仰宗教,但不墨守成规、不教条。“中国人说,在办公室里是儒教,退休后是道教,这就是不束缚于某种‘有组织的宗教’。”她说。
吴芳思从小数学不好,也不喜欢体育,只是爱读书,说那是她的“终极热情”。她记忆里,11岁以前常去家附近伦敦海格特的一家旧书店淘书、买书,回家看完了,就再卖给书店,买更多的书。
吴芳思说,回想起来,父母在各个年龄段将“正确的书”推荐给了她。十几岁时,她爱读英国作家高斯的《父与子》,会去伦敦书展上找童书作家安东尼·巴克里奇签名。甚至直到现在,她还喜欢读巴克里奇的书。
对书的热爱影响到了吴芳思后来的择业。大学毕业后,她本想进博物馆,“天天和器物相处”,但后来大英图书馆邀请她去,她欣然接受:“大英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古书旧书,所以也可以算博物馆吧。”
直到今天,吴芳思丝毫不隐藏她对书的喜爱。每当提到她写过的书,她都会起身去书房拿来,赠送给来访者。吴芳思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甚至比上班时还忙”。
她即将在英国出版的就是一本名为《中国那些伟大的书》的“书之书”。在此书中,她将向西方读者介绍60本她眼中的中国好书:《诗经》《浮生六记》《小二黑结婚》《毛主席语录》《干校六记》……
吴芳思觉得,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记得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时,司机在读《福尔摩斯》,“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在大英图书馆,Frances Wood博士向都本基一行展示珍贵的馆藏东方文献。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中文,“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
回想自己的一生,吴芳思说,也许她做得最“有挑战性”的事就是选择学中文,这个“决定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也始终让她感到庆幸。
因为父母的影响,吴芳思从小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她在上中学时想选择一门“越难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语,并最终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文,并一直坚持到了大学。
当时的英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牛津、剑桥等4所,牛津只有两名中文老师,吴芳思因此选择进入剑桥。“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吴芳思回忆大学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根本没时间顾这些。
偶尔闲暇,吴芳思喜欢给她的室友烧饭,常常搞些创新,比如试试中东菜,用羊肉丸子烩虾仁,用植物染料给米饭染色。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爱抚摸中国的小陶器,摹画上面的花纹。她的大学论文题目是《从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
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汉学家的大本营之一,吴芳思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她记得,那些给她上过课的汉学家各有特色:后来《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人鲁惟一喜欢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学希腊语”;荷兰人龙彼得非常不喜欢学生在论文中使用太多“某某主义”这样的大词;
还有从牛津赶来给他们开系列讲座的《红楼梦》译者大卫·霍克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吴芳思到现在也常常玩味:“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吴芳思。图片来源:China Daily
在北京练习手榴弹
“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人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几乎没什么贫富差距”,40年后回想在中国“文革”时的经历,头发花白的吴芳思更多的是强调,当时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吴芳思曾两次到访文革中的中国,这两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更让她对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理解更深。
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后给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留下250镑。她因为有这笔钱,再加上会说中文,于是被允许参加了文革开始后到中国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和“一些非常‘左’的英国学生”同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
在中国,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去了刚刚修好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让中国人骄傲的拖拉机制造厂,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因为对建筑感兴趣,吴芳思还在一个村子和木匠聊了很久,研究他们的工具和技法。
吴芳思回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文革的存在。”她认同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用“还好”来描述那时的中国。吴芳思后来写道:“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的青翠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吴芳思再去中国已是1975年。文革期间,中国与外界交流很少,当时学习中文好比是学一门“死语言”。为了到中国练中文,吴芳思和其他8个英国学生一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交换项目,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
作为交换生来到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学英语、闹革命”为使命,却见到了和描述中大相径庭的英国。而28岁的吴芳思则发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那时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20个朝鲜女学生合用。”但在吴芳思眼中,北京与中国和她上次到这里时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欢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命名——“绯红”“杏黄”“酱紫”,喜欢中国人把猫头鹰称为“猫头鹰”,这些命名在她看来,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的描述”。
在文革末期的北京,吴芳思发现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冲突了,但“树上的喇叭里不时传来政治宣传,这种宣传只有在播放又一位老革命家逝世的消息时才会中断。”但吴芳思隐约感到,“似乎会要有改变”。
吴芳思在回英国后所著的《在北京练习手榴弹:我在文革中》一书中写道,自己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挖防空洞;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必修课;体育课上,要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手榴弹投弹训练……
40年后回想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头发已经花白的吴芳思除了讲述那场政治运动外,更多的是强调她对北京的喜爱: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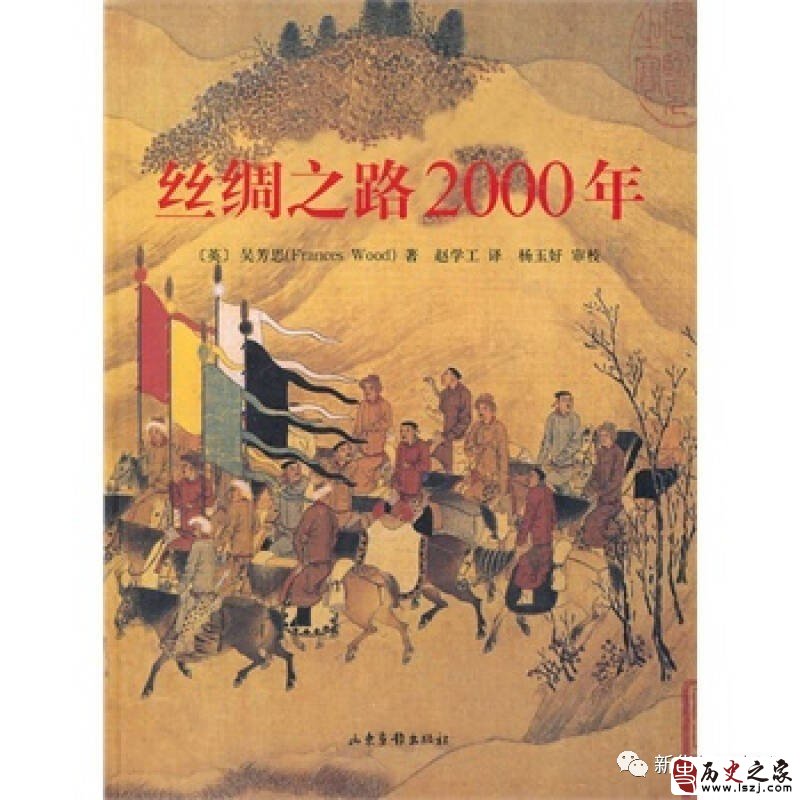 吴芳思的著作《丝绸之路2000年》封面。
守护敦煌经卷
“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
就在吴芳思离开中国后一年,她所预感到的“改变”终于来了。文革结束,这给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去西方研究机构学习的机会,回到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吴芳思也继续有机会和中国人接触。
那时,大英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用14块马蹄银换走了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发现的经卷,从此它们就成了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
经卷记述的内容从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珍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谈到敦煌经卷,吴芳思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总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天天守护这些宝贝。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这让她很自豪。
“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吴芳思说,“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吴芳思向来对纸张很着迷。她管理的图书馆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岁的《金刚经》以及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那之后1000多年,欧洲人才造出第一张纸。
敦煌经卷中,除佛经外,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通过它们,吴芳思看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她对敦煌这个位于丝绸之路南北路分界点、将这条东方贸易之路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吴芳思在她的《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一书中,详尽描绘了丝绸之路5000年来的兴衰,追溯这条西方人笔下浪漫又危险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丝绸之路有极大的兴趣,路的那头就是神秘的中国,那是茶叶与丝绸的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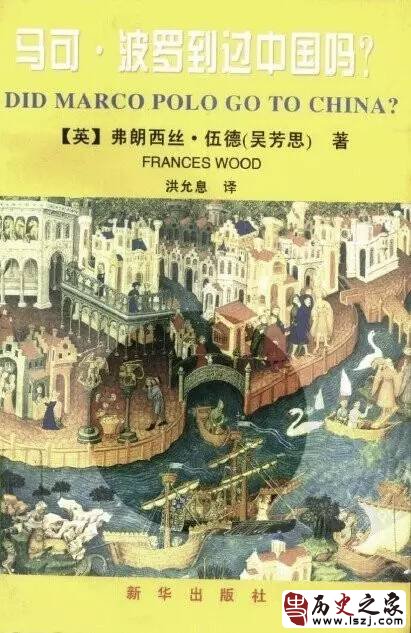 吴芳思著作《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封面。
“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吴芳思认为,即使是在朝发夕至的今天,“去中国”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还是一项成就与壮举,“就像他们去的是月球”。中国独特、遥远、浪漫,与西方如此不同,一方面吸引人,另一方面又显得无法穿透。“今天,我也不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过去相比进步很多。”吴芳思说。
她反感那些仅仅因为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就盲目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想想北爱尔兰那些年不停发生的爆炸,看看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她鼓励西方人不要因为汉字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文难学,她认为学者更应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吴芳思曾邀请多位中国敦煌学专家来英国共同研究敦煌经卷,并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对他们关怀备至。她说,当年斯坦因去敦煌时,他的助手就是一个识字、但不懂佛经的中国官员,正是他与不认识汉字、但却多少知道一些佛经词句的斯坦因合作,才让敦煌经卷得以重见天日。
“某种意义上说,从发现敦煌经卷时起,中国人就在与外国人合作吧。”吴芳思说。她同意把斯坦因称为“强调”,只不过是一个“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些经卷的强调”。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在那本《中国的魅力:趋之若鹜的西方作家与收藏家》中,吴芳思挑选出大量关于中国的精彩记述,用西方人的小说、回忆录、随笔等追寻了那些和她自己一样,“仿佛是中国造就”的西方人:探险家赫定和斯坦因、作家毛姆和安·布里奇、艺术鉴赏家阿克逊和韦尔奇、记者弗莱明……
吴芳思说过:“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当被问到她是否已经是半个中国人的时候,吴芳思说:“可能不到半个吧,我还应该学更多的中文。”但过了一会儿,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择“留欧”的她又调皮地补充道:“但‘脱欧’后,我又算多少英国人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