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页)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季先生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如此为《列子》成书断代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张湛《列子注序》称“遭永嘉之乱……仅有存者”云云,对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一段凑成一部《列子》。”此说则可商榷。其实古人编书和传播书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为例,其《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甚至连“机关木人”也被套装在“穆王西巡狩”的叙述中。《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因此,《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而特别令人惊喜的是,《生经》的译者竺法护也是《移山经》的译者!而“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也都见于《列子·汤问》篇!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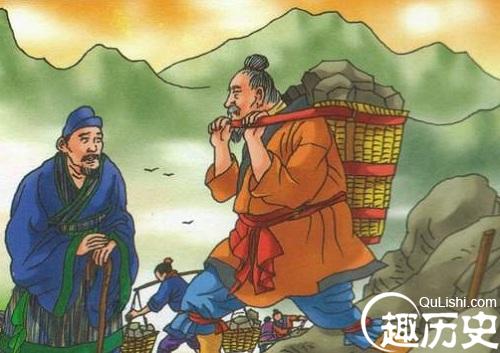 《佛说力士移山经》,又称《力士移山经》或《移山经》。南朝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第二:“《移山经》一卷,旧录云《力士移山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页)隋沙门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第三:“《移山经》一卷,一名《力士移山经》,晋世竺法护别译。”(《大正藏》,第55册,No.2146)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十三:“《力士移山经》一卷(或直云《移山经》),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大正藏》,第55册,No.2154)其作为法护译经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移山神话乃是中古时期佛典的常见物语。我们试读: 昔佛在王舍城竹园中说法,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后七日,皆当命尽。自共议言五通之力,反复天地,手扪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晋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第一,《大正藏》,第04册,No.0211)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大正藏》,第04册,No.0212),东晋太元时期的名僧竺昙无兰所译《佛说忠心经》也有关于“梵志三尽道力”的移山故事(《大正藏》,第17册,No.743)。凡此均导源于《移山经》,由此足见其流布之广与影响之深。《移山经》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这一点比较容易发现,而另外两个“前文本”则相对深隐: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卷第三《北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所谓“北山愚公”与“河曲智叟”之名,即从《论语》所载孔子“上智”“下愚”之说而来,《列子》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故“上智”与“下愚”是“可移”的,而非“不移”的;其次,“愚公移山”的寓言乃是针对《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神话摄取天竺佛典而创作的(如《山海经》夸父逐日的神话被《列子》摄取,其文本位置紧随“愚公移山”之后,见杨伯峻《列子集释》,第161—162页),移山与填海正好匹配,因为这两个故事张扬了同样的人文精神。如果没有精卫填海的神话,也就不会有“愚公移山”的寓言。基于《列子·仲尼》篇的儒学语境,我们对“愚公移山”与《论语》之关系尚可深入讨论。《论语·子路》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 孔子并非鄙视劳动,更非鄙薄体力劳动者,而是客观说明其与农圃社会分工之不同。《孟子·滕文公》所载孟子关于社会分工的言论实际就是对孔子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结论是: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4页) 而《列子》“愚公移山”的寓言则张扬了劳心者未必智、劳力者未必愚的人类平等思想,于是,我们看到了“叩石垦壤”、志在移山的劳动人民的身影。在魏晋门阀世族主导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人文景观!在张扬儒学的同时,《列子》又援佛入道,融化西来之佛学思想,以沟通释、道二家之津梁,其孤明先发已经为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文化融合导夫先路了。在儒释道合流的前夜,在历史天宇的深处,《列子》仿佛是一颗幽栖的孤星,虽然光彩熠熠,而周遭的却是难以穿越的寂寥。《力命》篇仿佛是日神的恣意欢歌,《杨朱》篇仿佛是酒神的猖狂舞蹈,其作为全书之核心(其他六篇都是对此二篇的“学术掩护”),无疑是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王肃(司马昭的岳父)构建的伪儒学以及在此伪儒学支配下的行为方式相背离相抵牾的(王氏公然伪造孔子言论,编成《孔子家语》《圣证论》和《孔丛子》三部伪书),故《列子》的作者不得不托名于古人,不得不暗淡了自我。因此,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列子》是伪书的话,那么,我更愿称它为一部杰出的伪书!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