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二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两年间,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和干预欧洲的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这场外交大辩论不仅仅是围绕美国如何应对欧洲战争这一具体政策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即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民主和人民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大辩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思想和外交观念,使强调美国大国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孤立主义者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了,但其思想在战后仍然对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关 键 词:孤立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 外交辩论 国家身份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德国入侵波兰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两年多时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辩论”(Great Debate)时期。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大辩论展示了美国社会在美国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围绕外交政策的政治斗争”①。大辩论使自由国际主义思想②深入人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走向,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场外交大辩论,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研究,但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孤立主义一方,对国际主义者的主张语焉不详,特别是对大辩论的意义阐释不足。③而在我国,除少数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场大辩论略有提及外,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对这场外交大辩论的过程进行梳理,并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来揭示这场大辩论的主题及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意义。 一、辩论的由来与过程 从美国陷入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相对超然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美国的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参与,以远离国际纷争与冲突。在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面对30年代的欧亚国际危机和战争,美国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国会相继通过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中立法》,试图通过禁止与交战方进行商业和金融往来避免美国再次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国际局势使国际主义者开始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9月8日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取消军火禁运,把1937年《中立法》的“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以便使握有制海权的英、法等国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随后,罗斯福总统又相继提出其他动议,包括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向国会提出为反轴心国家提供租借援助,为美国商船护航,对德国潜艇进行攻击等,带领美国一步步走上干预欧洲战争的道路。从提出修改《中立法》开始,罗斯福政府的这些行动引起一些人士的激烈反对,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外交大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向英国和其他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方主张美国应修改或取消《中立法》,向英、苏等国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战胜德国。其中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为了阻止希特勒称霸欧洲,即使美国直接参战也在所不惜。这些人通常自称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但常被对手称为“干涉主义者”(interventionist)。另一方则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和援助英国,认为欧洲的战争与美国没有关系,德国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而援助英国和苏联会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引入战争。这些人自称是“不干涉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但被对手称为“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 9月23日,国会开始就修改《中立法》问题进行辩论,拉开了外交大辩论的序幕。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E. Borah)、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和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众议员亚历山大·菲什(Hamilton Fish)坚决反对修改《中立法》。洛奇声称,“英国和法国被击败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要么德国战败,要么出现僵持的局面”,“即使德国获胜并企图征服美国,它也永远做不到”。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修改《中立法》是不必要的。④罗斯福政府则动员美国政界的元老如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等出山,组织由威廉·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担任主席的“通过修改《中立法》争取和平跨党派委员会”(Non-Partisan Committee for Peace through the Revision of the Neutrality Act),宣传修改《中立法》的必要性。在国际主义看来,对交战双方平等地实行禁运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而只有实行有区别的禁运,美国才能避免战争。参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W. Norris)指出,如果取消武器禁运,就会帮助英、法;如果不取消则有利于德国,“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⑤。 辩论的结果是,1939年11月4日国会通过1939年《中立法》,把“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用物资,并禁止美国公民和船只进入总统划定的交战区。1939年《中立法》的通过是孤立主义者在罗斯福任内首次重大的立法失败。 1940年6月22日,法国战败。随后,德国开始攻击英国。法国战败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使美国民众产生强烈不安全感。为了确保英国能够顶住德国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拨款向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主要是英国)提供军用物资。1月10日,国会开始就《租借法案》进行辩论。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反干涉团体“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宣布反对《租借法案》,并发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有关《租借法案》的争论在全国展开。 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援助欧洲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这是欧洲的战争,是欧洲旧的帝国争夺的继续,并不涉及道德与国际正义问题,因此与美国没有关系。早在二战爆发前夕,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就称欧洲出现纷争的原因是“旧的权力政治”,“与民主事业无关”,而且欧洲一向如此,美国没有必要插手。⑥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也称“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这是欧洲的冲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我们的国家远离这些冲突”⑦。第二,德国无法战胜英国,更不能威胁美国,因此援助英国是不必要的。众议员克努特·希尔(Knute Hill)问道:“希特勒倾其全部力量都不能跨越20英里的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他的军队如何可能跨越大西洋登陆西半球?”⑧第三,欧洲经常陷入相互争斗之中,美国无力解决欧洲的问题,援助欧洲是得不偿失的。《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兼编辑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指出,“由于欧洲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在欧洲组织起像美国那样的联盟“超出人类的能力”。如果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20年前的那种成果——美国青年遭受屠杀——加强争端一方的力量——随后是忘恩负义和辱骂伤害”⑨。第四,《租借法》将把美国带入战争。众议员詹姆斯·欧康纳(James F.O’Conner)警告说,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将是美国干涉欧洲战争的第一步,最终会导致美国“一头扎进战争中去”⑩。 而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从1939年9月开始的战争不是一场欧洲国家争权夺利的战争,而是涉及民主存亡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希特勒“追求用剑对世界进行永久征服和主宰”,德国实际上是“所有法律、自由、道德和宗教的敌人”(11)。德国和意大利获胜“将威胁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12)。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也指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相互敌视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它是一场将使自由和民主遭到毁灭的战争。”(13) 国际主义者还批评孤立可以保障美国安全的说法。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飞剪船的时代,大西洋的宽度已经没有意义,那种“以为我们可以退居自己大陆的边界之内而维护自己安全”的想法是“枉费心机”和“毫不现实”的“幻想”(14)。 针对援助英国会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说法,《租借法案》的支持者指出,援助欧洲恰恰是避免美国直接参战的最佳途径。《纽约时报》社评认为,“如果英国牵制轴心国的时间能长一点,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享受和平的能力也会提高。”(15)罗斯福也提出,通过援助英国等民主国家,“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16)。 国会于3月8日通过《租借法》,3月11日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但是,辩论并没有结束。“美国第一委员会”内口才最好、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到全国各地演讲,反对罗斯福援助英国的政策。在1941年4月23日纽约的演讲中,林白还号召“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阻止美国“极少数权势人物”把美国拖入战争。(17)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罗斯福总统提出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9月末,美、英、苏签订《援助苏联议定书》。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国家。这引发了更激烈的辩论,因为苏联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是与纳粹德国一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孤立主义者似乎找到了反对干涉的更强有力的理由: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罗伯特·塔夫脱在6月25日的广播演说中声称:苏德战争爆发更加证明了“欧洲的战争并非民主与专制之战”,因为俄国实际上应为目前的战争和德国的侵略负责,如果没有苏联与德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就不会有德国侵略波兰。“苏联是与德国一样的侵略者”,而且苏联不可能因为遭受德国的入侵就一夜之间从“侵略者”变成了“民主国家”。因此,罗斯福以传播“四大自由”的名义向苏联运送飞机、大炮和坦克是极其“荒谬可笑的”。(18) 1941年8月初,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战争目标问题在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会晤,并于8月12日发表了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9月,由于美国军舰在冰岛海面遭到德国潜艇袭击,罗斯福明确要求美国军舰可以对德国潜艇开火。国会于11月13日再次修改《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允许美国船只开往交战区与交战国进行贸易。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随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增加,孤立主义者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语言和行动阻止美国卷入战争。林白1941年9月11日在衣阿华州的得梅因发表演讲,公开提出:美国之所以从最初的中立走到现在的战争边缘,是“外国利益集团”和一小撮美国人鼓动和强迫的结果。这些人是“战争煽动者”,包括三个最重要的集团: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林白声称,这些“战争煽动者”人数虽少,但是却有极大的能量,掌握着宣传、金钱和公职任免的权力,图谋一步步把美国拖入战争。他声称,犹太人和英国人煽动美国参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号召美国人给国会议员写信,组织集会,以阻止美国干涉欧洲的战争,保卫美国自身的独立和自由。(19)这一演讲遭到广泛而尖锐的批评,也极大地损害了林白个人的声誉,“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声誉也受到影响。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孤立主义者虽然对美日关系的紧张也表示关注,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日本胆敢袭击美国。日本偷袭珍珠港无疑对孤立主义者造成沉重打击,但对日宣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是否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美日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急需人力和资源投入太平洋战场的情况下,罗斯福恐怕更难以在德国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加入欧洲的战争。但是,此时希特勒却帮了罗斯福一个大忙,德国居然于11日对美宣战。在美国已经被迫卷入战争的形势下,继续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干涉欧洲的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同时,美国领土遭受袭击本身也证明了孤立主义者以孤立求安全的虚妄。12月11日,美国第一委员会全国委员会通过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关于参战问题的民主辩论时期已经结束了,军事行动的时期开始了”,决定“停止所有的活动并解散”;同时,该委员会“敦请所有曾追随本组织领导的人士全力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直到和平得以实现”(20)。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外交大辩论终于结束了。 二、关于国家目的与国际角色的不同思考 从表面上看,这场外交大辩论主要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欧洲和干涉欧洲的战争展开的;但在实际上,辩论双方的言论已经触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国内福祉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怎样?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美国究竟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大辩论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形势下,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与意义、国际角色与身份等对外关系基本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一)美国与国际体系:脱离还是改造 从建国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认为外部世界是危险的,特别是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遵循的是君主国的逻辑,充满欺诈、阴谋、强权政治和战争,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并不适合在这一体系里生存。美国要么脱离这一体系,要么按照美国的原则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造,使其适应共和国的需要。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无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唯一的选择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卷入欧洲的纷争,也就是与这一体系相脱离。 在这场外交大辩论中,孤立主义者坚持美国继续保持19世纪的那种孤立,利用西半球有利的位置继续保持在欧洲国际体系之外。《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社论中强调:二三十年代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欧洲争斗的间歇期,旧大陆的人民有一种疯狂的倾向,不断地“从事杀戮和消灭,并践踏基督教的每一项原则”。“这种疯狂会传染”,美国的先辈就是为了逃离欧洲的疯狂,包括战争和暴政,才来到美洲。美国应该远离欧洲的争斗,“为世界的未来保留一个最光明希望”(21)。众议员乔治·本德(George H. Bender)也认为,“我国政治的历史代表了拒绝卷入欧洲事务的决心,代表了对欧洲统治方式和欧洲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的彻底否定。”(22)林白则直言:“美国的命运与欧洲是分离的”,美国不应该把自己与欧洲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而应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以一种比欧洲交战各国更富有建设性和更英明的方式来促进人类的进步”(23)。 而《租借法》,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其后果就在于让美国错误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拴在一起。范登堡在《租借法》通过当天,也就是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抨击《租借法》使美国“投入到欧洲的权力政治和欧亚非的战争中去”,“有意选择‘参加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冒险中去”(24)。 孤立主义者还主张,美国要尽可能地缩小美国的利益范围,从而使美国与外国争吵的机会也就会少些。大多数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者,即关注国内市场,主张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孤立主义者甚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和平,而自由贸易导致经济冲突,会引发战争。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之一、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讲话中称,近些年来,美国的外贸出口额每年30亿美元,大约占其总收入的5%;而对南美洲的出口约3亿美元,约占总出口的1/10,占美国总收入的0.5%。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对西半球的出口还是整个美国对外出口在美国经济总量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从贸易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几乎可以自给自足”(25)。 总之,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离开欧洲照样繁荣,大洋仍然可以成为美国与欧洲相隔离的屏障,美国没有必要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美国要做的就是要待在西半球,做好自己的事情,欧洲不论发生什么都与美国无关。奉行孤立主义立场的诗人奥利弗·奥尔斯特洛姆(Oliver Allstrom)创作了一首长诗《战争——“在那边”》,被“美国第一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其中写道:“‘那边’,一个充满血污的地方,言语混乱而乖张,为什么向这帮异类(alien)施以援手,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梦想?……不,不,一个声音在美国的天空中飘荡,我们决不做同盟国的工具,再一次在外国人的队伍里接受检阅,就像一队傻瓜里的笨蛋一样。……欧洲可以踏着血迹炫耀杀戮趾高气昂,并筹划各种阴谋、圈套和罗网,但是我们将待在家里,在大洋的这一面,把我们自己的事照管得妥妥当当。”(26) 乔治·本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一直是坚决让欧洲远离美洲,让美洲远离欧洲”。“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相分离”是“我们对外关系的基石”(27)。 同孤立主义者一样,国际主义者也明白世界是充满冲突的,欧洲是动荡不安的,但是他们更相信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这个拥有20亿人口的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同一世界,即从根本上不可分割的世界”(28)。如果说孤立主义者从一战经历中体会到的是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弊害;国际主义者则看到的是参与海外事务的必要。在国际主义者看来,由于美国力量的崛起、军事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由于美国海外利益的扩大,美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掌控事态的进程和方向,对无政府的、充满冲突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从而塑造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环境。 1939年4月14日罗斯福泛美联盟的演说中说:“毫无疑问,用不了几年,机群越过大洋就像今天越过欧洲内海一样容易,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注定会成为一个整体,未来任何地方的经济遭到破坏都会对所有地方的经济造成破坏。”(29)他在4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的维护都对我国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消失都会削弱我们的安全与繁荣。”(30)史汀生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了,并且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美国的孤立是一个“陈旧过时的传统”(31)。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和德国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了国际主义者关于美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看法,认识到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著名媒体人士杰拉尔德·约翰逊(Gerald W. Johnson)在1941年6月评论说:在1919年,反对国联的人相信“欧洲总是需要美国的力量,而美国需要欧洲力量的时代永远也不会到来,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一信念坚信不疑”。但是到了1941年中期,他们发现,一批专制国家似乎正在把自由政府在欧洲的最后堡垒消灭掉,美国突然之间陷入一种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是“美国人从未想到和最不希望的”。这时,他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所有自由国家人民的安全密不可分,不保障其他人的安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32)。 在国际主义者心中,正因为相互依赖的潮流已经使美国无法与国际体系相脱离,美国只能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去,但他们对这一体系的规则并不满意。在罗斯福等国际主义者看来,在一个“被几个人手中武力所统治”的“卑鄙和危险的世界”上,美国的制度无法长存,(33)因此必须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建立一个由美国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秩序。亨利·卢斯提出:美国无法为其他国家的良好行为负责,但是“美国必须为她生存其中的世界环境负责”。如果美国所处的环境不利于美国制度的成长,那美国人就不要指责他人而只能怪自己,因为美国是影响这一环境的最大力量。卢斯称,美国必须运用自身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世界环境。“各种形式的孤立主义在道义和实践上的缺陷,就在于没能抓住美国和美国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34)。而罗斯福则明确地提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建立在“四大自由”的基础上,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由希特勒支配的世界”,也绝不会接受类似一战后20年代那种“使希特勒主义(Hitlerism)的种子再次种下并长大的世界”;美国将“只接受致力于言论和表达自由、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灵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35)。 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将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分为两类:一是占有性目标(possession goal),一是环境目标(milieu goal)。前者是指领土、资源、市场、成员国地位等排他性的、有形的目标,一国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通常会构成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而后者是指一国试图塑造国外的事态,建立有利于本国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包括友善、秩序、规则与和平,环境目标并不是排他的和竞争性的,一国在追求环境目标的时候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36)从这一分类来看,孤立主义者重视的是占有性目标,对环境目标不感兴趣;而国际主义者虽然也追求占有性目标,但是他们更重视环境目标,关注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关注外国国内政治的演进,认为一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影响其外部行为,重视国际事件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示范效应以及国际舆论和国际伦理的变化。罗斯福也从国际环境和秩序的角度看待欧洲战争对美国的威胁。在罗斯福眼中,轴心国的威胁主要不是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德军占领美国),而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对美国国家特性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罗斯福1940年12月29日炉边谈话中的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如果英国倒下,轴心国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我们就会走进一个新的可怕的时期,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将屈从于野蛮武力的威胁之下,要在这样的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永远转化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37) 总之,国际主义者不是消极地回避战争,而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行动来防患于未然,致力于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繁荣的环境,追求的是“积极和平”。孤立主义者关注的是让美国如何避免战争,追求的是一种“消极和平”。孤立主义者的大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脱离”战略,即通过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保持美国“高尚的孤立”(virtuous isolation),以维护美国的自由与安全;而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是“改造”战略,通过参与和改变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 (二)对外干预与国内自由:破坏还是保护 大辩论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卷入海外事务是否会损害美国民主和国内福祉。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卷入欧洲的战争,会使总统及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并制造出不受民众和国会监督的、热衷于秘密行动的情报机构,从而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战争会导致高税收、国债和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战争会制造一个庞大的军工企业集团,他们依赖政府订货,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敌人,渲染仇恨,从恐惧和战争中获利。战争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从而大大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战争期间,公民自由会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受到践踏。总之,对外干预和战争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按照军事化原则进行管理,崇尚军人价值观,对公民进行严密控制和高度整合的“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38)而这一切都会威胁和消灭美国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等。在孤立主义者的眼中,“兵营国家”的出现将是美国的梦魇,是美国理想的覆灭;一言以蔽之,对外干涉会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和民主,损害美国人民的福祉。 阿瑟·范登堡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关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的自杀”,《租借法》“意味着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我们民主制度的终结”。(39)罗伯特·塔夫脱称“战争不仅不能保卫民主,相反可能会摧毁我们美国这里的民主”,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很可能会摧毁美国自由赖以建立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40)林白则直接抨击罗斯福“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任总统任期”,利用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用战争为限制国会的权力、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实施独裁权力寻找依据”。(41)一言以蔽之,“紧急状态的保持”成了总统扩大权力的借口。 在孤立主义者心中,民主是极为脆弱的,威胁民主的力量有很多,包括金钱的腐蚀、财富的集中、民众的盲目、外敌的入侵和敌对势力的颠覆。而过多地卷入外国的事务也会对民主构成威胁:腐蚀民众的品德,卷入外国的阴谋,为外来势力收买美国的政治人物打开方便之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义者奉为金玉良言:(美国)一旦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42)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美国利益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已经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不闻不问,那么美国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来自两大事态:一是霍布斯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一是出现世界性的帝国。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领域盛行的是均势原则,而均势原则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和均势会引发战争,一战暴露了均势的脆弱。而美国的政治传统为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验,那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各国结成联盟、和平相处、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世界性帝国的出现虽然可以避免无政府状态,但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自由制度构成极大威胁。一战期间,威尔逊曾对德国可能成为这样的帝国深为忧虑,担心德国的胜利将“改变我们文明的走向,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事国家”(43)。这成为美国向德国宣战的动因之一。在国际主义者看来,1940—1941年与1917—1918年的形势非常相似,美国不能容忍希特勒德国征服欧洲,就像当年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迎接专制德国的挑战并在击败德国后以理性原则重建国际秩序一样。 因此,国际主义者声称:如果美国对欧洲事务不闻不问,那么极权主义就会获得胜利,欧洲就会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霸主或同盟。到那时,美国很可能会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家”(Fortress America):处在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一个充满敌意、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封闭自己,时刻担心敌对霸主的入侵和破坏;而为了安全,不得不减少对外交往,牺牲自由,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堡垒国家”无异于一个孤岛、一个监狱,自由和安全无从谈起,美国生活方式也无法维持。1940年6月10日,罗斯福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说:一些人实际上仍然抱有现在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幻想:我们美国可以安然地让美国成为武力哲学统治的世界的一个孤岛。这样的孤岛可以是那些仍然以孤立主义者身份说话和投票的人的梦想。但是对我和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孤岛代表着一种无助的噩梦;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无助的噩梦;一个被关在监狱里,带着手铐,忍饥挨饿,日复一日地依靠其他大陆倨傲冷酷的主人通过栏杆提供食物的民族的无助的梦魇。(44) 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希特勒残暴武力的威胁,为了生存,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长久地变成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militaristic power)”(45)。国务卿赫尔也警告说,到那时,美国将不得不把自己变成“隐士国家”(hermit nation),并“改组我们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重新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对生活的每一方面进行严格的管制”(46)。 国际主义者还指出,希特勒主宰欧洲对美国经济也将构成严峻挑战,从而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国内社会的福祉和生活方式。美国前驻柏林参赞道格拉斯·米勒(Douglas Miller)向美国民众描述了德国主宰世界可能带来的最可怕的前景:希特勒征服英国后将控制欧亚非三洲,柏林的中央机构将控制三大洲的贸易。美国的私人企业将无法与受到极权主义政权补贴的商品进行竞争,美国不仅无法获得国外的原料,其产品将大量过剩,贸易将大大缩减。美国要么按照希特勒的条件进行贸易,要么陷入经济萧条,而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将得势。简言之,“美国将从一个文明的时代跌入遭受围剿的漫漫长夜”(47)。 国际主义者辩称,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反抗纳粹主义的力量不会损害美国的自由,相反却是保卫美国民主的途径。罗斯福在1941年5月27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些懦弱之辈,他们说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维持和平,否则我们就将永远失去自由。对于这些人,我要说: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竟会由于成功地保卫民主而丧失其民主。我们决不能被我们准备抵抗的威胁所吓倒。我们的自由已经证明它能够在战争中保存,但是绝不可能在投降中保存。(48)同威尔逊一样,30年代国际主义者相信,只有通过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与英、法的合作,才能建立一个“让民主享有安全”的世界。因为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美国维护安全的代价会非常低,就用不着对社会进行控制或使其军事化。只有这样,在面对希特勒德国的威胁时,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才能真正得以保存。 (三)美国的国际角色:“自由灯塔”还是“世界领袖”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何种身份?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美国人。孤立主义者试图继续恪守建国之父们的告诫,让美国仅仅充当“共和典范”和“自由灯塔”。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面对希特勒德国对民主国家的进攻,美国必须挺身而出来捍卫自由和民主,仅仅“垂范”是不够的,美国还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抵御民主的敌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进攻,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领导的角色。 孤立主义者认为,通过树立民主的典范,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美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义的领导,为和平与进步作出贡献。比尔德在其1940年出版的书中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庞大常备军、巨额债务和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满足于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国结成联盟,干预或卷入外国事务”(49)。“美国第一委员会”在1940年的一份宣传广告中称:“充当游侠骑士无疑不是我们的使命”(50)。 孤立主义者认为,民主是无法用武力进行输出的,强制输出民主带来的将是专制和暴政。塔夫脱在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中说: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可以支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征服改变其他民族的哲学,没有人能够长期把一种其他民族不希望或不适合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民族。我们不时地会听到有人鼓吹美国要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我们在1917年曾尝试这样做;但是从那场战争中生长出来的,是比我们一百年间看到的更多的“主义”、专制统治和残暴的独裁者。(51) 塔夫脱声称,以捍卫正义和民主的名义卷入欧洲的战争“恰恰会摧毁我们要捍卫的那种道德”,“通过残忍的战争武力的方式把任何特殊牌号的自由和民主强加给其他民族,而不管他们想不想要,都是对我们努力促进的那些民主原则的否定”。他批评罗斯福的主张“非常类似曾激发中世纪圣地十字军运动的那种宗教狂热”,是错误地相信“我们有改革世界的神授使命”,这是极端危险的。(52)在塔夫脱看来,“在世界上促进民主事业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证明民主政府是能够给采用它的人民带来最大的和平、安全和幸福的政府,证明即使在战争、危机和紧急状态下,民主过程也能够得到保持。”(53)范登堡也提出,“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国和本国暴行的受害者充满同情,并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54) 孤立主义者并不渴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领袖,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美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建立和维护全球体系。这会让美国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从而会损害美国国内的繁荣。不仅如此,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the Augean stables)(55);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简言之,美国的民主将遭到严重腐蚀。 而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在民主制度遭受法西斯主义威胁,人类遭受贫穷、饥饿、战争和暴政蹂躏的时候,仅仅率先垂范和进行道义领导是不够的,美国还需要通过承担国际义务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导世界抵御专制主义的进攻,保卫民主和实现和平。 卢斯在1941年2月发表的《美国世纪》一文集中,阐释了当时国际主义者对美国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思考,那就是充当世界的领袖。卢斯在文章开头即提出,美国面临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问题,这是“20世纪的美国所独有的问题”,“这一问题远比眼前的战争问题更深刻”。这一问题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称: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卢斯号召共和党放弃孤立主义而拥抱国际主义,支持罗斯福承担对世界的领导,“使孤立主义成为像奴隶制那样的已经死亡的问题,让美国真正的国际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像飞机或收音机那样自然的东西”。卢斯说: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20年代我们把它搞砸了。在30年代的混乱中,我们把它葬送了。领导世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下,罗斯福一定能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成功。(56) 亨利·华莱士1941年4月21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在一战后拒绝世界交给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迟早有一天,美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世界地位将迫使美国接受与这一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责任。美国已有《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现在应该制定一部《责任法案》(Bill of Duties)。《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葛底斯堡演说》是美国的“旧约”(Old Testament),《责任法案》则可作为美国的“新约”(New Testament)。美国“既要有独立的意识,也要有相互依赖的意识;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责任意识——一种与我们的实力相一致的责任感”。他说:我们美国不能再一次拒绝承担我们的责任,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不能靠穿短裤而避免成为一个成年人一样。对于已经长大的美国来说,“孤立”一词意味着短裤。美国现在又一次拥有了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的机会。(57) 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到卢斯的“美国世纪”,再到华莱士的“美国责任”,国际主义者实际上是在阐释美国新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身份,这就是充当“世界领袖”。而在《纽约时报》看来,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领导人签署大西洋宪章标志着美国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开端。该报社论称:“这是孤立主义的终结,是美国承担天然地落在世界大国肩上的责任的新时代的开始”(58)。 三、大辩论的结局与意义 国际主义者无疑是这场大辩论的胜者。孤立主义者则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阻止美国卷入欧亚的战争,甚至未能挫败1940—1941年行政当局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虽然后来有人继续指责正是罗斯福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和对英、苏的租借援助招来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德国对美宣战证明孤立主义者的两大主张是错误的:一是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二是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正如罗斯福在1941年12月9日的炉边谈话所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极端的过去的几天中,我们学到了一个可怕的教训:……在一个由强盗原则(gangsterism)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会获得安全,面对在暗中鬼鬼祟祟和实施偷袭的强大侵略者,没有任何防御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这个由大洋环绕的半球并不能免遭剧烈的进攻,我们不能根据地图上的英里数来测量我们安全的程度。(59) 而主张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和领导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国会内最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资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转变成为国际主义者赢得胜利的标志。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就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当天的下午,通过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实现和平的信念在我心中牢牢地形成了。对任何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来说,那一天都标志着孤立主义的终结。”(60)罗斯福在1942年1月1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一段话,不再是国际主义者的宣言而是两党的共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是绝不罢休的。我们也不会满足于争取到这些目标后就收工不干。……这一回,我们下定决心,不仅要打赢这场战争,还要维持战后的和平和安全。(61) 正是这一共识使美国没有重蹈1917—1920年卷入——退出的覆辙。赫尔在1944年4月的演讲中宣称,美国人民已经决定不仅要同盟国一道打败纳粹和法西斯制度,而且“还要同我们的盟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道,全力以赴地去建立和维护使自由与和平成为持久现实的制度”。美国做出的“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决定”。美国不会像一战后那样,“在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责任时出尔反尔”(62)。 从威尔逊在1917年首倡算起,自由国际主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孤立主义和保守的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它不仅主导了美国参战后的外交政策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实际上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角色也得以重塑:美国的安全不能依赖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和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来获得,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来实现。美国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自由灯塔”,还应该对世界进行领导,运用美国的力量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的国际环境。美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转向以多边主义形式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这无疑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用阿瑟·范登堡的话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美国“丢弃了实行150年的传统外交政策”,走上一条“永远无法回头的路线”。(6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加入二战前的几年是美国外交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时刻;美国外交的转折点不是1945年,而是1941年。 自由、公开的辩论是美国社会得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稳定、长远的国家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正是1939—1941年的外交大辩论与当时的国际事态一起促成了国际主义共识的形成,并导致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和德、意对美宣战,这场大辩论极有可能还会继续。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民调表明,孤立主义者在辩论中已处于下风,舆论已经转向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尽一切可能援助英国,即使因此卷入战争也在所不惜。(64)从这个意义上说,珍珠港事件前的外交大辩论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交大辩论。 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大辩论的失败者——孤立主义者视为目光短浅、幼稚愚蠢、不负责任的可笑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美国的精英人士,在美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声望。(65)他们反对战争,揭露军火商与政客相互勾结的事实,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其勇气和品德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其言论代表着对美国国家身份和国家目标的另一种思考。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安全形势的过分乐观、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美国干预必要性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担心也是颇有预见性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是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联邦政府集权化的趋势,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把孤立主义者的警告抛于脑后,滥用美国的力量,走上全球干涉的道路,“帝国过度扩张”的恶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证明了孤立主义者警告的正确性: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代价就是陷入各种阴谋之中,就是“帝王般总统权力”的出现,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以及“军工复合体”的崛起。 孤立主义者主张严格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克制;反对美国滥用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反对威尔逊式的传教热情和输出民主,尊重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呼吁美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改革和人民福祉,减少对海外事务的参与以免浪费美国的资源。这些主张无疑是极有见地的。用外交政策评论家沃尔特·米德的话说,它可以使美国人“重新发现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放弃权力的傲慢,回到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处理对外政策的道路,削减帝王般的总统权力”(66)。美国参战后,孤立主义虽然已经无法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对美国过多卷入海外事务必要性的怀疑,对美国滥用权力的批判,对霸权代价的警告成为一种抗衡力量,对二战后的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制宪时期的反联邦主义者参与了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一样,孤立主义者同这场大辩论的胜利者——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注释: ①著名政论家、2000年总统大选改革党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语。帕特里克·布坎:《共和国,而不是帝国》(Patrick J. Buchanan,A Republic,Not a Empire: 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华盛顿2002年版,第249页。 ②本文中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的名词,与中国语境中的“国际主义”的含义并不相同。本文的“国际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兴起的关于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美国在自身国力增强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新形势下,应放弃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信奉和鼓吹这一思想的人被称为“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内部又因观点的差异分为“保守的国际主义者(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和“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两翼。保守国际主义者反对对国际秩序进行根本的变革,主张通过完善国际法、实施国际仲裁和建立国际法院来维护和平,他们不赞同集体安全原则,不支持甚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务卿、知名法学家伊莱林·鲁特、总统威廉·塔夫脱以及后来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和总统赫伯特·胡佛。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则试图用自由主义原则对19世纪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他们主张建立集体安全组织以维护和平,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繁荣,并支持在海外促进民主。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后来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媒体大亨亨利·卢斯等人都是著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 ③研究大辩论的著作有:韦恩·科尔:《查尔斯·林白与反对美国干涉二战的斗争》(Wayne S. Cole,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Ⅱ),纽约1974年版;韦恩·科尔:《罗斯福和孤立主义者》(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1932-1945),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反对干涉的斗争》(Justus D. Doenecke,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39-1941),佛罗里达州马拉巴1997年版;贾斯特斯·多奈克:《风暴将至:对美国干涉政策的挑战》(Justus D. Doenecke,Storm on the Horizon: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Intervention,1939-1941),明尼苏达州拉纳姆2000年版;戴维·亨德里克森:《联盟、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美国围绕国际关系的辩论》(David C. Hendrickson, Union, Nation,or Empir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789-1941),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著作或以大辩论中的活跃人物如查尔斯·林白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中心,或集中描述大辩论的过程和考察双方主张,而缺乏对大辩论的影响和意义的深入剖析。亨德里克森的著作虽然指出美国外交史上的历次大辩论实际上都是对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辩论,并给笔者以启发,但他把关于国家身份的辩论归结为美国究竟是联盟(union)、民族国家(nation)还是帝国(empire)的争论,与笔者的思路有很大不同。 ④美国国会编:《国会记录》(U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第76届国会第2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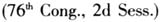 ,1939年10月10日,第85卷,第1部分,第250页。 ,1939年10月10日,第85卷,第1部分,第250页。⑤约瑟夫·海门:《人物百态:美国参议院中的傲慢自大与英雄主义》(Joseph M. Hernon,Profiles in Character: Hubris and Heroism in the U.S Senate),纽约州阿蒙克1997年版,第158页。 ⑥杰拉尔德·奈:《挽救美国的中立》(Senator Gerald Nye, “Save American Neutrality”),《当代重要演讲》(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第5卷,第23期,1939年9月15日,第725页。 ⑦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讲话(Robert Taft’s Radio Address),小克拉伦斯·旺德林编:《罗们特·塔夫脱文件集》(Clarence E. Wunderlin,Jr,ed.,Papers of Robert A. Taft)第2卷,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6页。 ⑧美国国会编:《国会记录》(US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cord),第77届国会第1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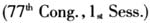 ,1941年2月5日,第87卷,第1部分,第590页。 ,1941年2月5日,第87卷,第1部分,第590页。⑨《专栏作家麦考密克追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屠杀和阴谋》(“Col. McCormick Traces Europe’s Centuries of carnage and Intrigue”),《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1939年9月4日,第1、5页。 ⑩詹姆斯·欧康纳:《美国不应该向英国提供租借援助》(James F.O’Conner,“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Extend Lend-lease Aid to Great Britain”),约翰·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John C. Chalberg,ed., Isolationism: 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1994年版,第181页。 (11)1941年9月11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 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012#axzzl rjhW2SA1(2012年4月11日获取)。 (12)罗斯福1940年6月10日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Roosevelt’s Address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赛缪尔·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Samuel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1940年卷,纽约1941年版,第261页。 (13)亨利·华莱士:《重生的民主》(Henry Wallace,Democracy Reborn),拉塞尔·洛德(Russell Lord)编,纽约1944年版,第173页。 (14)1940年5月26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59#axzzla TyRc14J(2011年10月11日获取)。 (15)《加快我们的援助》(“To Speed up Our Aid”),《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41年1月6日,第14页。 (16)《民主国家的兵工厂》(“The Arsenal of Democracy”),刘易斯·科普兰等编:《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讲》(Lewis Copeland,et al., eds.,The World's Greatest Speeches),纽约州米尼奥拉市1999年版,第521—522页。 (17)查尔斯·林白:《美国无法阻止德国获胜》(Charles A. Lindberg,“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Prevent a German Victory”),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93—195页。 (18)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讲话(Robert Taft’s Radio Address),小克拉伦斯·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5页。 (19)《林白发现了战争“阴谋”》(“Lindbergh sees a‘Plot’for War”),《纽约时报》1941年9月12日,第2页。 (20)韦恩.科尔:《美国第一:反对干涉的斗争》(Wayne S. Cole, America First: The Battle against Intervention,1940-1941),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95页。 (21)《休战期的结束》(“The End of a Truce”),《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39年9月4日,第18页。 (22)乔治·本德:《1940年的挑战》(George H. Bender, The Challenge of 1940),纽约1940年版,第100页。 (23)查尔斯·林白:《美国无法阻止德国获胜》,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93、195页。 (24)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Arthur H. Vandenberg, Jr.,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伦敦1953年版,第10、11页。 (25)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8页。 (26)曼弗雷德·乔纳斯:《孤立主义在美国》(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1935-1941),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7页。 (27)乔治·本德:《1940年的挑战》,第93页。 (28)亨利·卢斯:《美国世纪》(Henry R. Luce,“The American Century”),《生活》(Life)1941年2月17日,第64页。 (29)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1939年卷,纽约1941年版,第198页。 (30)乔治亚州温泉镇记者招待会摘录(Excerpts from the Press Conference in Warm Springs,Georgia)http:// 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735#axzzlaTyRc14J(2011年10月11日获取)。 (31)亨利·史汀生:《美国必需抛弃其孤立主义的过去》(Henry Stimson,“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ject Its Isolationist Past”),查尔伯格编:《孤立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第141页。 (32)杰拉尔德·约翰逊:《伍德罗·威尔逊的幽灵》(Gerald W. Johnson,“The Ghost of Woodrow Wilson”),《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第183卷,1941年6月,第7、9页。 (33)罗斯福致国会的年度咨文(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Jan.3,1940),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856(2011年10月12日获取)。 (34)卢斯:《美国世纪》,《生活》1941年2月17日,第63页。 (35)《宣布全国处于无限紧急状态的广播讲话,1941年5月27日》(Radio Address Announcing an Unlimited National Emergency), 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120&st=&st1=#axzzlaTyRc14J(2011年10月12日获取)。 (36)阿诺德·沃尔弗斯:《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3—74页。 (37)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17#axzzlaTyRc14J(2011年9月11日获取)。 (38)“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37年提出的概念。他预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外部威胁的增加,国家形态将从过去的“市民国家”(civilian state)演变为“兵营国家”,即“专制的、支配的(governmentalizd)、集权的和高度整合的(integrated)”的国家形态,政府大权不是掌握在谈判专家,即商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暴力专家(specialists on violence),即军人的手中。在美国人观念中,“兵营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是截然对立的,“兵营国家”的出现意味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毁灭。而市民国家之所以变成“兵营国家”,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因为在遭受巨大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会把安全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不得不改变经济和政治生活,牺牲美国的自由和生活方式,其结果就是把公民社会转化成了军事化(militarized)社会。哈罗德·拉斯韦尔:《中日危机:兵营国家vs.市民国家》(Harold D. Lasswell,“Sino-Japanese Crisis: The Garrison State versus the Civilian Stat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37年第11期,第643—649页;哈罗德·拉斯韦尔:《兵营国家》(Harold D. Lasswell,“The Garrison State”),《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46卷,1941年第4期,第455—468页。 (39)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0、11页。 (40)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6页。 (41)《林白发现了战争“阴谋”》,《纽约时报》,1941年9月12日,第2页。 (42)瓦尔特·拉菲伯编:《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国的大陆帝国:书信、文件和演讲汇编》(Walter LaFeber, ed.,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芝加哥1965年版,第45页。 (43)阿瑟·林克编:《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Arthur Link,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第30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44)罗森曼编:《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讲集》1940年卷,第261页。 (45)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5917#axzzlrjhW2SAl(2012年4月11日获取)。 (46)国务卿赫尔1938年3月17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s Addres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D.C.),http://teachingamericanhistory. org/library/index. asp? documentprint=655(2011年2月14日获取)。 (47)道格拉斯.米勒:《你无法与希特勒做生意》(Douglas Miller, You can’t Do Business with Hitler),波士顿1941年版,第167页。 (48)《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的广播讲话,1941年5月27日》 (49)查尔斯·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Charles Beard,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纽约1940年版,第12、31页。 (50)韦恩·科尔:《美国第一:反对干涉的斗争》,第190页。 (51)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46页。 (52)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6月25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4页。 (53)罗伯特·塔夫脱1941年5月17日的广播演讲,旺德林编:《罗伯特·塔夫脱文件集》第2卷,第250页。 (54)范登堡1939年2月27日在参议员的演讲(Vandenberg’s Speech in the Senate),《当代重要演讲》第5卷,1939年第12期,第357页。 (55)沃尔特·米德:《上帝特别的佑护: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Walter 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纽约2001年版,第205页。 (56)卢斯:《美国世纪》,《生活》1941年2月17日,第61、63、64页。 (57)华莱士:《重生的民主》,第176、179页。 (58)《与命运相约》(“The Rendezvous with Destiny”),《纽约时报》1941年8月15日,第16页。 (59)科普兰等编:《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讲》,第535页。 (60)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页。 (61)富兰克林·罗斯福国情咨文(Franklin Roosevel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1942),http://www. presidency. ucsb. edu/ws/index. php? pid=16253#axzzlaTyRe14J(2010年10月11日获取)。 (62)国务卿赫尔1944年4月9日在哥伦比亚广播网的演讲(Cordell Hull’s Radio Address Delivered over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当代重要演讲》第10卷,第13期,1944年4月15日,第388页。 (63)阿瑟·范登堡编:《参议员范登堡私人文件集》,第10、11页。 (64)1939年11月,只有2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援助英法;1940年5月,33%的美国人开始认为支持英国战胜德国比置身于战争之外更重要,即使冒卷入战争的风险;到1941年10月,这一数字是70%;到11月,则高达近80%。1941年秋,6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海军为向英国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护航,而海军护航实际上意味着与德国的准战争。因此,实际上,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多数民众已经不再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珍珠港事件在改变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上并没有过去认为的那样大。史蒂文·凯西:《小心翼翼的讨伐运动: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舆论与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Steve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American Public Opinion,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0页;亚当·贝林斯基:《发生战争时:理解从二战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舆论》(Adam J. Berinsky,In Time of Wa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from World War Ⅱ Iraq),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0页。 (65)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当时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杰出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是孤立主义者。 (66)沃尔特·米德:《上帝特别的佑护: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第217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