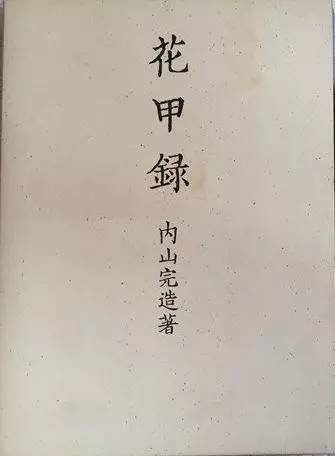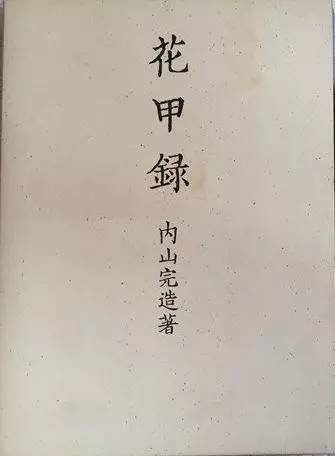|
“也许内山书店在中国比在日本更有名气。”日本的报纸这样写道,这家书店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而闻名于世。甚至不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夏丏尊、欧阳予倩等人也是该书店的常客。
但是,也有人质疑内山书店在战时出售鼓吹侵华的书籍,而另一方面,战时上海日本人中一直有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说法,这间历经百年风雨的书店,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年是日本的内山书店创立一百周年。日本一家大报在相关报道中写道:“也许内山书店在中国比在日本更有名气。”(《东京新闻》2017年7月10日)。
1917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创立内山书店。1935年10月,完造弟弟嘉吉先生(1900~1984)在东京开办了一家同名的书店。二战之后,上海内山书店不复存在;而东京内山书店至今仍在神保町营业。今年5月,店长内山深先生(嘉吉先生之孙,完造先生侄孙)来沪参加内山书店100周年的有关活动,他带上了全体职员,为此书店停业四天。
内山书店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而闻名于世。不过,几年前,笔者读到一本国内刊行的文集,其中一篇文章“献疑”道:为何内山书店在战时出售鼓吹侵华的书籍?  内山书店旧影
历史的复杂,恐怕超出献疑者的想象。笔者手头有一本《传说中的日中文化沙龙——上海内山书店》(太田尚树著,平凡社2008年初版),书中指出,内山书店的常客除了鲁迅和左翼文人,还有藏书家兼后来的汉奸、汪伪政权内政部长陈群。陈与内山还是美食同道,从名店吃到街头小摊(见小泉让《鲁迅与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6月初版,图书出版1989年9月再版)。小泉让是内山友人,他的书中还提供了一则史料:内山书店的主要客源是在沪日本人,售书金额中日本客户占四分之三。  鲁迅与内山完造
笔者对献疑者的叩问抱有敬意,惭愧自己少有简单和纯真了。只是想赘言一句,这种可以“正己”的思路,较难说明历史,尤其是风霜严寒的年代。
内山完造(1885~1959)十二岁从老家到大阪布店当学徒,1913年,他经熟悉的牧师介绍,作为一家药厂的推销员只身来到上海,时年二十八岁。当时,闯荡十里洋场是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选择之一(参见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初版)。1945年初,妻子亡故后,内山在上海购入墓地,墓碑铭文由其友人、开明书店掌门人夏丏尊撰写。1947年,内山突遭遣返回国,才给他终老上海的安排画上休止符。  内山完造
那是列强鲸吞中华的年代,后起列强日本的存在,给内山带来不便也带来便利。一方面,上海日本人中一直有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说法,1932年“一·二八”战事前后,就不时有日本浪人在他书店前晃来晃去(参见内山完造回忆录《花甲录》,岩波书店1960年初版)。另一方面,内山帮助中国友人做事时,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乃至军警难以对公共租界下手。这些都是今天不再、而回望当年时不可忽视的背景。
我们不妨从内山“不属于”哪类人群说起——他不是鹿地亘与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决然立于重庆或延安从事反战活动;他不是中西功或西里龙夫,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在地下系统出生入死;他也不是日方出没在前线的“笔部队”或摄影人,必须奉命书写或摄写“皇军”的战功。
内山完造是书商,是日本国民,他身属营利一族,虽然出售的是比较特殊的商品。来的都是客。在写于战后的《花甲录》中,他并不回避往日的营销手法,比如对中国顾客同样给予赊账的优惠,内山坦言这是围棋中的弃子之法(日语称“舍石”),目的是长期拴住客人。作为日本国民,他不能不听从日本官方的指令。他参与接管了英美租界的文化机构,将中美图书公司改名为内山书店南京路分店。但是,内山比别人、比众多的“别人”多走了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日本人中,也有不出卖自己朋友的人。”(参见《上海内山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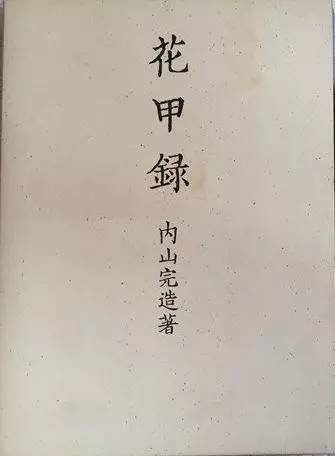 《花甲录》
以《花甲录》中出现的人物看,进出书店的中国文人可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从1949年后活跃在大陆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欧阳予倩、李初梨、阳翰笙、彭康、冯乃超等左翼人士,到郁达夫、夏丏尊、陈群、张资平、王独清、曹聚仁等各色人物,再到李大钊、李汉俊、朱镜我等革命先贤,多姿多彩。他们都是书店的客人,共同特点是留日经历。郭沫若1927年先避居内山书店,然后东渡日本,内山独自到码头送行(参见内山书店刊物《邬其山》1985年刊)。也许正如同时代人中西功描述的那样,内山“融入了中国社会,就是非常喜欢中国(见中西功《发自死牢——给妻子的信》,岩波书店1971年初版)。
小泉让在《鲁迅与内山完造》中称,内山的存在,给那个肃杀的年代留下了一丝光亮。他大概是把内山看成在沪日本人中的一个例外——例外自有其意义。内山书店出售各类日本读物,包括有侵华内容的书籍,是上海日文书商之日常。内山书店同时还是中文书籍的代理,发售之书包括《北平笺谱》等等,亦有鲁迅编辑的瞿秋白烈士遗著《海上述林》。有张内山书店的老照片,《海上述林》与日文书籍的广告同时出现在墙上。在那样的时代,没有日本出版物的经营,能有中文书籍的代理吗?推究内山没有做到什么,不如推究与其他在沪日本人相比,内山做到了什么?有意或无意地期望日本民众振臂而起,大概和期望本国民众都能慷慨赴难一样,美好,然而不易,甚至有点残酷。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能够有所为甚或有所不为,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不容易。在和平的今天,我们这样想,是否更好一些?  1934年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
战后,两手空空回到日本的内山,
投身于民间层面的日中友好活动。北至北海道,南抵鹿儿岛,他三次自费走遍全国,从事日中友好讲演活动,累计三千多场,听讲人数超过三十万(参见《花甲录》)。1949年筹建日中友协时,酝酿中的会长与理事长在战时曾任高官,方案被否,最后出任第一任理事长的是内山完造(参见《六十年——我们生涯中的中国》,伊藤武雄等著,1984年日本美篶书房初版)。
不妨提一下在今日日本也几被遗忘的“鹿地亘事件”。1951年,正在养病的鹿地突然被驻日美军绑架。“失踪”一年后,日本看管出于同情,私下告知了内山完造。内山立即行动,求助于社会党国会议员并告知媒体,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美军在某晚开车把鹿地拉到临近东京闹市的一条小街,让他自行回家。老友性命得以挽救,也让人看到了冷战岁月的冰山一角。与抗战时期内山营救许广平和夏丏尊的活动不无相似的是,鹿地亘事件中,内山仍然是几乎不见于大舞台的存在,又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1936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上海新月亭合影
内山著述的中译从1936年开明书店初版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算起,已经过去81年。近些年来又有多家出版社刊行了内山战前的中国观察散文集,不过其自传《花甲录》与小泉让、太田尚树撰写的两种传记尚未译出(这也是笔者引用的理由之一)。读其书,观其行,能更好地认知其人。年代久远,有些细节也许较难厘清,有些事情也许会有别解,但只要不是喜欢翻烧饼,就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