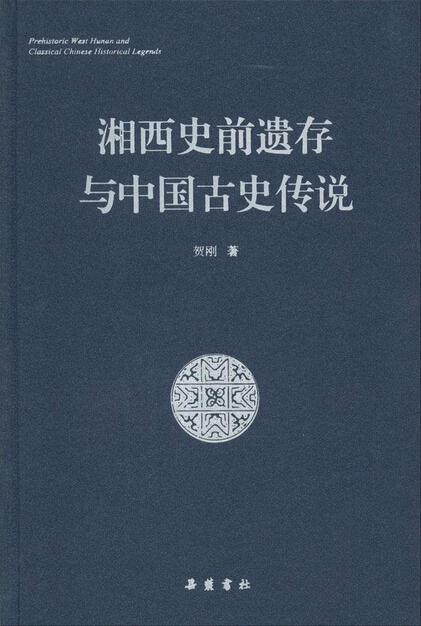 大凡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都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崭新的启迪和巨大的遐想空间。贺刚先生的新作——《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运用考古学资料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研究便拥有这些特征。该书资料详实、分析准确、考证严密,教科书般的叙述、激情洋溢的笔法、创新的思维,令人对湘西史前文化遗存底蕴的深厚和意义的重大印象深刻。 该书2013年10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据说现已售罄。全书分十个章节,洋洋洒洒50多万字,囊括了史前湘西现知的所有考古学资料。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是湘西的自然地貌与早期历史,以及湘西远古传说与田野考古探索;第三章至第九章都是考古学研究,分别是高庙遗址与高庙文化、高庙文化的区域类型、高庙文化的来源与演变、高庙文化若干遗存研究、高庙文化先民的初创与发明、高庙文化的对外传播、湘西史前文化的谱系与特征;第十章则是高庙、大溪文化与中国古史传说。该书致力于扎实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又以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为抓手、为重点、为突破口,对该地区以及相邻地区距今8000~4000年的考古学资料全面扫荡,不留死角地比对、甄别和研究。对遗存类型的确认、陶器组群的划分、年代的推定、它们的来龙去脉、对族属的认定等都巨眼卓识,都有创新与发展,都有实物与文献的相得益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全面提升了该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水准。该书使用的考古学研究手段是最近30年来为考古界普遍使用的基本方法,不外乎类型学、层位学、谱系学和年代学方法等。然而到今天能够如此运用自如、拿捏到位、游刃有余地研究,却仍不多见。犹如武术中的平凡招法,功力不同者其使用的效果便完全是天壤之别,真是令人感慨:高手就是任性!吹尽了狂沙,揉碎了资料,为后面的“重建”工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资料的详实和研究的深度显然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与过去相关的研究不同,《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特别注重深度发掘高庙文化的精神境界,坚持透过物质看族群、透过物质见精神、透过物质现制度的研究,为读者展示出高庙精神世界的博大与深奥,让人们领略湘西史前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与辉煌。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历史的伟大奇迹,远比现在的认识更加灿烂夺目,只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岁月的尘埃被淹没、被遗忘。正是这个原因,中国考古学才拥有了特殊的魅力。可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不是苍白地描述,就是简单地用来证明经典作家的正确,考古学从来就附属于历史学家的指挥与调遣,考古学写史的能力与渴望被传统研究压抑到丧失自我的境地。现在,《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的脱颖而出,再次证明中国考古学书写早期中国历史的特殊能力与优势。该书对高庙文化的研究是动态的系统分析,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考察,因之,高庙先民的初创与发明就被框定在一个特定的宏观体系之中。这个体系的完整与严密,为伏羲和炎帝的湘西说奠定了可信的基础。于是,太阳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白陶和祭器、梳理法则、艺术构图等发明创造就不是简单个别的、零散偶见的文化因素,而融入了伏羲炎帝族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贡献的体系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贡献具有鲜明的传承性,如果不是当时流行某种特殊的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力量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呢?深度发掘早期中国湘西地区精神生活与制度建设的特殊贡献,造就了该书层层深入和柔中有刚的第二个特点。作者高度与深刻的总结包含着对湘西土地深情的热爱,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国考古学自豪和奔放的情感,重建中国古史传说的责任溢于言表,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自从中国考古学登上历史舞台,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学者,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考古学资料的理解、认识和研究深度,其二是能否科学地驾驭文献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两重证据法进行到底。前者的粗疏容易流入对号入座的窠臼,后者的半途而废,则易于跌进文献的误区。所以,自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之后,真正能够一以贯之,并将其进行到底者实属凤毛麟角,寥寥无几。《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对伏羲与神农氏的考证和研究颇为精辟,就是因为真正将两重证据法的精神贯彻到底,完全是根据考古学资料摆事实讲道理,自觉地把考古学资料的研究提升到史学研究的层面。所以,文献的考证中体现着辩证的精神,创新的观点中闪烁着逻辑的力量,全书的体系追求的是超越梦想。写到伏羲和炎帝与湘西史前遗存的关系,作者几乎控制不住滚滚的思绪,他说“对始见于高庙文化而后才流传到长江下游流域和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八角星图像,无论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天文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已获得了基本共识:这类图像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位观,以及当时人们对日影的观测和历法的运用,同时也反映和揭示了远古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起源。且《周易》一书就是以这种图像和历法为基础的。由此可见,高庙文化始出的八角星图像及其内涵,不独是中国古代历法的源头,而且也是周易八卦的源头”。这个结论当然是完全建立在高庙文化先民的初创与发明基础上,与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更得两重证据法的精髓。这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在结语中他说,“传说时代的中国古史,自来史家众口一词,均说伏羲生于成起(纪),徙至陈仓,或都淮阳;炎、黄同出少典,发迹中原。今核诸载籍,勘验遗存,窃以为断非故实,务须重构。而由湘西波及洞庭,连横粤、桂,分布在此区域里的高庙文化与大溪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种种史实,均与古史传说中伏羲、炎帝的事迹相契合。遂可以认定伏羲和炎帝皆是生活在南方地区以远湘流域为中心的远古族团,前者是后者的直系祖先”。可见,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自信,无疑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对高庙文化的獠牙徽号、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徽号与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图像、制图原理和内涵等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则提出了早期中国古礼体系之间的影响与渗透,交流与融合的大课题。其研究视野之宽广远非湘西一个地区,而是投向了所有早期中国创造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探索拥有独到的建树。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和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实际上是古礼时代的传说和故事。早期中国在西周社会以前上推至万年以来,是中国的古礼时代。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脉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色。古礼是周礼的前身,是中国礼制体系的上游,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创造的集中体现。中国古礼有南北两大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多个特色类型,而湘西史前遗存正是江南地区古礼的主要代表,其时间发端最早,特征独特而鲜明,连绵不断,可以断言是良渚礼制的直接前身。目前已知,在早期中国的时候,黄河流域以北的古礼是龙凤为祭祀徽号,而长江流域之南是以夸张的虎头和凤鸟为特点,至迟约在距今6500年前两个系统的古礼就已经开始了交流与借鉴的历程。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时代的蚌塑龙、虎、鹿动物图像就是明证。高庙文化夸张的虎头经过良渚文化的改造与传承,最终成为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饰。由是观之,湘西史前遗存的特殊意义不言而喻,湘西史前的问题说不透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就讲不清楚。同样,湘西史前遗存若不能与中国古史联系,重构中国古史体系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此色彩斑斓,如此破天荒的贡献,如此意义重大的考古学遗存都不能参与“重构”的大业,那还能拿何种考古学文化参加讨论呢?尽管《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目前还将古礼系统概括为“神系”,并没有直呼高庙文化就是代表古礼的南方大系,但其笔锋所向,已经进入到问题的本质。所以,视野之开阔和志趣之高远是该书的第四个特点。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真是期盼《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一类的高质量学术著作能够更多一些。作者曾用刘禹锡“千淘万滤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诗句,形容他发现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心情。毫无疑问,但凡从事过田野考古的人都能体会到那份艰辛和喜悦。然而,该书的出版,又何尝不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更值得称道的“吹尽狂沙始到金”呢? (《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贺刚著,岳麓书社2013年10月出版,定价160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13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