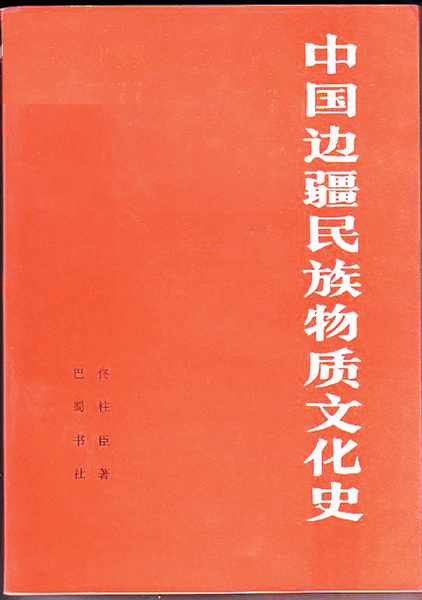 佟柱臣先生在花甲之年,写下60余万言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如今他去了,这是他留下的巨著中的一部,对我来说,也觉得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这是通过全景式视野研究边疆民族考古的著作,不仅是包括了全部边疆区域,而且包括了早晚不同的时代,一书在手,以往的边疆民族考古成果一览无余。 佟先生早年从事东北地区考古研究,著有《西团山考古报告集》,这可以看做是他关注边疆民族考古的一个开端。他虽然后来直接介入边疆民族考古实际田野工作并不多,却独具慧眼,写成《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将边疆地区考古全部已有的资料进行了爬梳整理,由考古资料出发对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探讨,从考古学上探索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过程。《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实际上是一部边疆民族地区考古发现史,是中国边疆民族考古的奠基之作。是佟先生的辛勤努力,才使得那些原本零散细琐的资料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中国边疆考古的轮廓也随之清晰起来。 《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以边疆民族地区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体例是以古代民族分布的地区为纲,以一地区先后不同时期活动的民族为目,巨细兼及,条分缕析。正如先生在提要中所说:本书就是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边疆民族的珍贵考古材料和准确的历史典籍,研究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特点,以探讨中华民族形成的规律。 本书按东北地区历史上的诸族、北方草原地区历史上的诸族、西北地区历史上的诸族、西藏的历史与文物、南方西南东南地区历史上的诸族、台湾和南海诸岛历史上的诸族分作六个大的地理单元,再分别叙述各地区不同时期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翻开这些构架有序的篇章,可以感受到佟先生书写文稿时饱含的民族感情,我们能觉出他心中奔涌的激情穿行在字里行间。以他为本书撰写的“提要”中的文字为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力,他这样深情地写道:“考古材料证实,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祖先,均以其优良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开发了边疆和捍卫了边疆,为中原的经济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中原地区在夏商周三代有许多的民族,这许多民族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华夏族。所以华夏族既包括多民族的血统,也包括多民族的文化,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战国时期和战国以前,她多半是一种自然状态,把中原的青铜器和丝织品等,传布到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边疆少数民族,也以一种自然状态,把她的文化教育传入到中原地区,这是边疆民族同华夏民族接触的开始,也是融合的开始。 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佟先生关注的重点。根据他的研究,战国时期华夏族形成后,边疆民族同华夏民族的接触与融合就开始了。秦统一六国,设立了郡县,为多民族的交往,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东北南部乌桓、鲜卑族居住的地方,才发现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陶量;在广东越人居住的地方,才发现始皇十四年铭文秦戈,这些证明秦代民族间接触和交往的地域,已经超出中原以外很远。汉承秦制,设都护置初郡,出现了中原汉族开始与边疆少数民族杂处的新景象,如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不仅有护乌桓校尉出行图,而且还表现有乌桓人的容貌和服饰。在匈奴人居住的北方草原包头附近,则发现了“单于天降”和“单于和亲”铭文的瓦当。而西域精绝国尼雅墓葬中,更发现了汉代织锦,那是丝绸之路的见证。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滇王之印”金印,证实了滇国与汉王朝的密切联系。随着交往的深入,交流地域不断扩展,边疆民族以其畜类等物产,源源不断地输进到中原地区,汉族则将中原出产的丝织品、漆器、铜器、铁器等物质文化带入边疆民族地区。佟先生认为,汉代民族间的交往多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机会也多了,其实汉族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包括比华夏族更多的民族的共同体。它既包括更多民族的血统,也包括更多民族的文化,所以汉代是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非常显著的时期。 魏晋以后,进入黄河中下游汉族农业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敕勒,果然完全融合了,其中有的更是建立了政权。农业和定居,在历史上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这又为汉族吸纳包容更多民族的血统和更多民族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唐代时边远的渤海和南诏出现了封建制,渤海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宁安等地均发现了很大城址。南诏建立的政权设十六节度使,大理也发现有不小的城址。春秋战国之际在中原出现的封建制,在唐代边疆较为发展的地区也出现了。渤海和南诏都使用汉文字体系,也与唐代有相似的筑城理念和建筑艺术。而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又把唐文化带进了吐蕃。到了唐代以后,北方的大族契丹、女真、西夏,又融合于汉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之中了,进一步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统和文化,扩大了汉族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 这是佟先生根据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大致轮廓。读了佟先生的著作,进一步领会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考古意义之所在。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少数民族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分布的地域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过去的田野考古在中原地区开展得很深入,而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显得较为薄弱,研究也欠系统。尤其是像佟先生这样的全景式综合研究,更是还不曾有人进行过的,所以《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的写成更显得重要非常。 相对于内地来说,边疆民族考古尽管还有不少空白与缺环,但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丰硕。边疆考古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对边疆民族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边疆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虽然不平衡,但远比过去人们估计的水平要高得多,边疆古代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边疆民族考古以其目标与方法而言,与内地考古并无本质区别,却也并非是一点区别也没有。主要的区别是有边疆的特点,有民族的特点,各地各族的考古学文化体现有独特的面貌。另外边疆民族考古涉及的范围更广,它要面向内地,还要关乎境外,边疆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从事边疆民族考古的学者,有素质上更高的要求,要了解边疆,要了解民族,也要了解周边国家的考古学文化。佟先生做出了一个榜样,他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佟先生的这部著作,成了从事边疆民族考古的必读书。本书是一个相当全面的索引,有了这部著作,我们不必去东寻西查。书中不仅涉猎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在书后分章节附有详尽的目录索引,为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我相信佟先生的这部著作对于今后边疆民族考古工作的开展还将起到更多的指导作用。 (《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出版,定价:13.85元) (《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8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