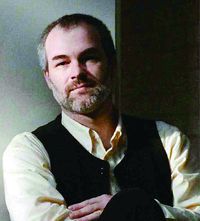 施耐德,曾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Erlangen University)、德国波鸿大学(Bochum University)和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学习社会学、中国史、日本学、政治学和东亚政治,1994年获得近代中国historiography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从2000年起担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学教授,于2006年建立现代东亚研究所并兼任该所所长,今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任教。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史学及政治学和中国思想史。 近年来,民族主义及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的构成与发展等问题又引起了学者的很大兴趣。这一重新关注不仅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再兴有关,同时也与全球化现象以及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相关。 基于对两位被称作“中国的兰克”的杰出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和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的理解,我认为,首先,可以用德国的历史主义做背景来更好地理解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家所面临的有关现代性的主要问题。其次,正如已经被注意到的,一些被称为保守派的思想家确曾显示出对现代性问题较强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是隐含在有关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争论中。 关于“现代性”,我是指正在进行的历史化过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那些曾被认为永恒和普遍规范与价值的相对化。在欧洲,该过程的标志是关于世界结构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假设的衰落,以及伴随而来的传统的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一致性断言的衰落。世界越来越被认为不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而变成一个元世界(meta-world),消解在多种可能的世界观的多样性中,多元世界观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了已经发生的变化。 康德的哲学仅仅是通向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说的“觉醒”的第一步。在他的认识论转变中,康德将世界结构转变为先验的意识的结构,因而为尚在进行之中的世界去中心化过程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被理解为人类实在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的观点尚未发挥作用——康德的世界依然是一个世界,尽管它变成了认识论的。 但至迟到黑格尔,历史便成为中心议题,西方思想界自此以后始终在努力调和历史的相对性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然而黑格尔的历史观不仅基于对历史个别性必须调和普遍精神的确信,它同时也提供了世界历史中绝对精神的目的论表达途径,因而最终使得个别性服从普遍原则。 在德国唯心主义衰落过程中,其大历史观以及启蒙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前提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从赫尔德的个体文化哲学到兰克的历史主义以及狄尔泰的基于生命哲学的历史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反对相对主义的尝试,努力维护个别性,同时不放弃将历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追求。直到一战以后,这些努力才被逐渐取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偶然事件与规范原则之间的裂痕无法调和。例如,海德格尔驳斥了所有证明形而上的绝对性的企图,声称人类剩下的唯一带有普遍性的就是他的历史性。 这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重新建立一个普遍的历史目的论。作为启蒙主义的支柱的普遍理性,丧失了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其本身也被历史化了。大部分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都否认启蒙主义关于进步的观念,并用“发展”的观点取而代之。这一观点基于对个体有机生长的类推,而不赞成一种靠一些在历史的进步过程当中实现的、可知之标准来定的优劣层次。 根据反思“历史发展”的那种历史发展,我认为仅仅用理性进步这样一个概括性的观念或者任何其他绝对性观念作为现代性的特征都是不充分的。现代性应当被理解为各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一方面,是一定程度上哲学的、神学的、历史的,或者科学的和确定性的复兴。另一方面,由尼采的断言所带来的后果,上帝死了,人类从有坚实的形而上学或神学基础的生活中获得解放,也就是说人类被逼迫过一种丧失这种稳定基础的生活。 在中国研究领域,不认同理性主义的学者通常被视为是保守甚至反动的,然而在欧洲,正是保守派对澄清历史性的观念以及现代性的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保守派的更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流派关于历史性、民族个别性和普遍性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 在历史上,史学撰述在中国享有比在西方社会更高的地位,因此毫无疑问在各种现代的争论中,史学往往处在中心地位,不仅引发了对中国认同的重新定位,同时也使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意识日益增强。早在晚清时期,西方观念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用以应对这种挑战的概念甚至语言。虽然史学早已受到进化论世界观的深刻影响,但在20世纪前10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种引进的史学概念与传统的史学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并且多元化的史学话语。(《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