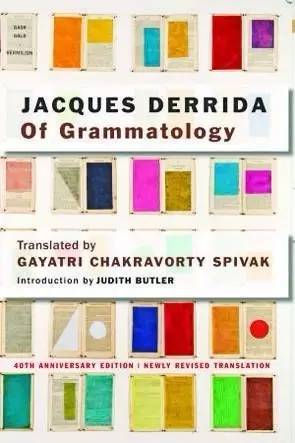 解构主义如日中天的那段时光已恍如隔世。现代学术生活已然植根于解构主义的核心要义——揭示文本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批判西方思想传统中隐匿的偏见,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这场运动曾经多么振奋人心。今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解构主义奠基性文本之一——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40周年纪念版,引发了对解构主义价值的新一轮讨论。《论文字学》原来由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翻译,此次她修订译本,朱迪斯·巴特勒撰写前言。 今天的斯皮瓦克是学术界的超级巨星——她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同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院的共同创始人。而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斯皮瓦克着手翻译《论文字学》时,不过20多岁,当时这位爱荷华大学的助理教授在学术界籍籍无名,德里达在美国也鲜为人知。斯皮瓦克习惯从图书馆目录上订购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有必要一读的书,从而使自己的智识与时代同步。就这样,斯皮瓦克读到了《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认为《论文字学》非同寻常。她离开康奈尔大学时她的老师尚未见过德里达,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斯皮瓦克更无从得知德里达是谁,但她决定翻译这位没有名气的作者的书。她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听说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在做译著,所以在1967年底1968年初的样子她愣头愣脑地写了一封问询信,结果真的得到了翻译《论文字学》的机会。 《论文字学》是一部高度理论化、艰深难懂的著作,今天读起来仍然具有挑战性。而斯皮瓦克是那个看起来最不可能翻译德里达著作的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英语法语都不是她的母语——翻译这样一部复杂的高级理论著作是个大胆到近乎荒谬的决定。但斯皮瓦克不仅翻译了这本书,还写了一篇长度相当于专著的序言,把德里达介绍给新一代的文学研究者。这是斯皮瓦克加在翻译合同里的条款,她说,如果她不能写一篇和专著一样长的导言,就不做这本书的翻译了。 斯皮瓦克1976年首次将《论文字学》译成英语,40年过去了,她一直在研究德里达,对这本书也有了新的理解。“欧洲中心主义”这个词在1967年还不那么常见,因此斯皮瓦克当时并没有重视它。1930年,德里达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从内部遭遇西方哲学,审视着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斯皮瓦克认识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关键意义;并能更清晰地把握贯穿此书的理路——关于应该如何阅读、如何生活;她对黑格尔的认识更深入了,可以看出期间的关联性。 斯皮瓦克认为这本书是对西方哲学的批判,而这也是解构的一部分。解构不只是破坏,也是一种建构:从内部说话,这种批判基于与批判对象的亲密关系,而不是从远处观望的批判。正如斯皮瓦克的老师保罗·德曼曾对另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说,“弗雷德,你只能解构你所爱的东西。”《论文字学》也是真正熟悉其批判对象——西方哲学。德里达要解构的是在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几百年的主流话语,由于这种主流话语的建立,许多群体都被排除在外。非洲人能通过口传追迹七代,而现代西方人已不再具备这种能力。“书写”代替了“记忆”。德里达将此与弗洛伊德相联系。现实正是经过编码,能够为其他不在场的人所理解。而德里达研究这一能力在哲学传统中如何被压抑。 斯皮瓦克翻译《论文字学》时并没有和德里达本人接触,直到1971年两人才相见,在一次会议上,斯皮瓦克都没认出这是德里达,还是德里达自己主动上来相认。之后,两人便成了朋友。用斯皮瓦克的话是“盟友”。这个亚洲姑娘既不是法语博士,也不是法语或英语母语者,翻译了他的书,使这本书走出欧洲高级哲学小圈子,走向世界——不是因为崇拜,她根本都不认识他。这让德里达非常欣赏。德里达皮肤黝黑,两人结伴吃饭的时候,会有人把他当成印度人,文化印记很强的斯皮瓦克有时还会穿纱丽,这时候德里达便会开玩笑说,“是的,我就是印度人。” 在随后的几十年,斯皮瓦克开辟出几条看似相互独立的职业道路。她成了先锋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发表了《底层人能说话吗?》,开启了后殖民研究。但斯皮瓦克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她还在家乡印度为文盲创办了小学,曾在那里教过几十年书。很少有人能将理论和实践如此融于一身。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