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生长于北京,但身为蒙古族人的邢莉,自幼便因着家族渊源,而接受着蒙古文化的教育。而在成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后,她更是将蒙古文化作为自己的课题研究方向。 最新出版的《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是邢莉最与众不同的一次写作尝试。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她,将民俗放在了整体的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去探讨,并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和草业科学等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历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中国经营报》:这本书为何要选择从明朝开始的节点?从明朝到当代这一段时期,对于游牧民族及其文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邢莉:这个节点其实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个转折点——从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成吉思汗时代,游牧文化随着政权的扩张而达到了顶峰。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图片里展现,几十头马车拉着一个巨大的蒙古包——我们称之为蒙古包的宫殿——在游牧。直到元朝,游牧文化还可以说是独立的、未被冲击的文化体系。而那个时代,我们也称之为“大游牧时代”。而在明朝替代了元朝以后,各种原因导致了游牧文化开始被农耕文化所冲击,蒙古族也分支出两个方向,其一是坚持游牧的支脉,我们称之为长袍蒙古;而转向农耕的支脉,就被称为短袍蒙古。 所以,可以说,明代开始是蒙古族的巨大转折点,而我这部书主要的脉络就是从其“变迁”谈起。当然,大规模的变迁是从清代中期开始的,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自然原因,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治原因。 《中国经营报》:你是最早提出草原文明的人,而此次所书写的游牧文化是否就等同于草原文明呢? 邢莉:应该说,游牧文化是草原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草原文明并没有作为独立的体系与中原文明并列,顶多被认为是半文明,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往对文明的认知是人本位的,所以人类过得是否富裕安稳便成了重要的衡量指标。在那种标准看来,游牧民族是落后的、原始的。而如今的文明评判标准,着重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么草原文明,尤其是游牧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及生态的保护作用就立刻显现出来。游牧民族不会去破坏土地和生态,他们哪怕辛苦自己,也要遵循草原的生态规律。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不游牧?妈妈回答,不可以,因为我们的游动保证了草原母亲的呼吸。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体现在思维模式上。比如在汉语里,草是一种贫贱的东西,这是由于农耕过程中,草是需要被拔除的。所以汉语里的草菅人命、草民等,都是贬义的。而在蒙古文化里,多是歌颂草的,视草原为母亲。这进而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这些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也对如今如何保护草原的探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位海拉尔的老牧民告诉我,蒙古族哪怕成吉思汗也是不留坟墓和墓碑的,是因为蒙古族认为,不能在草原上留下任何伤痕。蒙古族人的价值观,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自然为本的。 《中国经营报》:随着现代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游牧民族也都形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会不会也导致草原文明及游牧文化的消失? 邢莉:如果定义草原文化,我认为就是依托于草原的生活方式,草原作为基本并必须的生产资料的地位没有改变的话,草原文化就依然存在。但是就游牧文化来说,的确有这种可能,而当下就处在这种文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我的书里展现的是蒙汉融合的一个过程,因为游牧的地区并不是说一下子被占领的,而是逐渐的,通过移民而导致的缓慢的过程。当然,我的书中也提到了几个关键时期,包括清朝的旗县分治,以及建国后的分草场,都是使游牧文化逐渐衰落,及向农耕文明转移的标志之一。 分草场其实就是通过一种行政命令,使游牧的生活方式固定下来了。但是草场固定了,反而不够用了,随着放牧数量的加大,固定面积的草场总是不够使的,而且又没有时间进行自我修复。早先去调查的时候,碰到一户已经很富裕的牧民,他家有很珍贵的白马和白骆驼。他说他正要出去,要跑到很远的边境去放牧,因为居住的地方分的草场根本不够用。所以,研究游牧文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会对当下我们该如何进行草原的保护和畜牧业的发展,起到指导意义。 这其中不仅仅包括生态环境的治理,也包括游牧民族的人员安置等问题。硬性把他们搬到可以定居的地方,他们是否可以适应,未来干什么,都是需要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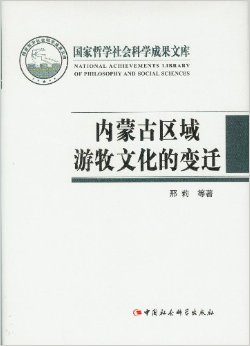 (本书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