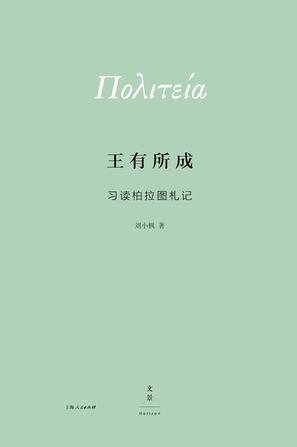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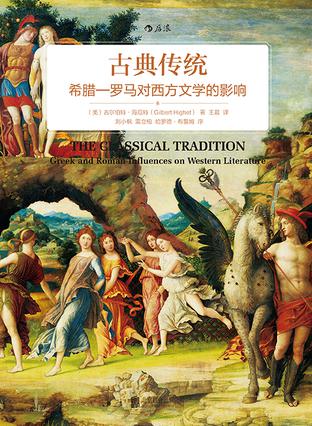 近几年,“古典学”日渐流行起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康德的著作曾在沙龙里十分流行,“相对论”一诞生就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古典学的流行与此颇有几分相似,一则,古典学的确在学术界、知识界、出版界甚至大众媒体成为具有相当热度的话题,特别是书店里关于“古典学”、“古典研究”的书籍和期刊一下子多了起来;不过,古典学研究的难度和阅读所需要的知识积累,恐怕并不在读通康德和弄懂相对论之下。所以,古典学成为一种时尚,就十分有意思了。 何谓古典学?若是笼统来说,这个词和“国学”有些相似,只不过古典学首先是泰西的一门学问、学科,是西方的“国学”,因此,西方的古典学“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维拉莫威兹),包括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校勘整理、文物的发掘辨识以及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一众学科的研究。古典学在西方,既是一种具有通识性质的、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个人素质,也是一门极为规范、严谨,对古代语文能力要求很高的学问。 因此,尽管目前中国没有古典学这门学科,但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中国自传教士东来之后就没有停止过。远的就不提了,只说最近几年,先后出版了西方古典学不少经典著作。像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三联书店,2008)展示了作为现代学科、使用科学方法的古典学,不过毕竟篇幅太薄,两年后,和维拉莫威兹生卒年基本重合的英国学者J. E. 桑兹的通史巨著《西方古典学术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世纪文景,2010)出版,这既是饱览西方古典学全貌的必读书,还可以作为研究的工具书。因为卷帙浩繁,这本书的第二、三卷中译本至今尚未面世,第一卷只写到1300年。不过没有关系,不久前,上述两位学者的后辈,德国人鲁道夫·普法伊费尔的《古典学术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已经出版,此书虽然没有涉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相关内容,但毕竟后出,吸收了前著的优点,用力更深,内容更准,而且一直写到1850年。我在书店里找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13年推出了“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至今仍在不断推出新作,既有译著,也有本土学者的汉语西方古典学研究,还有影印的《希英词典》《拉英词典》(2015)等,值得关注。 古典学术的出版如此繁荣,就连并非专门出版古典学术的出版单位也推出了一些书籍,如后浪出版公司就出版过人民大学外籍教师雷立柏的《古希腊语入门教程》《拉丁语入门教程》(2014),还在公司里专辟房间供学生向雷立柏问学,传为京城美谈。不久前,又推出了美国学者海厄特的《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2015),这本书虽然蒙受“教科书”之讥,实则以讲解详细、清楚明白而成为名著,且本书从文学角度论述,远比他书更为吸引普通读者。 看到这么多严谨的译作和著作,一本本充实着汉语学术,我们不禁想知道,如此专门化的学术怎么就成了大众的热爱、出版的宠儿呢?这不得不提到刘小枫等学者。刘小枫在国内鼓吹对西方学术从源头进行梳理、解释已经十几年了,运作出版了大量西方古典学的著作。同时,他的目的却是建立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中国的“古典”。刘小枫切入中西古典学的角度,简言之,分别是施特劳斯学派和经今文学,学术界内外对此的声音和调门因此各有不同。但不得不承认古典学的热度与刘小枫等人的弘扬是分不开的。仅看刘小枫本人,近一二年再版、增订、收集了他前几年的一些著作,如《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3)、《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5)、《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世纪文景,2015)等,不久前还效仿朱熹,亲自编译了一本令人十分惊讶的《柏拉图四书》(三联书店,2015)。而他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在今年初隆重举行了十五年三百五十种出版纪念会。 这些实绩首先是书籍的出版,也的确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和刘小枫的个人意图,因此,引起的争议一直存在。面对争议,我更关注的是西方古典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和风气上的影响,这个话题,等我再去书店巡礼一番,才能有答案。不过,我忽然想起多年前读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时抄录的一段笔记,说的是古典学的“大方向”,共同走向同一个目标,争议不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古典学的任务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