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文为新书《广州贸易》的结论部分。作者提出当今对广州贸易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25%~30%贸易量的内容,由此得出的认识实质与清政府所为无异,即在没有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贸易决策。而《广州贸易》一书则以瑞典、荷兰、丹麦、英国、美国和葡萄牙档案作为研究基础,以更完整的数据呈现彼时广州贸易的运作机制。范岱克(Paul A.Van Dyke),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今,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最好和最详细的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这些事情在中国显得不重要,故没有留下记录并保留下来。数位中国行商变得极其富有并建有大庄园,但其财富没有传之后世,关于他们生活的许多记忆也早已消失。这不能归咎于是广州体制的设计者深思熟虑或有意破坏或损坏地方利益,更应该是他们太过关注国家事务,从而忽视了个体的结果。 仅有涉及国家事务的记录被保护和珍藏下来,所有来自较底层的其他汉文记录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文件应该数以百万计(甚至可能数以亿计),包括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方海关税口140年的每日记账簿;成千上万签发给在黄埔与广州之间转运货物的转运船的牌照;数以百计粤海关存留的用以审核文件真实性的船牌核对单;粤海关140年记录每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进出口情况的分类账本;成千上万的船只丈量计算记录;为每个外国公司制定的数十份规章,列明了交易条款和规定;成百上千份发放给外国人允许其在西江航道航行的通行证;数以千计来自三角洲直达舢舨向粤海关监督报告下游一带海事活动的报告;成百上千被派送至外国商馆及船只的信件、法令和通告;以及数以百计的派发给通事、买办和引水人授权其为外国人服务的执照。 我们知道行商也保存有详细的记录,当交易出现问题,诸如欠账、包装错误或货物未交付时他们常常会要求查找先前的交易记录。行商偶尔也会拿出过去外国人未能偿还的债务凭证,这些都能在其记录中核对。我们还知道行商保存有成百上千份与外国人签订的合约,有时他们必须查阅这些文档以查实过去几年贸易合约的条款。所有在外国档案中出现的文献都有用汉文写的材料,因此我们能证明其的确存在过。但是行商不敢长期保存这些记录,不需要了就会销毁它们,唯恐其落入某位贪婪的官员手中。这是中国商业缺乏保护的另一个标志。 如今,仅有几百份详细的汉文记录保存了下来并为我们所知,而且都藏在外国档案馆中。缺乏对复原历史记录的关注是另一个清楚的标志,即地方个人利益及其当地遗产的保护(包括对当地财富的积累和长期保护),并不是广州体制基本思想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历史中遗忘得最彻底的是帆船贸易,几百年来数以千计的帆船和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其中,但现今几乎没有文献讲述他们的故事。 本书使用的数百条详细的中文贸易记录,都是来自瑞典、荷兰、丹麦、英国、美国和葡萄牙档案,都明显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些文件都是当年定期在广州记录下来的。从外国记录的信息可以看出,在控制贸易的粤海关和实施贸易的中国行商两方面,我们都能够描述其成熟而系统的记录保存原则和实践。目前仍然保存下来的,来自三角洲一带海关税口的任何详细汉文记录都是那些派送到澳门的文件,它们之所以幸存至今,是由于它对葡萄牙人来说十分重要。 中国唯一得到系统保护和保存的档案记录,是官方的往来文书。但是这些档案只包含了参与贸易的个别人的信息,而这些人的活动以某种方式与国家有关。一则简短的笔记可能会记录下夷欠严重的、犯了罪的、寻衅滋事扰乱贸易的、影响呈送朝廷税收的诸如此类事项的中国人,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名字就会消失。这些官方文件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前文提及的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细节内容都保存在外国档案中。 缺乏对广州体制自身历史的重视是其最大的弊端之一,因为这些记录是其高效运作和维护至关重要的信息。没有关于贸易所有细节和环境变化的详细内容,就没有办法准确预测或确定贸易何时、何事、何地、为何、如何改变或如何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公司(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保存了在中国的记录副本,他们的大班就能够将这些材料作为参考资料,更好地了解贸易本身以及他们过去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当然这些信息本身并不足以确保自身能够被保存下来。如果不采取措施,或者从这些信息上得出一些不实在和不切实际的政策,那么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在一个有持续需求的静态世界里,经济走势或态度没有任何变化,技术或生产也没有太大差别,也许密切关注贸易与环境的各个方面并不重要。但是18~19世纪的广州肯定不是这样。由于未能保存其详细记录,广州体制必然失败。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朝廷大臣尽管不断采取措施,但治标不治本。由于官员并没有控制住那些底层发展出的问题,问题出现多年后,在通常由一次危机暴露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却采取了反作用的措施。 由于缺乏收集贸易和更广泛国际环境的信息,在行政结构被削弱之前,没人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深入理解,朝廷努力支撑这种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打败这种体制,是因为这种体制自身已溃败。 清政府需要一个拥有主动权、意愿、权力和必要信息的行政部门来分析弱点、检讨贸易政策和工作程序,并在需要的时间做出正确的纠错。但由于没有贸易所有细节和所在环境变化的详细叙述,就没有办法形成准确或全面的认识,以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政策。此外,还需要互相制衡的信息交流,以便行政官员能够确保重要细节没被篡改或遗漏。但是,广州体制中缺乏这种机制,至少没有有效的机制,其结果就是官僚机构做出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是基于不完整、不准确和具有误导性的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与现在的研究情况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将有可能让研究者吸取清政府失败的教训。前文提到的新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所有关键细节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信息,我们无从理解贸易的运作。以往贸易史也是依靠片断画面来讲述整个故事。正如序言指出的,这一结果有很好的原因,但导致了类似清政府的境地。由于缺乏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数据以及对中国帆船和澳门贸易的了解,过去的历史论述一般都省略或忽略了中国帆船和澳门方面的内容。其他小公司的经验也很大程度上在口岸史研究中被忽略,尽管它们对贸易的发展也很重要。许多诸如亚美尼亚人马修斯·约翰内斯这样非常重要的代理商很少得到关注。 正如前文曾论述的内容,18世纪60年代这部分贸易内容占了整个广州贸易的70%,地位举足轻重,塑造和影响了历史。他们每个人都在促进贸易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弥补了贸易中的缺漏,保持着这台贸易机器的运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历史中被遗忘,在于研究重点通常被放在贸易瓦解上,只关心其衰落的原因,却不关心其增长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弄清楚该体制如何成功运作,又如何去解释它的失败呢?过去获取和利用许多不同历史记录(多地点、多语种)困难重重,导致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 于是,直到现在研究者对广州贸易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25%~30%贸易量的内容。虽然原因和环境都不同,但分析贸易却不考虑其所有部分,这便与清政府所为无异:没有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贸易决策,定义商贸,确定问题与解决方案。办事员与官员没有理解如此庞大的贸易机器,缘于他们没有获得其中所有细小部分的信息。本书呈现出的是一个崭新而更全面的图景,因为研究的基础是掌握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释这台机器如何运作。1835年清政府也开始收集和接收与贸易相关的非常详细和准确的信息,然后朝廷终于看到哪些方面需要做出改变。但对清政府而言,想改变历史进程为时已晚,这些问题已经被忽略太久。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重新审视证据和修订历史书尚且不晚,我们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呈现这些历史的本相。本书作者希望,研究者能够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将来写出更详细和全面的历史,将此项研究遗漏的地方填充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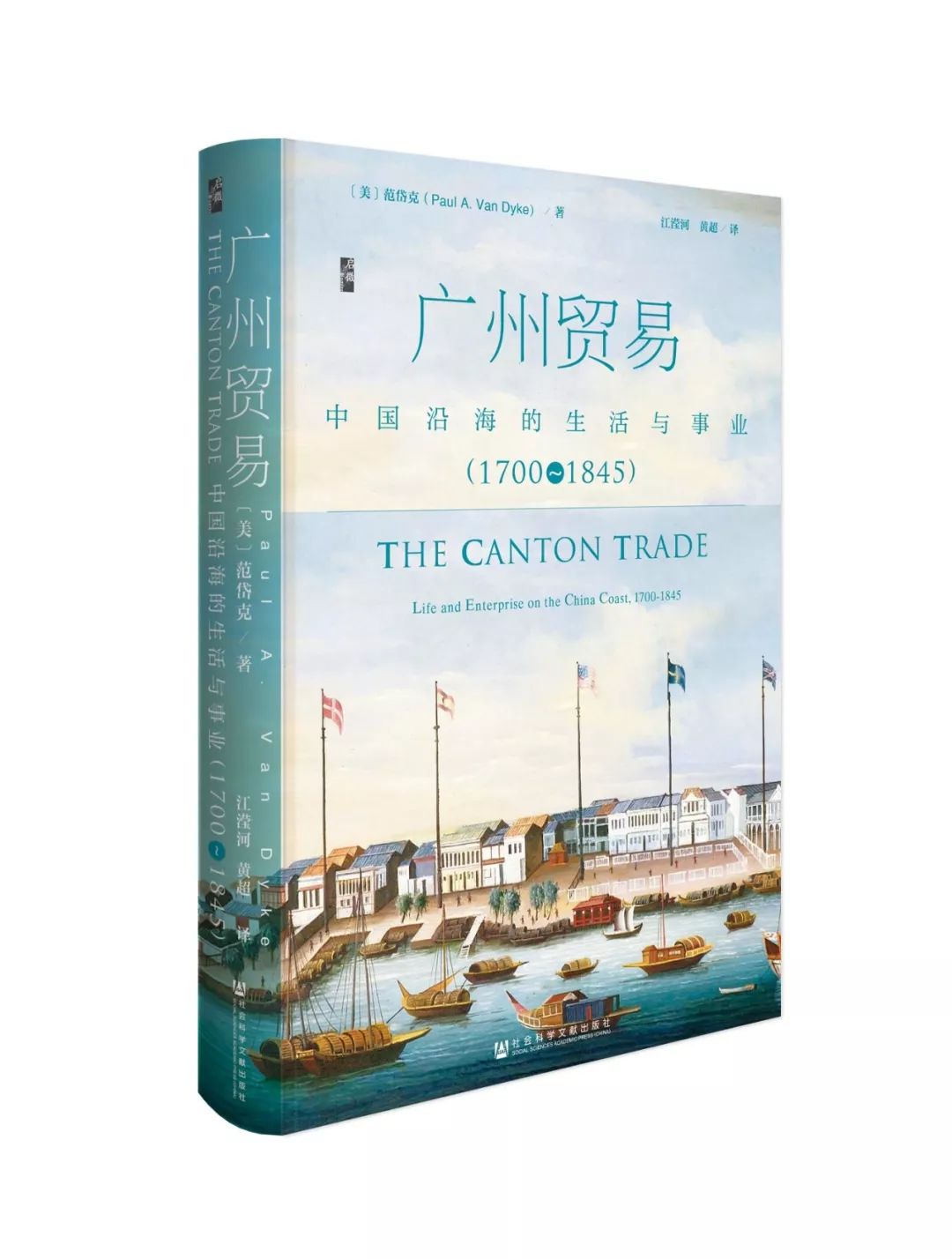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