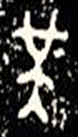|
西周成王時期的沬司徒疑簋過去常被稱為“康侯簋”,是最著名的周初青銅器之一。該器傳係1931年河南濬縣辛村(今屬鶴壁市淇濱區龐村鎮)衛侯墓地(出土之地有三種説法:浚縣、汲縣(1988年改名衛輝市)、輝縣固圍村),後流散到英國,1977年入藏於在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簋高21釐米,無蓋,侈唇深腹,口沿下飾涡纹與四瓣花紋,腹飾直棱紋,雙耳上有帶扁角的獸首,下有垂珥,圈足紋飾與口沿下相同。器的圖形見《商周彝器通考》259,銘文見《殷周金文集成》4059[1]。  沬司徒疑簋  沬司徒疑簋銘文 先把簋的銘文寫出來“王朿(來)伐商邑, 與“沬”有關的銅器還有如下幾件: 3件爵,銘文是“ 沬伯疑尊“ 第一件沬伯疑卣“ 第二件沬伯疑卣“ 沬伯疑鼎“ 以上這些銅器都是同一人所作,“沬伯疑”就是“沬司徒疑”,司徒是他的職官名稱。所謂的“沬”字,有兩種寫法(從“口”或從“甘”):   此字陳夢家先生隸定為“ 唐蘭先生把此字隸定為“ 杜正勝先生認為“ 張光遠先生把此字隸定為“ 周永珍先生認為“ 李春桃先生認為此字讀為“沬”是可信的,字形分析,當是我們之前討論甲骨金文中的“沐”字“ 杜勇先生認為沬邑除了泛指朝歌外,它還是朝歌城郊的一個小地名。《詩•桑中》:“沬之鄉矣”,所指為衛國之都朝歌,又“沬之北矣”“沬之東矣”,則表明朝歌在沬之東北,與統稱朝歌的沬邑並非一地[4]。 對於這種細微差別,清人馬瑞辰有過詳實考證,不妨迻錄如次:“沬,《書•酒誥》作妹邦。沬、妹均從未聲,未、牧雙聲,故馬融《尚書注》:“妹邦即牧養之地”,蓋謂妹邦即牧野也。妹、牧、母亦雙聲,牧《說文》作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後漢書•郡國志》“朝歌南有牧野”,正與妹在鄘地居紂都之南者合。《左傳》“鄭人侵衛牧”,杜注:“牧,衛邑。”牧邑即沬邑也。《酒誥》鄭注“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據说沬之北、沬之東為朝歌,則不謂朝歌即沬明矣。其说“妹邦,紂都所處”者,紂都之郊牧亦可以紂都統之也。此詩孔疏“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猶鄭君以妹邦為紂都,亦統言之耳。”[5] 這個考證很精闢,最大的價值在於厘清了不同語境 下的“沬”有泛稱和專稱兩種涵義作為泛稱的沬妹指紂都朝歌,專稱則指朝歌南郊牧野的沬邑。據我們研究,邶鄘衛之“鄘”當在今河南衛輝市東北十三里處的倪灣村,與牧野今河南新鄉市北正相鄰近。《桑中》一詩歸入鄘風,正合其宜[6]。 明確“沬”的兩種涵義,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沬司土疑的身份。關於沬伯其人,過去杜正勝先生以為是“殷獻臣”,是很有見地的。沬伯疑諸器銘文前後有殷商舊族的族徽,即是明證。金文稱“沬司徒疑”,是以“沬”為氏名,司徒是康叔衛國政府的司徒,而不是商郊沬邑的司徒,因為他不能既是沬伯,又是沬司徒。說他“在康侯的政府中任沬司土之官”,把這裡的“沬”與“衛”視同一事,是不確切的。實際情況是,沬為疑在殷商時的封邑,其地又稱“牧”,“即《牧誓》的牧野”。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封康叔于衛,以治殷畿,疑作為“殷獻臣”或“商耇成人”,仍享舊有爵邑,故稱“沬伯”。之後被周人啟用,出任衛國政府的司徒,故稱“沬司土疑”。所以簋銘中的“沬”,非謂朝歌或衛,而是特指商郊的沬邑,用作沬伯之氏。由於冊封康叔為衛君,須昭告國之疆界,如《左傳•定公四年》所言“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因而掌管衛國土地圖籍與人口的司徒疑亦須參加此次冊封儀式。他以此為榮,故作器紀念先考[7]。 目前學術界大部分學者對於此字的看法,同意陳夢家和唐蘭先生的意見,認為此字是“沬”也就是《尚書•酒誥》中的“妹邦”,《詩•鄘風•桑中》:“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毛傳:“沬,衛邑。”詩中又“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可知沬為衛邑,地處淇水之濱。這個衛邑,《水經注•淇水》引《晉書• 地道記》:“朝歌,“本沬邑。”故稱“朝歌、殷墟、商墟、沬、妹、衛、舊衛並是一地” 我們認為以上看法中,周永珍先生對於此字的觀點最值得注意,認為“
“某”可以從“口”,也可以從“甘”,可以從“木”,也可以從“大”。以上所謂的“沬”字,只不過把“某”所從的“甘”或“口”寫在了“木”的下面,而不是上面,這在古文字裡面很常見,字上下的位置不固定,左右結構也可成上下結構。所以此字當隸定為“ 康侯簋“王朿(來)伐商邑,卿盤“周公朿(來)伐商”,何簋“(周)公䧅殷年”,太保簋“王伐录子聽”,小臣單觶“王後反克商”,清華簡《系年》第三章“成王屎(纂)伐商邑”[10],這些指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周公二次東征,平叛武庚和三監之亂[11]。 康侯簋“王朿(來)伐商邑, 鄙于衛,雍伯鼎“王命雍伯鄙于ㄓ”,《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群公子皆鄙”,杜預注:鄙,邊邑。齊侯鎛“與鄩之民人都鄙”,越王朱句鐘“之後者(諸)侯自寧(寧),四啚(鄙)同安”,殷簋“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友司東啚(鄙)五邑”,恒簋蓋“令(命)女(汝)更克司直啚(鄙)”,賓組大字甲骨“土方征我東鄙捷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董珊先生認為“鄙于衛”,應理解為以衛為邊邑,這是增大康侯的封地,也就是“徙衛”[13]。 李學勤先生認為“鄙于衛”,分封康叔到衛,劃定國土的邊境。牧司土疑眔啚(鄙),眔,有“參與”的意思,這句話的大意是“牧司土疑參與了康叔封衛,劃定國土邊境的事情”[14]。 為什麼“牧司土”要參與這個事情呢,以前由於對“牧”字沒有正確的釋讀,對於這一問題大家都不甚瞭解,現在明白了此字是“牧”字,我們就明白了。誕令康侯啚(鄙)於衛,其中的“衛”指的是現在“安陽殷墟一帶”,啚(鄙)於衛,也就是在劃定衛國土的邊境,衛的郊外,衛指商都朝歌。衛郊也就是“商郊”,正好可以和《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中的“商郊牧野”相吻合。 牧野,河南省新鄉市的別稱,是史上的一個地名,其地在今新鄉市北部,包括新鄉市所轄鳳泉區、衛輝市、輝縣市、獲嘉縣等地。牧野原非專有名詞,這裡是相對于殷都朝歌(今河南鶴壁市淇縣)而言的。從朝歌城由內向外,分別稱作城、郭、郊、牧、野。《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歷史上的牧野主要指衛輝市,廣義上的牧野也包括新鄉市鳳泉區、獲嘉縣部分地區。牧邑的具體位置,東漢的許慎在其所著的《說文解字》裡說得最為明白。他說: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漢代的七十里,約合二十公里,正是衛輝市區所在地[15]。 上面我們提到康侯簋一說傳係1931年河南浚縣、汲縣(1988年改名衛輝市)、輝縣固圍村出土,這個出土地點正好是“牧野”所在地,可以為我們把此字釋讀為“牧”提供一個佐證。 綜上,康侯簋銘文“王朿(來)伐商邑, [1]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10卷3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 [2]以上資訊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一書。 [3]以上關於所謂“沬”字各家的考釋觀點,引自馬飛:《西周成王時期銅器銘文集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50-189頁。 [4]杜勇:《關於沬司土疑簋考釋的幾個問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5]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第178-179頁。 [6]杜勇、孔華:《關於邶郞衛與淶水北國的地理糾葛》,《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第 78-86頁。 [7]杜勇:《關於沬司土疑簋考釋的幾個問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8]周永珍:《釋康侯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年,第295-304頁。 [9]張儒、劉毓慶:《漢語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頁。 [10]黃甜甜:《<系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補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3月,第29卷第2期。 [11]李學勤《讀<系年>第三章及相關銘文劄記》,《夏商周文明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61-263頁。 [12]董珊:《清華簡<系年>所見的“衛康叔”》,《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87頁。 [13]董珊:《清華簡<系年>所見的“衛康叔”》,《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87頁。 [14]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释读沫司徒疑簋》,《夏商周文明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77-180頁。 [15]宗福邦等:《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400頁。 [16]彭裕商:《沬司土疑簋考釋及相關問題》,《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80-84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8年6月17日19: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