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严成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读史札记 “上海律师甚多败类”: 从一起名誉纠纷看民国律师形象 李严成 在近代中国律师职业发展史上,上海律师可谓是最受瞩目的一个群体。关于近代上海律师,已有相关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论及。有学者认为,自民国初年律师制度建立,国家实行司法监督与行业监督双重管理体制,对律师的管理日趋严格。在民国时期,律师已经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在上海建立起来,律师执业亦日益规范。关于律师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有学者肯定律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在民国律师队伍里,虽不乏一些具有正义感的律师,但更多的是败类和丑角。也有学者指出人们习惯用丑化甚至妖魔化的讼师形象比附律师,严重影响了律师的正当性形象,笼罩于讼师阴影下的近代中国律师职业,很大程度上只有一种脆弱的正当性。就上海律师而言,既有受人称颂的“人权卫士”,也有为人所不齿的“现代刀笔”,尽管后者只是少数,但严重影响了律师在社会中的形象,削弱了律师职业的社会信誉。关于这些律师“败类”及其劣行,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已有较详细生动的刻画。但是,民国律师群体是否能从传统“讼师”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构建新的自我形象,律师如何对待同行的恶意言行以及律师公会这一行业自治组织如何应对有损律师形象的事件,尚缺乏细腻、深入的探讨。 本文以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起名誉侵权纠纷为个案,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代理律师在法庭上的一句“上海律师甚多败类”引发轩然大波,不仅触动了律师群体的敏感神经,也聚焦了社会公众的质疑目光。这一纠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发生于律师之间,是同行之间的相互指控。它不仅关系到涉讼的双方律师,也牵涉了上海律师公会这一行业自治组织。《申报》对这一案件多有报道,上海市档案馆也存有相关案卷材料。综合这些史料,本文试图梳理这一纠纷的诸多细节并对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 “连环案”:由坟产争夺案而起的名誉侵权案 瞿周两姓为争夺坟产,争讼多年。涉讼坟产位于上海小西门外赵家牌楼,面积约2亩5分,户主为周檀溪。光绪二十四年(1898),瞿祥麟买进这一坟地,次年将其祖坟的8具棺木迁入。光绪三十年(1904),瞿祥麟将该地皮契据6张以300元大洋抵押给刘姓。光绪三十二年(1906),瞿祥麟与周菊坪(时为官契局局长)发生坟产买卖纠纷,或许由于周氏的官方背景,坟产易主。瞿姓并不甘心,一直保留坟产契据,其中包括抵押给刘姓的契据凭证。1930年春,周菊坪之子周鉴人草签协议,以16300元的价格将坟地售予陆幼渊,将瞿家祖坟的8具棺木迁至建汀会馆。瞿家知悉后立即加以阻止。瞿家本拟起诉,但经疏通,周家承诺给大洋若干,加上双方亲戚以及地保都主张和解,瞿家也表示同意。4月30日,瞿祥麟之子瞿顺祥以700元大洋收回抵押契据。5月4日,瞿周两家在上海大富贵菜馆订立和解协议,周家给瞿家大洋6200元,瞿家交出坟产契据。周鉴人与瞿顺祥因事未到场,瞿家委托汪承宽律师代理,周家则委托苏佐贤为全权代表,聘顾永泉律师为法律顾问,地保郁炳臣为中介人,两家还有亲戚数人在场。5月26日,周家正式签订坟产买卖契约,但拒绝交付承诺给瞿家的6200元大洋。为此,瞿家向上海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控告周家私掘坟墓、诈财、倒卖地产,请求依法严惩,并归还棺木。 上海地方法院立案后,饬传被告周鉴人到案,判令交保候审。7月24日,刑庭庭长沈炳荣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在法庭上,瞿周双方各执一词,法官无法判明坟产归属,只好宣布休庭。7月30日,瞿周坟产争讼案再次开庭,有两位律师作为证人出庭,即汪承宽与顾永泉。汪承宽律师称,他受瞿家委托来到大富贵菜馆,达成了和解协议,并由他经手将1张方单、5张契单转交给周家的法律顾问顾永泉律师,此事中介郁炳臣可以作证。顾永泉律师则称,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后,瞿家仅交出白契2张。针对两位律师截然不同的证词,庭长质询汪承宽证言是否真实,汪表示:他身为律师,不会作假。顾永泉则斥责汪承宽“太无人格,律师中之败类”。法官当庭制止,指出二人同为律师,不得当庭侮辱。法官还提出质询:为何和解协议写有“所有一切凭证,不书种类”?汪承宽称,这是顾永泉有意所为,还当庭指认顾永泉行贿、诈财。据他说,5月26日,坟产买卖契约生效。上午11时,顾永泉与苏佐贤来到他的事务所,行贿2000元遭拒,企图侵吞6200元和解款未遂。对此,顾永泉断然否认,称其当日上午10时与郁炳臣一起到陆幼渊家,郁炳臣要求陆幼渊直接向瞿家付款,陆氏表示应由周氏直接交付瞿姓。他们12时3刻才离开陆家,不可能有行贿的时间。至此,两位律师的证词再次相左。法官认为需要进一步取证,遂宣布退庭。 瞿周坟产案休庭后,汪承宽认为自己只是履行律师职责,为当事人谋利益,不应当庭受侮辱,于是一纸诉状将顾永泉律师告上刑庭,指责其侮辱人格。顾永泉也不甘示弱,除答辩外,又反诉汪承宽当庭诽谤,还向上海律师公会指控汪承宽对其诬告、诽谤。顾永泉指出,在签订坟产和解协议之前,瞿家声称坟产契据甚多,但在立下字据之后,只拿出两张毫无价值的“白契”,所以周家不愿履约。而汪承宽律师在庭审中帮瞿家作不实之证词,谎称在订立和解协议前,双方已看过证据,事后瞿家交出绝卖契约5张、方单1张,这“关系个人之人格尚小,关系全体律师人格与律师风纪甚大”,要求律师公会召开执监联系会议处理。收到顾的指控后,上海律师公会当即决定要汪承宽在一星期内作出合理解释,并照转顾永泉原函。汪承宽回应称,他对顾永泉的不客观指控表示震惊,瞿周坟地争讼的是非曲直自有法庭认定,待人格侮辱之诉解决后,他再向律师公会汇报。律师在法庭上恶言相向,本已损害律师行业的形象;若为此对簿公堂,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考虑到这一点,上海律师公会特意委派执行委员汤应嵩从中调解。但汪承宽律师认为人格侮辱之诉与瞿周坟产案应同时解决,不同意和解,坚持诉诸法庭。 8月19日,律师人格侮辱案在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公开审理,庭长仍由沈炳荣担任。原告汪承宽聘请陶嘉春律师代理,被告顾永泉则聘请邹玉律师为之辩护。在法庭上,原告汪承宽陈述了案件经过,请求法庭依法判决,并将判决结果公开登报。顾永泉辩称,自己说汪承宽律师太无人格,是因其当庭诽谤;说汪律师败类,是因为其作伪证,这是证人之间的争辩,并非侮辱,而汪承宽的诽谤则是明显的。 顾永泉的辩护律师邹玉也发表了意见。他说,被告的言论只是对原告诽谤的自辩与自卫,意在斥责对方不应做无人格之事,自然不能认定为公然侮辱。邹玉坚决反对与原告和解,请求法庭对原告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并称“上海律师甚多败类”。此语一出,原告的代理人陶嘉春律师当即提出抗议,指出本案当事人、代理人与辩护人同为律师,要代律师公会全体会员警告邹玉不得当庭诽谤,并要求邹玉指出究竟谁为败类律师。邹玉辩称,此语是泛指,所谓律师败类即行为不检者,有上海律师公会信函为凭,并非特指。汪承宽也气愤地指责邹玉公然侮辱,邹玉回应说若为故意侮辱,须说汪律师是贼。汪承宽愈加气恼,要求书记员记入笔录。控辩双方的激烈舌战,不时引起法庭旁听者的哄然大笑。 其实,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人格侮辱的罪名是否成立,取决于坟产争夺案的证词真伪。如果汪承宽律师确实做了伪证,那么对顾永泉的指控就难以成立。但问题是,坟产争夺案尚未审结,证词真伪也未能确定,顾永泉此时指责汪承宽“太无人格”,是“律师败类”,就涉嫌人格侮辱了。顾永泉及其辩护人则坚称是在汪承宽作伪证后才斥责其为败类的。在听取当事人辩论后,庭长宣布改日再审。他还指出,当事人双方同为律师,事关律师声誉,建议庭外和解。经法官再三劝解,汪承宽也认识到继续纷争会进一步伤害律师的整体声誉,表示愿意和解,但前提是对方要有“悔过之意”。 二、 名誉侵权:“上海律师甚多败类”风波的演变 尽管法官、上海律师公会都希望这起律师名誉纠纷尽快和解,但邹玉律师在法庭辩论中抛出的一句“上海律师甚多败类”,刺痛了律师界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风波。上海各大媒体纷纷登载这一消息,律师界反应更是十分强烈,或惋惜,或愤怒。有人认为,汪顾两律师“各为当事人利益起见,自相攻击而致涉讼,凡在同人已深愧惜,方冀早日和解免自相残”。也有不少律师认为邹玉当庭声称“上海律师甚多败类”,贬低律师人格,纷纷致函上海律师公会,敦促邹玉指出所谓的败类律师,以免混淆视听。赵毓璜等33名律师更是联名致函上海律师公会,认为邹玉律师在法庭上公然毁损全体上海律师的名誉,若不严肃处理,上海律师群体将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为外界所轻视。公函指出,邹玉不仅违背《上海律师公会会则》的第37条规定,而且已构成妨害名誉罪,应依照会则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召集上海律师公会临时总会讨论处理此事,以便维护律师风纪。 8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专门为此召开执监联席会议。会上多数律师认为,邹玉诽谤上海律师为败类,侵害了上海律师公会全体会员的名誉权,应要求邹玉指出所谓“败类”。但汤应嵩委员建议先致函邹玉本人以了解详情,要求其在3日内列出败类律师;若其举措失当,再行决定是否召集会员大会。会议接受了汤应嵩这一建议,于9月1日将联名公函照转邹玉律师。 9月4日,邹玉致函上海律师公会,对联名公函予以答复。邹玉解释道,他在法庭所言既不存在主观故意,也不存在“措辞有所失当”,更不构成“妨害名誉罪”。他说,他在法庭所言是以善意发表言论,是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维持律师风纪考虑;汪承宽与顾永泉二人之中必有一人作伪证,因为上海这种败类律师很多,故以律师公会会员的身份请求审判长将二人送检察处侦查。邹玉还解释道,他所说的“上海律师甚多败类”并非特指,而是上海律师公会曾指出的违法乱纪者。事实上,上海律师公会早有律师败类“很多”“甚多”等类似表述,“最著者如李守法、李嘉泰等已经发觉”,“伪造汉密尔登文凭十三人已经公布”,“不著名”“未发觉”或“未公布”也不在少数,何以只允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再说,“甚多”的表述只是相对的,如果说乞丐身上有十余虱子,不能说“甚多”,但一名律师身上有十余只,一定称得上“甚多”。 针对“法庭为尊严之地,邹玉律师公然毁损上海律师全体名誉”的说法,邹玉辩称,法庭辩论不存在名誉侵权,律师在法庭为维护当事人利益之言论,纵有失当或涉及他人隐私,均不负任何责任。他指出,美国不乏这样的判例,最近美国芝加哥律师公会出版月报即载有这种观点。中国律师章程也有类似规定,如要求律师当庭发言不得涉及案外别情,此外则别无限制,此皆与欧美判例与学说一致,否则不足以尽律师辩护之职。如果律师发言是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尚须承担责任的话,则无人能够幸免。邹玉继而指出,律师之所以臭名远扬,乃是少数败类律师所致,要维护社会对律师的信仰,只有对那些败类严惩不贷,方能维持律师的清誉。汪承宽与顾永泉二人之中,显然有一人当庭作伪证,联名律师不追究此事,反而向邹玉严重交涉,不免使律师行业遭外界轻视。 至于公函所指控的“妨害名誉罪”,邹玉也为自己做了辩护。他指出,按照刑法“妨害名誉罪”的构成要件,一是须被妨害者自己告诉,不可由他人越俎代庖;二是须存在特定的侵权客体。邹玉认为,自己所言“上海律师败类甚多”没有特指的对象,既缺乏侵权客体,又无被妨害者亲自控告,自然难以构成妨害名誉罪。他还称,根据表达习惯,类似的表述随处可见,如“人心险恶”“世道崎岖”“某某奸商私运现金出口”,照此类推,难道还要表述者负责指出谁之人心险恶、谁为奸商? 邹玉还进一步对联名公函的出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律师联名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有人操纵。领衔律师赵毓璜与他素昧平生,日前方在特区法院休息室经人介绍相识。赵毓璜律师对他表示,联名公函系经某律师再三劝解、确保不会由其领衔的条件下才签上姓名的,不料待报纸刊载出来,方知遭受愚弄,便在地方法院休息室贴出声明,以备律师公会追究。邹玉由此推知其他联名律师签名或许也是受人鼓动,律师公会应对此明察,并对始作俑者秉公处理。邹玉在函中提出,希望律师公会在收到复函后3日之内反馈联名律师的答辩意见,并抄示联名律师名单一份。他恳请公会向联名律师转告其尽快消除误会的愿望,希望后者明白事理,不要再浪费时间。 邹玉致上海律师公会的函见诸报端后,9月11日,他再次致函律师公会,解释其言行并无恶意,所谓“律师败类甚多”,系根据1928年11月16日《上海律师公会呈文司法院教育部注意律师资格》一文中所载内容而说的。1930年9月13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执监会议。从相关记载来看,这次会议上没有再对邹玉的言行进行谴责,也未对邹玉的复函提出任何异议。会议最后决定,律师公会致函赵毓璜等联名律师表明态度,并照转邹玉答辩原函。指出若还有不满意之处,请相关律师于公会定期大会期间提议。显然,律师公会希望息事宁人。汤应嵩委员提出,这一名誉纠纷不必与瞿周坟产争夺案捆绑在一起,建议单独和解。联名律师可能也考虑到纠纷再继续下去将给上海律师的整体声誉带来更大损害,故在9月21日召开的律师公会秋季大会上,未再提及与邹玉律师名誉侵权相关的问题。就这样,一场事关上海律师的名誉风波悄无声息地化解了。 三、 “讼师”阴影下的律师形象 其实,上海律师之间的互相攻讦与谩骂决非个案。就在“上海律师败类甚多”的名誉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类似的纠纷仍在发生。1930年9月5日,律师顾惠章在辩护状中称“常闻人言,专营前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之律师大多好货利而昧大义,今益俗而可笑”,对方律师指控其“信口谩骂,有意侮辱”,要求上海律师公会予以严惩。1932年1月,前述案中的当事人之一汪承宽律师在代理遗产案中,突然起身打断对方律师的陈述,手指对方连呼“瞎说”,随后拂袖而去。为此,对方律师指控汪承宽“当庭公然侮辱妨害名誉”,要求上海律师公会“以资惩戒”。律师界的频频内讧,使得外界对律师的印象日益恶化。正如邹玉律师所言,上海律师“败类甚多”只是相对而言,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律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讼师被塑造为令人憎恶的形象,历来为官方所贬低、打压,这种妖魔化的形象根深蒂固。基于“无讼”的儒家理想以及力图减少治理成本的现实考虑,传统社会的官员往往刻意宣扬讼师狡诈与贪婪、逐利的形象,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以此警示民众远离这一“危险”群体。律师同样是从事民间法律服务,其角色与讼师近似,难免遭受同样的诟病。非但普通民众将律师视同讼师,连一些达官贵人、高级知识分子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民初总统袁世凯在力邀律师曹汝霖入阁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律师不是等同于以前的讼师吗?”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为律师是“破坏法律之讼棍”。对基层社会颇有研究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写道:“在乡土社会,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正是基于整个社会弥漫着对律师的成见,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际上均存在以讼师来定位律师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甚至质疑律师制度的正当性,批评律师制度“举国诟病”,“法院受其牵制,人民受其祸害”。其实,“上海律师甚多败类”名誉侵权纠纷中的律师攻讦行为与传统讼师的“狡诈”“贪利”并无二致,而且还暴露出这样的败类律师甚多,也难怪人们将律师与令人憎恶的讼师联系起来。纠纷律师当事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关系个人之人格尚小,关系全体律师人格与律师风纪甚大”。 虽然律师与讼师都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但是现代律师与传统讼师的角色与功能已经判然有别。要言之,在现代政府的体制框架之内,律师被定位为司法过程中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和司法公权力的对抗者,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免受国家司法权力迫害的重要内涵。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律师界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社会之灵魂”,认为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共同构成现代司法不可或缺的三大司法职务,处于同样公益地位,发挥着一样的重要作用,坚决反对将律师视为营利性质的职业。其对自身的职业定位与角色期待,也正是通过服务社会而实现“保障人权”的天职。 不过,律师界试图自我建构的形象与其真实的公众形象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纵观民国时期,律师行业的整体素质仍较为低下,律师队伍鱼龙混杂,乱象丛生,仍处于旧时讼师恶劣形象的阴影笼罩之下。参见尤陈俊《阴影下的正当性——清末民初的律师职业与律师制度》,《法学》2012年第12期。这与这一时期律师职业准入门槛较低有一定关系。1926年,司法部次长石志泉指出:“业律师者,流品太杂,恶草害稼,恶马害群,社会不察,遂疑操是业者悉颠倒黑白、舞弄文法之徒。” 1928年上海律师公会向南京司法部呈文指出,“近二三年来,公会会员骤增三分之二,内有未出国门一步,未入法校一日,向为洋人雇员,甚至工艺人等,徒以金钱购买文凭,朦领律师证书,执行律师职务,改律师身份”。上海是闻名的“十里洋场”,商业繁华,律师行业人数众多,律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以致不择手段、违法乱纪、沆瀣一气的现象层出不穷。《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尖酸地评论道:“现在那些狂吹法螺的大律师,就是过去的贼头贼脑、刀笔害人的老讼棍。时代不同,名称也不同,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更觉变本加厉。过去讼棍欺骗,是藏头露尾,作些偷鸡盗马的勾当。现在律师敲诈,公然明目张胆,有降龙伏虎的神通。”这篇文章固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多少也反映了当时媒体与社会对律师行业的观感。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很多能印证这一看法的具体事例。如在沪上臭名昭著的“强盗律师”范刚,与上海各捕房有密切关系,探目抓到犯人,会竭力向他们推荐范刚作为辩护律师,事成之后范刚会与介绍人“六四分账”。生意非常红火,应接不暇,有时连问明白案情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上庭辩护。范刚这类律师的存在,无疑恶化了公众对律师行业的印象。在本案“连环”纠纷中,律师的诈财、侮辱与诽谤毋庸置疑损害了律师保障人权的公信力。正如涉案律师汪承宽所言,“当事人不谙法律而延聘律师证明以获法律保障,不料虽有律师证明反而多生枝节”。邹玉律师也表明,律师臭名远扬正是这些少数败类律师所致,要维护社会对律师的信仰,只有对败类律师不徇私情,严惩不贷,方能维持律师高尚人格。 律师以助讼为天职,靠帮人解决纠纷赚钱,以赢得诉讼为旨归,整日周旋于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之间,不免经常发生请托、贿赂等情事,也容易导致这一行业内不良风气的滋长。不唯范刚这种品行不端的律师混迹其间,甚至连一些颇有操守、洁身自好的律师也会陷入浮华的名利场中难以自拔。1930年秋,吴经熊的律师行在上海刚开张了一个月,就收入差不多4万两银子。吴经熊自称比“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钱都要多”。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一时期时说,“这段时期从物质上说是最好的,从灵性上说是最坏的”,因为“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每晚都要出去应酬。即使是想起那些日子,也能闻到一股地狱的气息”。 此外,律师职业自身的特点也容易造成人们对这一行业的误解与偏见。首先,律师在诉讼中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角色,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其使命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即使当事人是犯罪嫌疑人,其辩护律师也要尽量为其做无罪辩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正因如此,普通民众往往对律师抱有一种“有奶就是娘”的偏见,似乎毫无良心和正义感,“不管你聘他来处理任何案件,明明你犯的是奸盗淫邪之案子,他都有法给你辩护”。其实,律师是现代诉讼程序中必不可缺的角色,不仅承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功能,还有着帮助普通自然人对抗国家司法权力,使其免受强权压迫的神圣使命。但是,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民众尚无这种觉悟。在民初轰动一时的宋教仁遇刺案中,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应夔丞竟一时无法找到律师。按照现代法律理念,即便“罪大恶极”,犯罪嫌疑人亦应享有辩护权,可以聘请律师代为辩护。而律师为之辩护,亦属保障人权,并不意味着就是为虎作伥。但是普通民众出于一种朴素的道德感,对此通常不能理解。故当杨景斌律师愿意站出来为应夔丞作辩护时,社会名流穆抒斋(穆藕初之兄)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对其予以规劝。有的律师为此感叹:“只可痛的是一般民众,对律师制度没有正确的认识。” 其次,律师提供的服务乃是有偿服务,且收费的数目不低。有学者考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律师的月收入一般在300—2000元之间。而当时上海的五口之家的生活水平是,每月66元为一般,每月100—200元为中等,每月200元以上为中上等。可见,律师行业的收入远远高出社会一般阶层。一些有名望的律师更是开汽车、住洋楼,过着美轮美奂、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虽然一般律师无法与名律师相比,但他们的收入绝对在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其生活质量远非普通阶层所能企及。律师收入的丰厚在受人艳羡的同时,不免也招人嫉恨。在很多普通百姓看来,律师办案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打官司不过是“帮人吵架”而已。在现实中,也的确有一些律师想方设法腐蚀司法人员,上下其手,翻云覆雨,给社会公众造成在诉讼中“有钱就有理,钱越多越灵”的恶劣印象。 再次,自清末法律改革始,西方(尤其是英美法系)的对抗制的庭审模式逐渐被引入中国,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律师各为其主,很容易从相互对抗演变成相互攻讦。在前述律师名誉纠纷中,双方律师正是因为案情事实及证据问题发生争吵,出现了侮辱性言论,继而升级为名誉纠纷。邹玉律师在激愤之中脱口说出“上海律师甚多败类”这样的话,对外界而言,无疑留下了律师行业内部自认黑暗的口实。因此,其他律师对邹玉的言论表达出严重不满,亦在情理之中。律师公会也认为,同业攻讦“影响本人地位事小,动摇社会对律师信仰事大”。如果这类事件“层见叠出”,更会为外界所耻笑,为整个律师行业抹黑。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已渐发达的报刊杂志对律师负面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地说,律师的执业活动需要报刊杂志等媒体的舆论监督,但是媒体为追求新闻效应、增加发行量,对负面新闻有着本能偏好,有时甚至添油加醋、恶意炒作,以致有关“花花律师”“妓女律师”“现代刀笔吏”“蝇律师”等负面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日益型塑并固化了社会公众对律师的印象。反讽的是,当时的一些律师为了给对方施压、引导舆论偏向,往往通过媒体公开相关案情,以致律师在报纸上互相攻讦已成为家常便饭。其中一个较为轰动的律师口水战,是1935年汉口律师公会的正、副会长在报纸上的骂战,彼此攻讦达数月之久,报道长篇累牍,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1930年发生在上海的这起律师名誉侵权风波,也是在沪上各大报纸的竞相报道中愈演愈烈,放大了律师的负面形象。 四、 上海律师公会维护律师形象的努力 晚清民国为了建立律师制度的正当性,避免传统讼师的不利影响,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名称上将律师与讼师进行切割。虽然传统社会对讼师刻意诋毁、打压,但对专门法律服务的需求并未随之减少。近代律师与传统讼师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保障人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公平正义性,而且在于其受国家与律师公会的共同监管。上海律师公会为了维护律师的人权卫士形象与律师制度的公信力,既对贫民实行免费法律援助,也对“犯人”权利保护不遗余力;既对律师的类似讼师欺诈、贪利、唆讼等进行惩戒,也对社会上损害律师形象的行为着力阻止。 但有关律师的负面消息仍然层出不穷,律师公会颇感头疼,疲于应付。作为行业自治机构,律师公会虽承担规范律师职业道德、维护执业纪律的职责,但由于它缺乏必要的行政权威和惩治手段,故其职责难以落到实处。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律师行业的负面形象已经生成。国民党政府实行司法党化,试图加强对司法领域的掌控力,对各地律师公会加强整治。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律师公会也进行了改组,着力改变以前会务废弛的状况。一方面,它努力清除假冒律师,提高律师素质;另一方面将所有上海执业律师纳入监管范围,并加大对违纪失德律师的惩处力度。 在现实中,控辩双方律师之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为了使纠纷不致升级,上海律师公会要求这类纠纷先由律师公会介入调解,“对曲者阻止其不法行为”,而不得直接向法院起诉。在本案律师“连环”名誉侵权纠纷中,因一方律师不听劝阻,执意对簿公堂,结果不仅没有化解纠纷,反而使律师名誉侵权纠纷升级。尤其要指出的是,该连环名誉侵权纠纷“宣诸报章,使社会侧目,丑声四溢”。 鉴于律师的形象不佳与新闻媒体的过分渲染不无关系,律师公会还尽力减少律师负面新闻的发表与传播。一方面,上海律师公会利用社会关系疏通报馆,尽量减少律师负面新闻的报道;另一方面,对报纸媒体的夸大、杜撰等失实报道,设法停止侵害,挽回影响。有时,律师公会直接出面制止,要求以后不再刊载侮辱律师之负面新闻。对那些经过交涉、抗议仍然无果的,律师公会设法请求国家权力机关出面制止,或请法院依法取缔。如《字林西报》不时刊发有关律师的负面新闻,经上海律师公会多次交涉仍不予理睬,最后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出面才得以制止。在法律手段之外,律师公会也会采取其他办法来对付媒体。天津《益世报》曾刊载文章,将律师与妓女相提并论,认为律师“无罪就该杀”,引起了律师界的气愤。上海律师公会积极配合天津律师公会,通过不订阅该报纸、不在该报纸登载广告等手段,迫使该报公开道歉。对贬损律师形象的出版物,律师公会也设法予以阻止。如大连图书供应社出版《现代刀笔》一书,刻画律师丑恶形象,经上海律师公会出面交涉,最终该书社与著作人声明道歉,并删改相关内容,回收出版物。律师公会的成员均为熟悉法律的律师,按理说应该比一般的团体更加明法、守法,但是在打压媒体这件事情上,却有侵犯他者言论自由权利之嫌。这也充分说明,民国时期的律师自治组织尚无足够的权利意识和言论自由意识,为自身的利益不惜侵犯他者的正当权益。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然而,律师公会在肃清纪律、重塑律师形象的过程中,有时也不免投鼠忌器、畏葸不前。1929年4月,上海律师代表吴迈向全国律师协会提出“屏除嗜好”提案,指出“每见多数同人,不惟视赌博为寻常,甚且眈鸦片如性命”。对这样一个本意为端正律师行为、改善律师形象的举动,上海律师公会却认为其言辞有损上海律师的形象,因而指责其“多数同人”好赌、沉迷鸦片的说法没有根据,并取消吴迈的代表资格,撤回提案。吴迈大为不满,指责上海律师公会不愿“自暴其短”,实属讳疾忌医、欲盖弥彰,激愤地指出为“图同业人格之向上”,必须“壮士断腕”“自涤其污”。不过,要做到“壮士断腕”何其艰难?事实上,对很多业内的不良现象,律师公会尽管有所意识,终究无能无力。 五、 结语 近代以降,源于西方的律师制度移植到中国,律师职业也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产生并逐渐壮大。有学者指出,清末法律改革后,官方不再接续明清以来的恶讼师形象,试图塑造律师职业的正当性乃至崇高性,但由于律师职业准入方面的宽滥之弊,民众在律师群体身上看到的仍然是讼师的影子,因此,中国近代律师职业在公众的心目中,正当性非常脆弱。从1930年发生在上海的这起律师名誉纠纷也可看出,某些律师的职业操守的确存在问题,而律师之间的互相攻讦,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上海律师公会虽然竭力调和,并试图改善律师形象,但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最终该案也只是不了了之。客观地说,上海律师公会作为律师行业的自治组织,对上海律师业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甚至对中国近代法制事业不无贡献,但在改善律师形象、型塑律师职业正当性方面,所起作用毕竟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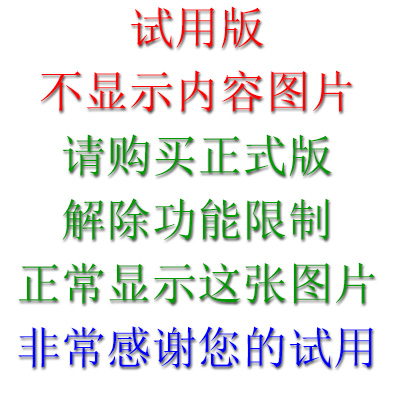 欢迎订阅《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modernchinesehistory 您目前使用的是【试用版】,很多功能受到限制!!如果试用此插件之后满意,对您产生了帮助,请购买正式版支持一下辛苦的开发者,插件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正式版用户的支持,优秀的应用得益于您的捐助,点击下面的链接去Discuz官方应用中心购买正式版永久授权 http://addon.discuz.com/?@csdn123com_weixin.plugin 正式版后续更新升级免费,一次购买,终身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