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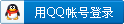  x 近年来人们趋向于把经济技术近代化称为近代化的第一个层次,把政治体制近代化称为近代化的第二个层次,把思想文化近代化称为近代化的第三个层次。据此,我们有理由称洋务运动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领导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是开明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群体。其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已被多方论及,而在中央主持全局的人物奕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不揣翦陋,拟对奕在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他的典型工作意义,他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论述,期望得到专家们的批评指正,以对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宏观研究有所裨益。 一、首倡“自强”与制定近代化纲领 “自强”是一百多年来全中国人民,包括地主阶级有识之士、进步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分子的共同奋斗口号。它提出于19世纪60年代,并成为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中心口号。 这个口号是谁首倡的呢? 美国的费正清教授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说是李鸿章于1862年接任江苏巡抚后首先使用“自强”一词(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版,上册,第466页。)。台湾学者一般对“自强运动”均很重视,但未见明确推定谁是首倡者。我们史学界在70年代以前多是笼统谈洋务和“自强”的,也没有注意首倡问题。80年代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开始注意首倡权问题。该书写道,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七日曾国藩日记中记有“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的《中国近代史》写道:1862年詹事府詹事殷兆镛上疏朝廷,建议实行“自强”政策(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1974年版,上册,第272页。)。以上诸说,皆以1862年首倡自强为是。 实际上,奕提出“自强”主张比曾国藩、李鸿章、殷兆镛等人都早。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会同桂良和文祥提出《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内称,于遭受英法联军重创之后,中国亟应“自图振兴”(《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五册,第340—346页。)。这就提出了“自强”的基本涵义,也可以说是“自强”口号的雏形。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奕等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对前折补充道:“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700页。)据此,把“自强”做为国策而见诸近代文献的大概以此为最早。 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是一次系统的改革工程,它是由中央统一规划,制定纲领,进行发动,朝内外有关大员创造性地实施的;不是由地方各省一哄而起的。以往的史著往往给人当中央衰微之际,地方实力派乘时而起掀起一场近代化的错觉。在当时,中央里能够制定政策并且具有革新意识的人就是奕。奕于英法联军之役亲历亲见落后挨打的严酷现实,这是他能够放弃“天朝上国”及“华夷观”等传统观念而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前提;在他周围又形成了一个与热河咸丰——肃顺集团隐相抗衡的留京王大臣集团,他本人又一跃而成洋务专家并掌握办理涉外事务的大权,这是他能够制定新政策的政治条件。 奕提出了近代化治国纲领,它存在于前述两个文件中,即《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和《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这两个文件相互补充,构成包括外交、内政、军事诸方面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全套大纲。其中,总纲是“自强”,它与“自图振兴”是同义语;总目标是“御侮”,增强中国国力,“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治国步骤是先平内患,后御外侮:“内患除则外侮泯”;“自强”的关键是军事近代化:“必先练兵”;而这一切都要在讲究外交策略的情况下进行,“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 关于“自强”的目的,多年来争论不休。从齐赫文斯基到范文澜都认为在于“镇压人民革命”,而“决无打击外国侵略之意”。近年来我国史学界趋向于认为“自强”的根本目的既在于强化国家镇压人民反抗,也在于增加御侮能力,是所谓双重的。可是,如果我们严格追寻“自强”口号的本来涵义,会认为那的确是在倡导增强国力以御外侮的。第一,这个口号提出的背景不是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掀起之时,而是在被英法联军战败之后,其目的在于筹办“洋务”全局,“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第二,提出这个口号的文件主要针对性是要解决中国的落后虚弱问题,自当是相对外国而言的;第三,从语法范畴上分析,“自强”是针对敌体而发的,因为外国强盛,战败了中国,中国才要自强,要重新称强于世界;对于国内人民来说,清政府不能承认农民起义是平等的敌体,只能污之为“匪”而决心剿灭之。就是说,清政府不能不以全体人民总代表自居,它不能自外于人民而向人民谈“自强”,它只能是针对列强而言的。归根结底,“自强”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列于强国之林以杜列强之侵凌。至于所谓“心腹之患”、“肢体之患”、“肘腋之患”的说法只表明为了谋求健康的体魄而需要疗治的疾患的严重程度,而不表明目的,目的只在于强盛。 那么,为什么说奕所提出的是一套近代化的治国纲领而不是一套复古主义的封建治国纲领呢?因为,第一,这套纲领的基本点是建立在崭新的外交思想上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弃传统的华夷观,决定平等地处理中外关系,自觉地把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作通盘规划,统筹兼顾;二、实施这套纲领的主要手段是推行近代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弃圣经贤传而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术。 咸丰帝虽然将这两个文件交给热河的诸王大臣及军机大臣们审议通过,成为定议,但事实证明,咸丰帝及肃顺等人对此还心怀疑虑。但是不久后发生的辛酉政变使奕大遂其志,后来35年内外的中国历史基本是沿着这套纲领所指引的近代化方向行进的。 我们无论从文献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有理由说第一个近代化纲领的制定者和提出者是奕,咸丰帝是批准者,曾、左、李以及其他洋务大员是实施者。 二、率先革新与积极推进近代化 史学前辈范文澜说:“满洲洋务派处处落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上册,第197页。)这种说法逐渐演为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似乎满族洋务派一定比汉族洋务派有较多的保守性。从满族最大的洋务派奕看,这个结论过于偏颇了。 中国近代化系统工程包括开展外交、编练陆军、筹建海军、兴办教育、建立工业等项目。在这些方面,奕都率先带动或给予推动。现择要胪陈如下: 1.创办第一套近代外交机构。闭关时代原无特定外交机构。清制规定,礼部受理附属国朝贡或敕封事宜;理藩院受理各藩部事宜,连俄国也被视为“北番”,不肯平等待之,归入理藩院管理;至于西洋各国非藩非属,则由两广总督办理,有时为隆重其事特加钦差大臣头衔,1858年后改归两江总督办理,也曾由江苏巡抚加钦差大臣衔办理。以上均非专任职务,也没有常设机关。奕于1861年1月吸收光禄寺少卿焦祐瀛、长芦盐政宽惠等关于设“办理通商处”的建议的合理内核,筹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五册,第228页。),并且抵制了咸丰帝颁予“通商衙门”的关防,坚持着把它办成近代第一个外交总机关和领导各项新政事业的总汇机关(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在总理衙门之外另设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开始时称三口通商大臣)。这项改革是我国外交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对于开展近代化事业产生了重要作用,体现了近代外交意识和近代化精神。过去有人把它斥为“清政府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似乎有欠公允。 2.引进第一批外国武器。中俄北京条约签字次日,奕得到俄国公使馈赠的一支转轮手枪和两只西式步枪,当下,他赞赏不止(A·布列斯盖夫:《1860年〈北京条约〉》,第146页。)。后来他迅速与俄使达成接受大炮50尊、鸟枪10000支的馈赠协议。辛酉政变一个月后,俄国第一批武器计大炮6尊、炸炮500件、鸟枪2000支运到恰克图。后来奕发现俄国企图以武器为诱饵换取在京师一带的开矿设厂权,果断地下令中止索要其余武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961页。)。这事成为一次宝贵教训,此后清政府转向英、美、法等国寻求有偿引进先进武器的途径。 3.奏请并支持创办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1860年11月23日)奕在奏请引进俄国武器并借师助剿折内谈到制造枪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药问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607—2608页。)经廷寄转发给曾国藩后,曾受到启示,复奏中写了前述“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名言(《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669页。)。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奕在总结借师助剿问题的奏折中明确要求曾国藩和薛焕在上海“酌雇夷匠”,“教导制造”洋枪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第2696页。)。奕担任议政王后更加频催南方学造西洋武器。从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到后来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第一批近代军事工厂的创建无一不是得到奕全力推动与支持的。 4.编练第一支近代陆军。1862年初,奕指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拟订一件训练章程。按照章程,将由崇厚在天津挑选存营兵300名,芦团勇500名,由奕在北京火器营、健锐营和圆明园八旗中挑选弁兵126名,作为第一期新兵到天津接受近代化陆军训练。教官聘用英国军官17人,翻译聘用3人,受训士兵按照西方军队编制,以12人为一队,相当于后来陆军的一个战斗班,每天操演2次,科目分枪法(即步兵)和炮法(即炮兵)两种(《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41—444页。)。六月初二日(6月28日),奕向重点省区上海、福建等地推广天津练兵方式,要求仿照办理(《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52—455页。)。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奕总结练兵经验教训,及时提出“练将”,即军官近代化的指示,以防临阵时被外国军官所操纵(《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第456—457页。)。天津练兵场进行的弁兵轮训,为组建京旗神机营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兵源,也为苏、闽、粤等省的陆军提供榜样和经验。后来,淮军近代化成效最著,湘军稍逊一筹。推原论始,奕亲自部署的天津练兵有肇始之功,这一点为许多近代史著作所忽略。 5.购买第一支海军舰队。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61年7月7日),奕奏请购买一支全套的英国小型舰队(《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222—223、7、23—25、159、165页。)。后经英人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得包括3艘中型军舰、4艘小型军舰和1艘运输舰在内的全套舰队及舰上全部用具,1863年驶至中国。随即发生所谓“阿思本舰队事件”。为了抵制英人操纵舰队侵夺海军指挥权的企图,奕又遣散了舰队,并于1863年11月15日宣布解除李泰国在中国的职务(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7页。)。此事经办者如果不是李泰国这样居心叵测的人,中国海军的诞生将提前二十多年,中国在亚洲及世界上的地位将另是一番前景。不过此次遣散舰队虽使中国蒙受了经济损失,毕竟及时地捍卫了国家主权,等于为日后正式建设海军预交了学费。 6.开办第一所近代学校。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1862年7月11日)。奕亲自创办的北京同文馆开学试教,学习外语和国际公法(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七月二十五日(7月21日)他正式具折请办,拟定了六条章程,聘用了外籍教师,规定了不准借机传教等工作纪律(《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222—223、7、23—25、159、165页。)。在北京同文馆带动下,南方又开办了上海同文馆(后称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外国语学校,其中上海同文馆还率先开设自然科学课程。 7.派遣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同治五年(1866)春,奕派遣知县衔总税务司中文文案斌椿率同文馆毕业生游历欧洲十余国,考察各国政教风俗,历时110多天。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身临其境地领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考察团以切身经历向国人证明在中华文化圈以外确实存在着灿烂的西方文明(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272页。)。 8.派遣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同治六年(1867年秋),奕筹划派遣巡回使团事宜(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291页。),至十二月初(1868年1月),聘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为使团首席使臣,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为副使,组成一支约30人的大型使团正式友好访问欧美各订约国(志刚:《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合订本。)。巡回使团的近期目标是为即将到来的“修约”直接向各有关国家阐述清政府的原则立场,远期目标是为日后派遣常驻外国使节作些准备。可以说,这是中国正式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始。 9.掀起第一次教育大辩论。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1月12日),奕奏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即设自然科学专业,令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五贡生员及五品以下京外官年龄在20以上者报考。一个多月后又奏请让翰林院编修、检讨和庶吉士们入馆研习,聘请西方教授任课(《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222—223、7、23—25、159、165页。)。表现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引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大辩论,史称“同文馆之争”。辩论结果,奕所代表的洋务派观点战胜了顽固派,第一次为自然科学在我国教育领域争得堂堂正正的地位,几年内,同文馆陆续开设化学、数学、天文、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第一所综合性近代学府;同时还推动了一系列近代科技专业学校在全国的建立。辩论的深远意义更在于论及自然科学的价值和面向世界的必要性(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6页。),为开展各个领域的近代化事业扫除了理论障碍。 10.组织第一次工业化大辩论。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止制造轮船,理由是,一、“糜费太重”;二、中外“早经议和”,故不必为此猜嫌之举(《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05页。)。奕没有立即表示态度,遵照两宫太后意旨发廷寄给造船基地所在省份疆吏,要求议复(《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06页。)。福建文煜和王凯泰的议复语意含混,既同意停造,又指出停止造船合同须承担经济损失,但老式师船巡逻不如轮船灵捷(《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07页。);而两江总督曾国藩则坚决反对停造。奕没有忙于裁决,他感到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大方向,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讨论。次年二月三十日(1872年4月7日),他由军机处发廷寄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闽抚王凯泰和船政大臣沈葆桢,要求重新议复。但寄谕中倾向性已很明显,实际是暗示他们要起来悍卫工业化生产的(《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08页。)。这时,曾国藩已经去世,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都从不同角度驳斥了停止制造的滥言。最后由奕从总理衙门角度作出总结,强调对于轮船等大机器生产不但要继续进行,而且要求“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则止”,通过这次大辩论,大机器生产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造成了新的观念:爱国就应拥护工业化,反对工业化不是真爱国;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搞工业化建设可以聘用洋人,引进洋机器,但应不准洋人操纵,要自操主权;探索出两条发展途径:一、要拓宽大机器生产领域,除军事工业外,还要举办民用工业,以民用养军工,以“富国”而致“强兵”,二、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方式,在官办之外,还可以“官督商办”或商办(时称“华商雇领”)(《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第119—124页。)。从而,中国近代工业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了。 11.批准第一条电报线的敷设。还在同治八年(1869年)奕就对信息手段近代化问题开始留意(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348页。)。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日本侵台事件为契机,台事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敷设闽台电报,奕当即请旨批准创办,随后又通过总理衙门一再强调要由中国“自办”,防止为外人攘夺,然而因闽省官绅群起反对以及民众损毁电线设施作罢(《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325—331页。)。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试架了天津至北塘炮台间的电报,并正式奏请架设天津至上海间电报,奕再次果断地请以上谕著令“妥速筹办。”(《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336页。)至中法战争前夕,东南沿海沿江各省都接通了电报,抵制了各国将海线牵引上岸的要求。光绪九年(1883年),奕要求李鸿章主持将电报经通州引进北京(《总署奏片》(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海防档》,电线,第四册,第793页。)。从而提高了清政府的中枢行政效率,也使北京官民得以享用19世纪人类最高通讯技术的福祉。 12.奠定第一期海军的基础。海防始终是自强运动的重点。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与后来的法国侵略北越问题又把海防问题提上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奕曾就海防设施,舰队组建,经费筹措,炮舰、巡洋舰、铁甲舰之购买与自造等一系列问题与海疆各省大吏往返咨商,苦心规划。在他被罢斥之前,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为日后正式建立海军衙门并建成庞大的北洋海军缔造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以上十二项只是大端,尚不足以概括奕为倡导近代化所进行的全部工作。 三、从“先觉”渐入“因循” 奕既以倡导近代化为己任,那么,他与同样致力于中国第一次近代化事业的洋务领袖曾、左、李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从前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奕在提出“自强”口号,制定近代化纲领,号召购买并自造枪炮船只以及开展近代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都稍稍先于曾、左、李诸人,因而构成了启发和诱导作用。 不仅如此,奕的思想还有因遥遥领先,先觉潮流,因而未能获得理解支持而不得不退回原处的时候。 例如,1866年处理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一事,奕虽然感觉出威妥玛和赫德的说贴中有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味道,但是认为抵制外国侵略的最好的办法是使中国强盛起来,“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因此,他由总理衙门拟定的处理意见虽未明确说要接受这一劝告,但已在强调借机推进近代化的必要:“该使臣等所论,如中国文治、武备、财用等事之利弊,并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至所论外交各情,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亦系应办之事”;并说即使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的铁路和电报,也难有效抵制,因为在通商口岸会由洋商首先兴办(《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1—13。)。 这是在用近乎外交辞令的策略性语言鼓动借法改革,只是对外国人的建议避免正面称赞而已。基本立场是立足于接受而不是立足于抵拒。他已经看出了世界工业化浪潮的伟力,明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趋势,不再沉醉于封建的田园诗般静谧的自然经济生活,倡言向西方学习搞近代化。 各省督抚大员议复的结果参差不齐。崇厚赞成仿效西法铸币、练兵、造船、制造军火,也赞成对外开放、派遣驻外使节以及外国公使觐见皇帝,但是反对修筑铁路和电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27—29。);李鸿章转呈丁日昌说潮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应予瓦解,但对法人深入内地不能给予方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30—35。);官文赞成对外开放,但对应否举办铁路、电报等近代化工业态度不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42。);刘坤一认为铸币、造船、军火、练兵等事尚可“斟酌仿行”,而铁路、电报则断不可行,更不应向国外派遣使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43—49页。);左宗棠断言英国人的所谓“援助”是为己谋利,否认英国武器先进,竟然说中国广东生产的无壳抬枪比英国来福枪射得更快更远,还将电报斥之为“奇巧”之物而反对之,不过他建议聘请法国人援建造船厂;曾国藩主张谢绝外国人的这一“劝告”。 在这些意见中,崇厚和官文是基本倾向于接受“援助”的,认为不必疑心这些洋人“挟诈怀私”,而应视为“求媚于中国”的友好表现;曾国藩、刘坤一、左宗棠是倾向拒绝的,是逆反心理:彼愈求而我愈应拒,以免堕其奸计。 奕关于迎接工业浪潮以推进近代化的设想没有赢得普遍的理解与支持,只好在人们的意见中筛选最急需也容易通过的方案加以扶植,遂批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指示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辛丑和约》订立以后,慈禧太后亲自接见赫德,重提三十余年前的《局外旁观论》,并深悔那时没有听从劝告,承认“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实了这些建议是多么地健全和有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二,第46—48页。)。这番悔悟又从另一侧面反衬出奕曲高和寡的“先觉”。 同治六年(1867年),奕为拟于八年(1869年)进行的中外“修约”预筹方针。他由军机处廷寄给各省督抚将军的文件中明确指出:绝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修约倒退回闭关的老路去,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但是要求对英国可能提出的请觐、遣使、电报、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通轮船、运盐、挖煤、扩大传教等条件进行讨论,各献既能挽回利权又可避免决裂的两全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24—29页。)。 在这次讨论中,曾国藩明确赞成向外国遣使,引进外国技术并用机器挖掘煤矿(《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1—4页。);李鸿章主张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内引进技术,强调“权自我操”(《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6—16页。);沈葆桢具体地建议聘外国专家购用洋机开挖湖北大军山煤矿,然后全国各地仿行(《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1—7页。);官文反对对外开放;左宗棠也反对进一步开放。似乎可以说曾、李、沈前进了,官文后退一步,左宗棠原地未动。 奕汇总上述意见后,拟定的修约宗旨是“于窒碍最甚者,应行拒绝,其可权宜俯允者,仍与羁縻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1页。),实际倾向保守主权,对近代技术只在能对中国直接有利的最低限度内加以引进。同治八年,当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奕以十分欣慰的心情奏道:新约是平等互利的,中国抵制了洋人欲向中国输入近代技术的诸多要求。实际上奕等人没有划清经济侵略与中外技术合作的界限,“抵制”是以保守中国自然经济为代价的。 奕的自鸣得意表现了思想上退坡,他的思想失去了三年前的光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初),李鸿章进京叩谒同治帝梓宫时,面见奕并“极陈铁路利益”,奕“意亦以为然”,但表示畏难情绪,“谓无人敢主持”,李请其对太后言之,奕复推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致郭嵩焘书》,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上册,第269页。)。在这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面前,奕明知其利国利民,却不敢出面主持,这说明他的改革勇气已被消磨,甚至落在李鸿章之后了。 光绪六年十月(1880年11月),李鸿章的老部下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陛见,奏请建两条铁道。这时慈禧太后生病不朝,政务一委于奕主持。奕开始时径直让直督李鸿章和江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001页。)。不料消息传出,又引起顽固派一片阻挠。这时李鸿章态度坚定,还请朝廷“破除积习而为之”,“决计创办”(《洋务运动》丛刊,第六册,第141—149页。)。但是奕却退缩了,以致顽固派阻挠得逞。 更能表现其思想退坡的是留学问题。奕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处理拣选知县桂文灿条陈时就指出中国有向西方留学的必要性,这在全国是很早的,甚至早于容闳的建议(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同治十年,又是奕审批了曾、李关于派遣赴美幼童留学的奏折,当时他兴奋地称此事为“中华创始之举”。可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他却由于顽固派攻击留美学生“沾染洋习”而命令全部撤回(《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222—223、7、23—25、159、165页。)。这件令中外有识之士视为倒行逆施的决定居然出自最早倡导近代化极力支持留学的奕之手,令人啼笑皆非。而对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是不以为然的。 所有这些,表明奕在执政前期确实是近代化的积极倡导者,他的认识曾经领先于曾、左、李等人,他的许多做法给他们以启示,他对他们的创造性的建议更能“有请必行,不加遥制”;然而当他柄政日久,频遇阻力之后,他确实变得因循保守了,开展近代化的勇气和锐气逐渐消退。 恭亲王奕是晚清封建统治阶级中具有睿见卓识却魄力不足的改革家,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是先知先觉却难以坚持始终的倡导者。但无论如何,他所倡导的“自强”口号,制定的近代化纲领,率先掀起的近代化改革,均不仅对后世发生着深远影响,既对当世的洋务巨子也给予了明显的启迪和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他是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