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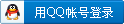  x 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 作者:李细珠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人,翰林出身,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倭仁(1804-1871),字艮斋,号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湖南开封驻防,翰林出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曾国藩与倭仁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主于外,一立于朝,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因此,从曾国藩与倭仁比较考察,可以看到晚清学术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诸多面相。 早年相交于师友之间 曾国藩与倭仁都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交往与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直接相关。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1]就在此时,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写道:“(唐鉴)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2]此后曾国藩与倭仁订交,终生相交于师友之间。 道光末年,曾国藩与倭仁同官京师,过从甚密。此时,他们的交往主要是相互切磋理学。他们共同崇信程朱理学。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3]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4]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5]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6]他们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学问,均成为继唐鉴之后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晚清理学两个路向 有人作了这样的假设:“假如曾国藩不曾出京办团练,一直留在朝中,他能扮演的角色和表现的心态,大概和倭仁不会相差很多。”[7]揆诸史实可知,这个假设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试问:为什么曾国藩能办团练而倭仁不能?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出京而倭仁在朝的缘故。这一点不得不叹服咸丰皇帝的知人之明。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就“用人行政”问题下诏求言,倭仁与曾国藩各上《应诏陈言疏》。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并引程颢之言:“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咸丰皇帝认为“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8]曾国藩则就“用人一端”详加阐述,认为“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皇帝以为“剀切明辩,切中情事”。[9]两相对照,在咸丰皇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不同的。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在召见吴廷栋时,又特地询问了他的看法,吴廷栋认为曾国藩“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倭仁“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体”。[10]吴廷栋真不愧是曾国藩和倭仁的知交,一个“激”字,一个“迂”字,刻画得如此传神,这不能不加深咸丰皇帝心中的初始印象。同年,何桂珍以性命担保举荐重用倭仁,“投以艰巨之任”,咸丰皇帝不为所动,“未从其请”。[11]咸丰四年(1854),京师办团练,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让倭仁“会同办理”,咸丰皇帝谕旨明白地宣称:“倭仁断无干济之才,况此事非伊所长”,终不得其请。[12]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书房,“授惇郡王读”。后来,曾国藩也在私下里评论倭仁有“特立之操”,然“才薄识短”。[13]显然,倭仁只是有学养道德的“君子”,曾国藩才有真正的“干济之才”。倭仁与曾国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虽然都信守程朱理学,但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仁偏于“内圣”修身,曾国藩重于“外王”经世,他们正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路向:理学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理学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14] 讲晚清理学当自唐鉴始。有人说:“鉴之学虽无足称,然亦为开风气者,能于理学衰微不振之时,独树一帜也。”[15]对“鉴之学”如何评价,似还得作具体研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唐鉴开启了晚清理学复兴的新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倡理学的复兴是要“守道救时”。关于“守道”,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编制出一个严密的程朱理学道统传承体系,要“守”的就是这个承接孔孟的程朱理学道统。所谓“救时”,即经世,唐鉴说:“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16]然而,唐鉴本人“守道”有余而“救时”不足。或许可令唐鉴欣慰的是,他的门徒倭仁与曾国藩此后一为“守道”的主将,一为“救时”的重镇;是他们共同高举了理学大旗,使程朱理学一度在咸同时期兴盛起来,蔚然形成一股潮流。 倭仁是理学修身派的代表,有人把他与唐鉴列为“纯粹理学家”,[17]即理学的正统派。所谓正统的程朱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倭仁正是如此。倭仁不仅自己注重道德心性修养,踏实做圣贤工夫,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而且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希望将社会上的人个个造就成儒家“君子”,他所编著的《为学大指》主要是介绍为学做人的方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以倭仁为首的修身派,他们尊崇唐鉴提倡的“守道”宗旨,以程朱理学为唯一的“正学”,排斥其他一切学术流派,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较深;同时,他们以维护程朱理学道统为己任,以为孔孟之道皆经程朱阐发无遗,只按程朱所说的去做,而不求理论上的创新,思想方法较为保守。正如倭仁所说:“孔门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18]这样,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理学修身派会很自然地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曾国藩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曾国藩治学较杂,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但就理学而言,主要的还是宗程朱,对王学稍有排斥。曾国藩未入理学之门前,曾与邵懿辰“谈及理学,邵言刘蕺山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陆清献公、李文贞公、张文端公诸集,最为醇正”。邵懿辰要曾国藩不要看王学殿军刘宗周的书,而郑重地推荐正统的程朱理学家薛瑄、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这对曾国藩理学宗向的取舍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久之后,曾国藩正式向唐鉴问学,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当以《朱子全集》为宗”。[19]从此便打下他的程朱理学的基础。日后他不时地对王学有所异议,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1844年7月28日),“竹如来,与谈吴子序及弟王学之蔽”。同治三年十月廿九日(1864年11月27日),“夜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阅孙奇逢《理学宗传》,认为其“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20]程朱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但也不排斥“经济”。曾国藩作为程朱理学家,大大地发扬了唐鉴提倡的“救时”之旨,他很重视“经济”之学。当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国藩特别问了“经济之学”:“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21]如唐鉴所言,在此之前,儒学内部一般只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22]“经济”被包含在义理之内而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到曾国藩,才把“经济”之学独立出来,将儒学“三门”发展为“孔门四科”。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3]所谓“经济”,即是经世之学。关于经世的内容,曾国藩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24]显然,曾国藩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个体心性道德修养,恐怕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政事。关于经世的方法,曾国藩认为主要是“学礼”,他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25]“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26]有人说,曾国藩这种“以礼经世”的思想是“经世理学之新方向”。[27]无论如何,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经世派,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社会,提倡了一种务实的精神,能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较为积极的回应。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28]因此,在中西文化接触后,他们能部分地或有限度地吸收接纳西学,进而举办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这是理学修身派的倭仁们所不及的。 理学修身派的根本目的是“守道”,其实,理学经世派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守道”。只是前者是为“守道”而“守道”,方法与目的合而为一,因而趋向保守;后者则方法较为灵活,能因时制宜,知权达变,所以显得相对开明。以下将要分析的“同治中兴”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朝内朝外共辅“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本文无意在此作具体的专题研究,只是试图考察曾国藩与倭仁所充当的角色地位,并以此来观察理学如何回应晚清社会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的挑战,从而为理解中国的早期近代化问题提供一点帮助。 据现在所见史料,“同治中兴”一词的最早出现,当是光绪元年(1875年)陈弢所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一书的书名。在该书的《叙》中,陈弢阐述“同治中兴”的含义是指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他说:“穆宗毅皇帝冲龄嗣服,躬遘殷忧,上赖七庙眷佑之灵,入禀两宫思齐之教,卒能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来所罕觏。”但是,书中具体的内容则较为庞杂,不仅有军事方面的,还有吏治、刑典、亩捐、商税、漕运、盐务、水利、文教多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五还编进了恭亲王奕訢奏请增开天文算学馆的奏折《酌议同文馆章程疏》和御史张盛藻的《请同文馆无庸招集正途疏》,表明编者已将“自强新政”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同治中兴”之中,这自然标明了“同治中兴”与历史上的“中兴”的极大不同之处。 “中兴”的本义只是王朝从内乱中复兴,但是,“同治中兴”的背景不仅有内乱,而且有外患。因此,有人把它与唐代的中兴相类比,但是也发现两者其实是不同的:“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29]的确,同治时期,中国早已失却文化上的优势,反而深受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威慑”甚至攻击。在这种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同治中兴”既有“王朝复兴”的本义,又有“自强新政”的新义,从而具有双重含义。 就“王朝复兴”来说,在同治时期的“王朝复兴”过程中,理学修身派与经世派都有积极的作用。首先,以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修身派倡明正学,以维系人心风俗,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同治初年,理学修身派的代表人物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人立朝辅政,时人寄予厚望。方宗诚在给“蒙特旨召起”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罗惇衍上书,希望他与倭仁、李棠阶“共讲明孔孟程朱之学,凡属吏门生进见,皆谆谆劝以读四书五经及宋五子之书以为根本”。[30]曾国藩致函吴廷栋称:“阁下与诸君子穆穆在朝,经纶密勿,挽回气运,仍当自京师始。”[31]倭仁等人“晚遭隆遇”,感恩戴德,竭尽衷诚,不负所望。李棠阶入朝不久,即与倭仁“商酌”,“拟陈时政之要四条:一端出治之本,一振纪纲之实,一安民之要,一平贼之要”,“以期致治戡乱”。[32]吴廷栋在同治三年(1864)平定太平天国时仍然大谈“君心敬慎”问题。他说:“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其疏受到“优诏嘉纳”,并被陈于弘德殿,“以资省览”。[33]倭仁称赞其疏为“陆宣公以来有数文字也”。[34]倭仁为同治帝师,更是努力以“正学”辅导圣德。他将自己所辑《帝王盛轨》与《辅弼嘉谟》进呈,被钦赐名《启心金鉴》,并陈于弘德殿作为同治帝读书的教材。同时,倭仁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他亲立《翰林院条规》,要求翰林们“崇尚正学”。对倭仁在朝的意义,时人以为:“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35]后人评论说:“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36]诚然,以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修身派对“王朝复兴”的主要作用恐怕就是“维持风气”或维系人心。至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是他们武力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回民起义,挽救了垂死的清王朝。因此,从“王朝复兴”的角度看,理学修身派与经世派的目标是一致的,前者主要作用于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层面,后者主要作用于政治军事的实践与操作层面,同治时期的“王朝复兴”正是这种内外作用的结果。关于理学的这种作用,后人有论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37]更有人说:“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国藩)胡(林翼),内推倭(仁)李(棠阶)。”[38]这些论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同治时期“王朝复兴”中理学的重要意义。 就“自强新政”而言,“自强新政”即通常所说的洋务运动,这是在“王朝复兴”过程中兴起的“师夷长技”的具体实践活动,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恢复和维护传统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理学修身派与经世派在“王朝复兴”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在“自强新政”的态度上则互有歧异。其实,也正是这种歧异而显示出理学与近代化关系的复杂性。 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所倡导的“自强新政”,使儒家传统的经世思想在新形势下增添了新内容,具体表现为部分地吸收或有限度地接纳西方文化,主要是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他们之所以有如此较为开放的心态,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客观环境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较大规模地输入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巨大的冲击。面对如此急剧变化的新形势,理学经世派再也不能固守儒家传统的经世方略,不得不因时制宜地增加西学的新内容。就主观条件来说,理学经世派人物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接触,逐渐体验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优越之处,由于他们大都担负着实际的工作,负有具体的责任,因而他们都很务实,能够重视西学的实用价值,并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加以吸收与接纳,以为自强事业服务。可以说,“自强新政”就是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近代科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初步结合的产物。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体现。关于曾国藩认识与吸纳西学的开放心态,这里仅简单地提示两点:首先,曾国藩不仅继承了林则徐、魏源以来“师夷长技”的经世思想,明确地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9]而且将这种思想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如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造火轮船”,[40]在这里诞生了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其次,曾国藩注重培养西学人才,不仅主张立足国内“开馆教习”,而且主张派遣留学生出洋“远适肄业”。这一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客闳“教育计划”的支持。有人说:“曾国藩用容闳,为其新事业最有关系之事,不特在当时与江南制造局,其于西学东来,实辟一途径。”[41]诚然,曾国藩对容闳的支持,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并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确实具有“开新纪元”的意义。可见,从曾国藩有关“自强新政”的主张与实践来看,理学经世派对待西方文化持有较为开放的心态。 理学修身派则不一样,他们虽然也主张“自强”,但是他们所谓“自强”的方法完全没有超出儒家道德论的范畴。倭仁主张改革风俗,他说:“人性皆善,皆可适道,只为无人提倡,汩没了天下多少人才,实为可惜。倘朝廷倡明于上,师儒讲求于下,道德仁义,树之风声,不数年间,人心风俗,必有翕然丕变者。道岂远乎哉?术岂迂乎哉?”[42]显然,倭仁等理学修身派仍然坚信儒学的现世价值。理学修身派向来以理学正统自居,而理学经世派倡导“自强新政”,有限度地吸纳西学,这自然是对理学正统的有力挑战,因而受到倭仁为首的理学修身派的反对。在这方面,倭仁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的反对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笔者没有发现倭仁反对设厂造炮制船的材料,只有一条倭仁反对开矿的材料,他在《答心农弟》中说:“开矿有害无利,何以当道必欲行之?吾弟拼著一官,不为地方留害,所见极是。然具利害是非委婉以陈,亦未必不见听也。”[43]另外,有记载说倭仁反对派留学生出洋,“曾国藩送学生留美,倭仁复阻之,然不送诸生举贡,亦卒如其议”。[44]倭仁是否反对派遣留学生,没有更充分的材料证明。但是,倭仁曾经反对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主要是反对“奉夷为师”,担心“变夏于夷”,而留学生出洋,将在国外生活十几年,这不更是“变夏于夷”吗?倭仁的反对自在情理之中。可见,倭仁出于对儒家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再加上对外部世界的隔膜无知,他对西学东渐持有抗拒的保守心态。正如《清史稿》作者的评论:“惟未达世变,于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45]戊戌时期梁启超鼓吹变法维新时就曾竭力抨击倭仁“误人家国,岂有涯耶!”[46] 总之,就理学与近代化的关系而言,理学经世派所倡导的“自强新政”,对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的拓展,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然而却遭到了理学修身派的反对。这表明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来自理学自身的内在限制是多么严重。 晚年“绝交”说史实辨误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47]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呢?这里有必要略作辨析。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相国倭文端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于冤狱,抗疏论之”。[48]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49]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50]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 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津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51]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52]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53]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54]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征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1]《唐鉴传》,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七,第540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2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3页。[4]《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5]《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43页。[6]《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7]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册,第403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8]倭仁:《应诏陈言疏》,《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1~3页,光绪二十年山东书局重刻本;《清文宗实录》(一),第104页,卷四,道光三十年二月下,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9]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10页;《清文宗实录》(一),第116~117页,卷五,道光三十年三月上。[10]吴廷栋:《召见恭纪》,《拙修集》卷一,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本。[11]何桂珍:《请特用诸臣疏》,《何文贞公遗书》卷一,第1~4页;《倭仁传》,《清史列传》卷四六,第3635页。[12]《清文宗实录》(三),第33页,卷一一八,咸丰四年正月中。[13]《能静居日记摘抄》,汪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93页,附录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14]参见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第27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史先生用“主敬派”指称前者,笔者以为,“主敬”仅是程朱理学的一种修养方法,为了与“经世派”相对而言,似不如用“修身派”为宜。[15]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卷下,第196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16]唐鉴:《学案小识序》,《唐确慎集》卷一,第16页,四部备要本。[17]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卷下,第1963页。[18]《倭文端公遗书》卷四,第21页。[19]《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0、92页。[2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二)、(三),第204、1072、1861页。[21]《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2页。[22]据考证,这种三分法本于北宋理学家程颐,清代学者最先正式提出者为戴震,同时姚鼐与章学诚各有发挥。参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70~2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3]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24]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曾文正公全集》,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25]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6页。[26]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58页。[27]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419页,台湾广文书局1978年版。陆先生在该书第八章“晚清理学”第4节详细阐述了曾国藩的“以礼经世”思想。[28]《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29]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59~4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30]方宗诚:《上罗椒生先生》,《柏堂集外编》卷六,第8页,《柏堂遗书》第四十八册,光绪年间志学堂家藏版。[31]曾国藩:《复吴廷栋》,《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第4141页。[32]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六册,同治六年五月十五、十六、十七日,1915年石印本;《条陈时政之要疏》,《李文清公遗书》卷一,光绪八年刻本。[33]《吴廷栋传》,《清史稿》卷三九一,第11741~11742页。[34]方濬师:《吴侍郎奏疏》,《蕉轩随录续录》,第7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35]此为倭仁同年朱兰(久香)语,见吴廷栋《寄倭艮峰中堂书》,《拙修集》卷九,第36~37页。[36]《清史稿》第11743页,卷三九一,《论》。[37]曾廉:《应诏上封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493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38]《李时灿序》,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一册。[39]曾国藩:《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40]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13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41]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61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42]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六,第13页。[43]倭仁:《答心农弟》,《倭文端公遗书》卷八,第21页。[44]李时灿:《倭仁传》,《中州先哲传》卷七,第23页。另有一则野史笔记材料类似:“初派学生出洋及入同文馆学习,曾文正谓应多派举贡生监,倭文端谓举贡生监岂可使学习此等事,卒如倭议”(《清人逸事·倭文端守旧》,《清朝野史大观》(三),卷七,第108页)。这其中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关于选派留美学生,根据容闳的“教育计划”,只是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西学东渐记》第122页,岳麓书社,1985)。曾国藩等人的奏折称“幼童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稍通中国文理者”(《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第42页)。两者都没有提到“举贡生监”名目。[45]《清史稿》,第11743页,卷三九一,《论》。[4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47]费行简:《倭仁传》,《近代名人小传》,第91页,中国书店1990年版。。[48]芍唐居士:《津事述略》,《防海纪略》卷下,第31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49]倭仁:《叩恳矜全良吏疏》,《倭文端公遗书补》,第12页,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刻本;《倭文端公仁奏疏》,芍唐居士:《防海纪略》卷下,第35~36页。按:王之春(芍唐居士)在《国朝柔远记》一书中节录此疏,却恰恰删掉这段话,很容易引起对此疏的误解。见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31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50]芍唐居士:《防海纪略》卷下《跋》,第39页。[51]《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788页。[52]曾国藩:《唁福纶福裕》,《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474页。按:原编者题为《唁倭福纶倭福裕》,误。倭非姓也,倭仁,乃名,其姓为乌齐格里,故其子不得如是称,但称福纶福裕可也。[53]曾国藩:《复刘坤一》,《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476页。[5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251~25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文章来源:《曾国藩研究》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