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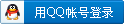  x 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概述 作者:徐松如等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一部分为国内学者所借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的概述。 [英文摘要]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circle,the research for correl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e,locality and peopl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foreign scholars on Western society and Chinese society,a series of relatively mature theoretical modules have been established,some of which have been borrowed by our scholars.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the domestic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is problem have achieved substantial fruit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umerous scholars.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statu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circle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of modern china. [关 键 词]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理论/研究状况/概述 "state,locality,people"/correlation/theories/condition/summary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日益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注重区域史研究与整体史研究相结合,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大量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做一概述。本文中“地方”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为地方政权,一为区域社会。 一、国外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主要理论 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有一部分为国内史学研究者所借鉴。 首先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是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基本通过国家政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控制的不断加强和推进,同时也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反控制也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的整合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在更多领域出现了对立与合作。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内卷化”(involution)的理论被引用到分析国家政权扩张的问题中来。 在考察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基本关系时涉及较多的是“公共领域”问题,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问题。对此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结构性变化的研究影响巨大。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是在西欧社会中伴随着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与资产阶级私人领域与国家的公共权力相区别的。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哈贝马斯的这一概念是有一个历史的范畴来限定的。哈贝马斯提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被看作是“私人身份的人们作为公众聚集一起的领域,他们很快要求拥有自上管辖的公域,用它来反对公共权力自身”(注: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童世骏译,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72页。)。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者很多,例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主张公共领域自成一体,是独立于国家与社会而单独存在的。 黄宗智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内核,结合自己关于长江三角洲(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与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这个第三领域处于国家与地方之间,并且国家与地方都参与到第三领域中来。黄宗智认为第三领域的存在推动了中国的社会整合与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他提出由于中国社会及政权的近代化并没有产生像西欧社会那样的民主进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领域显得格外重要。他所提出的第三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大的不同在于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 在中国市镇网络体系以及晚清以来城市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以对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将中国的地域分为中心地与地区系统两个层面,提出以经济职能作为中心地的基本职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经济职能上的差异而划分了不同的级别,以中心地的级别形成了相应的地区系统。在地区系统中施坚雅提出了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在各个地区系统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核心区域轻于边缘区域(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3页。)。施坚雅认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而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亚文化群(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页。)。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是以这些地区系统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一个个的市场体系为基础,以经济上的中心地为管理与控制的中心,强而有力的控制往往集中于级别较高的地区系统与中心地。而非正式官僚政治与亚文化群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则通过级别由低到高为顺序的地区系统向上渗透与扩散,其最终也集中到各个中心地。 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研究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萧凤霞(Helen Siu)(注:Helen,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89.)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杜赞奇在对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理论模式。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指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等级组织”(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杜赞奇所定义的“文化网络”包括了几乎中国乡村中所有的组织,也就是说包括了所有的资源。那么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社会想要在公共目标上或在个别利益上取得合法性的权威,就都必须通过文化网络来实现。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国家与地方包括民众在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 在国外社会学研究中,马克斯·韦伯享有较高的地位。韦伯关于中国有其独到见解。韦伯认为中国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独立的市民社会,而过分依赖祖籍渊源以及亲属关系。他提出儒教承担了调节与平衡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大部分职能,从而维持了社会运作的正常秩序(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地方社会中儒教是由士大夫与士绅控制的。有些学者如玛丽·兰钦(Mary B.Rankin)把士绅看作是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动阶层(注:玛丽·兰钦:《早期的中国革命党人,上海与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魏裴德(Frederic.Wakeman. J r)、孔飞力(Philip A.Kuhn)(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学者也从近代士绅权力的扩张考察了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注:转引自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页。)。 国外有关于中国近代国家、社会、民众互动关系的理论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英国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注: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贡献较大的有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注:Stephan,Feuchtwang,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1978;Arthur,Wolfed,The Imperial Metaphor  opular Religion in china.1992.)、桑格瑞(StevenSangren)(注:Steven,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Chinese Comunity,1987.)等。 opular Religion in china.1992.)、桑格瑞(StevenSangren)(注:Steven,Sangren,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Chinese Comunity,1987.)等。二、国内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研究的主要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在众多史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便对国内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几个具体领域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1.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目前国内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大多借鉴了哈贝马斯、黄宗智等有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论,但在运用这些理论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形成了研究近代市民社会问题的两大派别:一是以萧功秦、夏唯中等人为代表的“思辩派”;二是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的“实证派”。 “思辩派”主要在文化领域考察市民社会,如萧功秦认为国家政权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注:萧功秦:《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三重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夏唯中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中央高度集权为基础的大一统,始终是构建市民社会的强大障碍(注: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4期。)。 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的“实证派”主要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商会实证研究,并进而提出自己的中国近世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模式。他们提出了“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一说,并探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中,马敏、朱英指出弄清楚近代商会组织的实际运行情况,尤其是商会与行会组织和其他新式社团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们通过对晚清苏州商会的研究,认为晚清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话,可以将此在野城市权力网络称之为“公民社会”(或许称为“民间社会”更为恰当)的雏形,其背后的推动者,则正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注: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马敏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与西方相异,因为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中国早期市民社会建成的初衷,并不是与专制国家权力相对抗,而是谐调民间与官方的关系,以民治来辅助官治。晚清市民社会雏形与封建国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矛盾、摩擦的复杂关系,其中,依赖的一面又占据着主导地位(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朱英在《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推行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政改革。它的实施需要民间社会的参与,清政府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市民社会的运作,而市民社会雏形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对国家的特殊依赖性,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着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对国家也不仅仅只有正面的积极回应,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发挥了制衡国家的作用,如在对待清朝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加征税收的问题上,商会除了调停外也会领导商人予以抵制,使清政府加征税收的计划不能付诸实行(注: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无论是“思辩派”,还是“实证派”都认为中国近世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此外,虞和平提出“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解释框架,他认为,中国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实际关系,主要是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但张东刚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单纯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处于从属地位,而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正式权力之外的自发组织(注: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士绅阶层 一些学者通过对士绅阶层的研究,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仲礼认为绅士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既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注: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王笛则引入了“公共领域”概念,认为地方士绅充分利用了国家对发展公共领域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力,但双方的冲突依然存在(注: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郝秉健通过对清代绅权产生原因的探讨,认为主要是因为明清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绅士提供了空间,同时也是乡里社会所需。绅权的建立将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同时也在官民之间建立一个“缓冲”(注:郝秉健:《试论绅权》,《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高钟则从系统论角度探讨士绅在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注:高钟:《文化激荡中的政府导向与社会裂变:1853-1911年的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先明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绅士的权势本质上是对皇权的分割。绅士对于地方社会的权势影响,总体上是皇权的延伸或变形,是权力系统以外的社会控制力量。虽然皇权必须借助于绅权阶层的社会力量才能完成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以保障“以一人治万人”的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却始终高扬着唯一的“皇权”旗帜(注:王先明:《论“民权”即“绅权”——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的一个侧影》,《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6期。)。马学强则通过对地方政务、赋役财税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认为乡绅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既有合作的一面,亦有冲突的一面(注:马学强:《乡绅与明清上海社会》,《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赵世瑜还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地方士绅在协调国家与地方关系上所起的作用(注: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徐茂明在其博士论文《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中,通过长、中、短时段的结合,从“文化权力”的视角,探讨了在传统社会中江南士绅文化权力获得的渠道,以及其在维护文化秩序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注: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历史系,2001年。)。 3.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 国内一部分学者对国家权力扩张问题做出了回应,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扩张和渗透;一为地方社会的反控制乃至地方自治。 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控制总是不断的加强。部分学者运用人类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广泛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国家颁布的一些制度来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向地方社会进行扩张和渗透。王先明认为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折(注:王先明:《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张研也谈到了清朝统治者用强化保甲制度的办法加强其在社会的统治,造成了国家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赖”的局面,她认为保甲除了具有维护封建治安的主要职能外,还有代里甲督催钱粮赋税的职能,并且还参与基层司法等地方上其他事务的管理(注:张研:《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郑振满通过考察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认为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明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趋于萎缩,因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促成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注:郑振满:《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刘志伟则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地区的实行情况,探讨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注: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谢俊美通过对捐纳制度的研究,认为捐纳制度的开办造成吏治的严重败坏。吏治的败坏引起了下层民众的不满,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注:谢俊美:《捐纳制度与晚清吏治的腐败》,《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4期。)。 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研究了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行、实施情况。他运用了大量法律社会学的理论,认为黄宗智基于“清代民事法律”研究而提出的“第三领域”并不存在。他认为黄宗智套用的西方概念,夸大了民间调解与衙门判决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既然并没有截然对立的二元,第三领域就不存在。他还在文中重点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此作为切入口来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和谐统一,又存在矛盾冲突(注: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反控制也在不断扩大。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的是地方自治。高旺通过对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地方自治是民间力量与政府权力互动的结果。地方自治就是地方分中央之权,中央放弃部分权力而由地方独立行使,而清末新式绅商通过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权力,社会影响力大大增强,又形成了对政府权威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注:高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刘小林等谈到了地方自治的影响,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思潮是参政意识的产物。人们可以通过地方自治锻炼政治能力,进而能通过自治来治理国家(注:刘小林,梁景和:《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学术论坛》1998年第2期。)。马小泉则认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是封建统治者挽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一项自救措施。清政府的目的并非为了赋予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而是为了调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新的绅商“辅治”地位,以官办自治的形式达到稳固专制政权基础的目的。这样地方自治不仅应以辅佐官治为指归,而且要受政府的严格监督和控制,地方官员不仅可以随时检查监督其活动,甚至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撤消自治职员之权,这就决定了清末地方自治难以摆脱官治羁绊,也就难以实现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地方自治(注: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梁景和还对自治机构、自治研究所、自治范围、选举、自治功绩等方面进行探索,认为地方自治运动既得到政府的支持,又受到政府的控制,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在政府的框定下进行(注:梁景和:《清廷督导下的地方自治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运动促进了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注:余子明:《清末地方自治与城市近代化》,《人文杂志》1998年第3期。)。 4.民间信仰和传说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十分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学术方法,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出现了学科联合、课题整合等趋势。如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研究者如王斯福、桑格瑞等人的理论从民间信仰和传说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像陈春声对樟林地区三山国王的系列研究、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北帝信仰的研究等,他们研究的区域是华南这一“边陲社会”,主要通过对这一地区的一些神明的研究,探讨中国传统国家通过何种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向地处边陲地带的基层社会渗透(注: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如陈春声的《三山国王信仰与清代粤人迁台——以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心》一文指出,与三山国王有关的庙宇已成为跨村社的地域联盟的标志,发挥着极强的社会功能,而地方政府也默认和利用其社会功能,又扩大了其影响,反映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注: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清代粤人迁台——以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心》,《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赵世瑜则通过对明清北京“顶”和东岳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在不同的地方,通过民间信仰表现出来的国家——民间社会关系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在京师,民间社会利用了国家,国家也利用了民间社会。他认为民众社会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自己的壮大,国家能够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民众社会,只不过表现出来的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温和的互动而已(注: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6期。)。此外,一些学者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将文献文本与口述文本进行比较,然后将其情境化,从而用新的话语系统来解释民间传说的文化意义,这样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到对它的文化理解。如刘志伟的《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一文,阐述了当岭南文化逐渐归化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体系时,作为正统文化向地方社会渗透的教化手段之一——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即广州地区流行的“姑嫂坟”及其传说,是如何具体展示这一历史和文化的全过程的(注: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宗族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以宗族社会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唐力行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文以徽州方氏为个案研究,深入考察了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周期性的治乱兴衰、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传统社会转型。而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徽州引起回响。徽州与其他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应”,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注: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陈柯云也将目光投向徽州的宗族社会,探讨了宗族社会与封建国家在乡村事务管理上的关系。她通过对宗族在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及其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宗族统治与封建政权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使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补、自我完善的机制。宗族统治,比较单纯封建政权的统治更细密、更有效,而且乡人在思想感情上更易于接受。宗族有效有力地控制了某些地区的乡村,成为那里实际上的管理者和统治者,维护了封建秩序,使封建社会的基础更加强固(注: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英国学者科大卫与刘志伟考察了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的渠道,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推广,以及地方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他们认为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注: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有学者将视线转移到了近代宗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林济指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宗族社会的变迁呈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势:一方面,宗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趋新性变化,宗族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良;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固有矛盾推动宗族社会陷入衰败崩溃之中。这两种旋律交相变化,最终导致以革命方式完成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与此同时,宗族社会也同样对近代国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反作用(注:林济:《论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光明日报》1996年1月9日。)。 6.民间社团 近年来,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将民间社团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考察国家、地方、民众互动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商会研究之外,这里仅以会馆、公所为例,略作介绍。 王日根在他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通过对会馆的研究,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对会馆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及国家与会馆的关系的讨论上。作者认为明清会馆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对地方公共建设的捐助和支持上。他认为此时的会馆实际上在执行部分的“市政”管理权。到清末民初,会馆活动已和地方自治运动融为一体。同时,作者也专门探讨了会馆与政府的关系,并更为深入地指出会馆还是明清政府与重要新型社会成分建立互动关系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注: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忠民在《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一文中以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为研究对象,用了相当的笔墨探讨了其与地方政府乃至清政府的关系。作者认为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与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傍的关系,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随着清政府管理危机的加深而与日俱增,不断扩大。到清王朝最后10年的20世纪初,上海会馆公所的头面人物已成为地方自治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而地方自治机构在地方事务中所起的具体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注: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 以上我们对国内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状况做了简略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于扩大,思考有待于深化。我们在借鉴西方的理论进行本土研究的时候,应注意发展和形成自己的理论模式。 作者:徐松如(1978-),潘同(1979-),徐宁(1978-),均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转发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6期 补充说明:由于在写作过程中的疏忽,本文遗漏了一个出处,即关于国内目前研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是以萧功秦、夏唯中等人为代表的“思辨派”;二是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的“实证派”。”(系转引于张志东先生:《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因此,特借助近代中国网站做一补充说明,并向张志东先生表示万分的歉意! 本文作者:徐松如 潘同 徐宁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