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裘錫圭先生曾提醒“在大家把目光投注於新發現的時候… 我們不要冷落了舊發現。”[1] 事實上,每一次新發現都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新的視角,讓他們重新檢查舊資料,在其中獲得新的了解。本文試圖根據最近公佈的北大漢簡資料,回顧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第四次中亞考察中所獲的尼雅遺址漢簡,指出他1931年在尼雅發現的#N.XIV.20屬於《蒼頡篇》。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王樾先生在《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一文中首先指出在尼雅精絕故址發掘有《蒼頡篇》漢簡。[2] 1993年秋天,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進行尼雅故址的調查和發掘,當時有隨行工作人員採集到這枚漢簡。[3] 王先生目睹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原簡(他暫編為#N14:1),提供了以下釋文:[4] 谿谷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涣囗 #N14:1的內容與北大#4、阜陽#C008、英圖#3010、#3040、#3043、#3225、#3681、#3683等都符合,可斷定為《蒼頡篇》屬簡無疑。[5] 幾十年前,斯坦因也曾進入尼雅故址進行考古調查,多次獲得漢文簡牘。[6] 第四次中亞考察之中,因為中國各級政府不允許斯坦因個人進行正式發掘,他於1931年1月17到24日之間派遣隨行人員偷偷調查幾個尼雅故址地點,採集了一批文物,其中一共有二十六枚漢簡。[7]離開中國之前,斯坦因把這批漢簡拍了照; 實物移交給新疆地方政府之後,這批文物失蹤,去向不明。雖然斯坦因從未公佈他第四次中亞考察的資料,可是由於王冀青先生的努力,斯坦因拍的漢簡照片終於面世。[8] 關於其中的#N.XIV.20號漢簡,王先生在《斯坦因第四次中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中提供了初步釋文:[9] 林梅村先生在《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中採用了這個釋文。[10] 稍後,藉由整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未刊漢簡的工作,胡平生、汪濤等先生對#N.XIV.20重新作了釋文,先後發表在《中國簡牘集成》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11] 遺憾的是,解讀考釋這些文字非常困難。這枚簡不完整,右邊殘損尤其嚴重,幾乎所有的字右部都有缺失,少數字基本全部磨滅。因為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獲的漢簡現已失蹤,學者們無法參考實物。他所拍的照片質量值得稱讚,但是還不夠理想。而且,斯坦因因為覺得這些照片不夠清晰,曾經請求他人製作了一套“改進”的玻璃底版,以加重字跡的筆畫,結果混淆了木簡上的字跡。筆者認為已發表的#N.XIV.20照片很可能來自原始底片,但目前還不能確定。[12]關於現存的底片,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材料(尤其是玻璃底版)小而易碎,不便經常拿起來看,所以研究者難以親眼仔細觀察。由於上述原因,胡平生先生對#N.XIV.20所作釋文慎而闕疑,這種態度是很可取的。 儘管有這些困難,筆者認為#N.XIV.20上的文字與北京大學藏《蒼頡篇》#PKU40號內容明顯相當[13](而與阜陽雙古堆《蒼頡篇》#C043內容也有部分重疊)。[14]參考北大《蒼頡篇》對應位置的內容,有助於進一步確定#N.XIV.20上的文字。現將胡先生所作#N.XIV.20釋文跟朱鳳瀚先生所作北大#40釋文中的對應內容列舉如下(前後重疊外內容省略): 尼雅#N.XIV.20: 北大#40: …䡞䡩解姎婞點媿 下面比較這兩枚漢簡的文字圖片, #N.XIV.20圖片在前、北大#40圖片在後:[15] 字1: 轝 à 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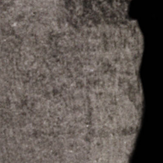  字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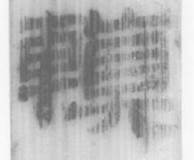 字3: 解 à 解   字4:   字5:   字6: 奴(?)à 點   字7: 婢(?)à 媿   由於#N.XIV.20右邊受損,簡上文字右部大多都不完整,但是還保留著部分筆畫,尤其是第2、3、4、5、7等字。這些殘留筆畫與北大#40文字的右半基本一致。#N.XIV.20第1號字,即胡先生疑為“轝”的字,下部的“車”可識別,上部有兩個相反對角線筆畫,雖然其他筆畫模糊,但依稀能夠看出來與北大#40“䡞”相符。第6字,胡先生疑為“奴(?)”,在筆者看來,其右部跟北大#40同位置“點”的右部“占”一樣。#N.XIV.20的第5字,右邊字跡比較模糊,難以辨認。只有第4字右部不同,雖然類似北大#40對應的“姎”字,但是右邊上部多了一橫;因為北大#40姎字的“央”旁也不規則,這處還待考。 根據上面#N.XIV.20 和北大#40的比較,筆者初步斷定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獲的#N.XIV.20為尼雅精絕遺址中所出的另外一枚《蒼頡篇》漢簡,釋文為:“䡞䡩解姎婞 (1)《蒼頡篇》有韻可尋,按照北大#40對應的內容,#N.XIV.20文字應該屬於《蒼頡篇》支韻部某章,同時,王樾先生以前釋讀的#N14:1文字,按照北大#4所對應的內容,屬於《蒼頡篇》之職合韻部某章,說明在漢代精絕王國中至少有兩章《蒼頡篇》內容。就書法而言,王冀青先生說#N.XIV.20“為漢隸,筆畫精細工整”;[16] 王樾先生說#N14:1也“為典型之漢隸…書法精妙,功力不同凡俗”。[17] 因為這兩枚簡的文字沒有互相對應的部件,而且樣本數量不夠,因此不能確定#N.XIV.20和#N14:1出自同一個寫手,但是從書法、筆法等角度來看,這兩枚本來歸屬同一個簡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假設與出土地點的細節有關,下面會進一步討論。此外,筆者也想指出,#N14:1第一個“谿”字前有空白,就是木簡的開頭;雖然#N.XIV.20木簡“媿”字後斷裂,可是在筆者看來這裏也有較大空白,是木簡的下端。這兩枚簡上的章句佈局與北大#4和#40一樣,既然如此,容易設想尼雅《蒼頡篇》版本與北大《蒼頡篇》版本的原有面貌和內容相似。這一點有待進一步考慮。[18] (2)王樾先生所討論的#N14:1一枚並不是科學考古出土的,其具體採集地點不明。王炳華先生在《精絕春秋》中說:“木簡出土在尼雅第14號遺址內,為考古隊隨行工作人員採獲。採獲者不識簡文的重要價值,事後也說不清楚見于遺址內的準確部位…。”[19] 根據林梅村先生的了解,#N14:1是林永健等隊員在尼雅佛塔西北大約7-8公里的房址東牆外側一個馬槽底部發現的,經王炳華先生再次核實這個地點,確認即斯坦因所稱的N.XIV遺址附近。[20] 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編《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對這枚漢簡的出土地點沒有加以說明,[21] 不過後來公布的《1988-1997年度民豐縣尼雅遺址考古調查簡報》反而聲稱這枚簡是在93A10遺址內發現的,即斯坦因N.XIII遺址,而不是N.XIV遺址。[22] 斯坦因《塞林底亞》提供的N.XIII繪圖的確記錄所謂v房屋內存有“木槽”遺跡,不知道與林永健等先生所說的“馬槽”有沒有關係。[23] N.XIII遺址離N.XIV遺址不遠,位於其東北大概0.5公里左右。同時,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說明N.XIV遺址iii故址木板圍場中有多層麥草等馬秣和馬糞, 他推定為古代馬廄,因此N.XIV遺址的性質也跟林先生所記得的採集地點相合。[24] 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獲的#N.XIV.20也不是科學考古出土的,其採集地點同樣地不確定。因為斯坦因個人未獲准親身進行調查,他派遣隨行人員替他偷偷發掘。王冀青先生仔細閱讀了斯坦因的田野工作筆記等材料,摘錄漢簡發現的記錄,得出的結論是#N.XIV.20這枚簡很可能是被阿布杜爾·賈法爾先生(Abdul Ghafar)在“(N.XIV.)ii號居室牆壁相連的垃圾堆中”採集的。[25] T.O.37照片中在這枚簡旁邊附加了“N.XIV.20”標籤,表明斯坦因認為這枚簡是在N14遺址附近被發掘的。斯坦因有細緻的記錄,但是依靠他的筆記有危險,因為這是斯坦因錄下的他人報告,而不是他科學發掘中親身經歷的第一手記載。再者,王先生也提出斯坦因筆記與照片中的標籤有些矛盾,提醒我們斯坦因會出錯。因此#N.XIV.20到底從何地採集,現在無從知曉。 雖然#N.XIV.20和#N14:1的發掘地點詳情不明,但是斷定#N.XIV.20為《蒼頡篇》內容並確立#N.XIV.20和#N14:1的關係後,主張這兩枚都從N14遺址附近採集,似乎更可接受。 (3)斷定#N.XIV.20為《蒼頡篇》中的“䡞䡩解姎婞點媿”,對於北大從文物市場購藏的《蒼頡篇》漢簡的真實性也提供了旁證。1931年11月21日英國駐喀仕總領事斐慈默先生(Nicholas Fitzmaurice)把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收集的文物移交給喀仕行政長官馬紹武先生以後,#N.XIV.20漢簡實物一直不知所蹤。斯坦因所拍的照片,之前的幾十年裏也被學者們忽視了,而且就筆者見聞所及,到目前為止,還沒人提出過#N.XIV.20內容跟《蒼頡篇》有關。除了阜陽雙古堆#C043上的“ (4)王樾先生先前提出,“尼雅精絕故址出土的《蒼頡篇》…說明:在統一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後,兩漢王朝曾努力在各有關城邦小國內推行漢語文化教育,以利于王朝政令的貫徹實施。”[28] 因為#N14:1漢簡採集情況不明,《蒼頡篇》在尼雅的存在易受一定程度上的懷疑;雖然#N.XIV.20的採集情況也不理想,但是這枚同樣是出自尼雅的《蒼頡篇》漢簡,進一步加強了王先生的結論。大部分的《蒼頡篇》課本、習字等殘簡都在邊緣地區發掘了,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這一現象很可能反映了漢朝派遣所謂“譯長”去邊疆進行翻譯、教育、外交等活動的政策。[29] 後記:黃傑先生費心改寫小文,筆者非常感謝黃傑兄的指正。筆者也很感激陳偉先生、陳侃理先生提供的幫助。 [1] 裘錫圭《談談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漢簡》,汪濤、胡平生、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57頁。 [2] 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55-8頁。王先生介紹了兩枚簡(他編為#N14:1和#N14:2),但是第二枚簡文字太模糊,沒法解釋,所以這裏不討論。第一枚#N14:1折斷,兩段能夠綴合,而且簡背存有三個字的筆跡, 王先生釋為“人仝人”。 [3] 關於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的調查,請參看: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学術考察隊、日中共同ニヤ遺跡學術調查隊《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佛教大學尼雅遺跡學術研究機構、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1996、1999年;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1988-1997年度民豐縣尼雅遺址考古調查簡報》,《新疆文物》2014年第3-4期,第3-183頁。關於這枚漢簡的發現,除王先生的文章以外,請參看:林梅村《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兼論懸泉漢簡中的相關史料》,《中國學術》2001年第2輯,第243-244頁和第14腳註;王炳華《精絕春秋:尼雅考古大發現》,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91-92頁。 [4] 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第55頁。#N14:1的圖片,請參看:林永健、李希光、孫躍新等編《夢幻尼雅》,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9頁;王炳華《精絕春秋》,第91頁;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小学書・童蒙書の諸相》,汲古書院,2006年,第57頁。 [5]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1頁;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第25頁;汪濤、胡平生、吳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33-49頁。 [6] Sir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Clarendon Press, 1907年,第1冊,第316-416頁;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larendonPress, 1921年,第1冊,第211-269頁;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Indian Government, Clarendon Press, 1928年,第1冊,第140-155頁(這次考察中在尼雅沒有發現漢簡);王冀青《奧萊爾·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亞細亞考察》,《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1期,第98-110頁;《中英關於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物的交涉內幕》,《現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42-257頁;《關於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發現的文物》,《九州學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第131-147頁(筆者未查到原文);《斯坦因第四次中國考古日記考釋 :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旅行日記手稿整理研究報告》,甘肅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十部分“在尼雅遺址考察”,第351-373頁;Shareen Brysac,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American Expedition,” Proceedingsof the British Museum Study Day 23 March 2002,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Paper Number 142, British Museum, 2004年,第17-22頁 (/uploads/collect/201810/19/Stein Brysac2915.pdf);Helen Wang,“Archives relating to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Expedition to Central Asia(1930-31),”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British MuseumResearch Publication Number 184, British Museum, 2012年,第1-5頁(/uploads/collect/201810/19/17-Wang pp2915.pdf)。 [7] 斯坦因1931年5月3日至4日撰寫的《奧萊爾·斯坦因爵士自和闐至婼羌旅行期間所獲古物目錄》內記錄“書寫有漢字的木簡(除1件外皆為斷殘)… 27支,”可是照片上只有26枚,少了一枚,王冀青先生認為斯坦因在寫目錄時可能錯數,請參看: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8、274-275頁。 [8] 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British Library Board, 1998年, (/uploads/collect/201810/19/article32918.pdf);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1998年,第259-290頁;John Falconer, “The Photographs from Stein’s Fourth Expedition: AFootnote,” The 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British LibraryBoard, 1998年, (/uploads/collect/201810/19/article42928.pdf);胡平生、汪濤《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簡牘》,《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第150頁。高度清晰度照片已經在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公佈了(http://idp.bl.uk/ ),可用關鍵詞“T.O.37(C)”檢得。 [9]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第267頁。韓厚明《新疆出土漢晉簡牘集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第312頁也討論了這枚簡的釋文。 [10] 林梅村《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第248頁。 [11]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二十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四川省、北京市),第2362頁;胡平生、汪濤《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簡牘》,《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第148頁。 [12] 英國國家圖書館不但保存著斯坦因第四次考察的“改進”玻璃底版,也有原始硝酸鹽底片一張和從原始硝酸鹽底版複製的副本底片全套,請參看:John Falconer,“The Photographs from Stein’s Fourth Expedition: A Footnote,” 第75-76頁。 [1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第107-108頁。 [14]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第27、30頁。 [15] #N.XIV.20照片見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http://idp.bl.uk/ ),輸入關鍵詞 “T.O.37(C)”即可查到;北大#40圖片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第50頁。 [16]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第267-268、285頁。 [17] 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第56頁。 [18] 關於編繩痕跡, #N14:1開頭“谿”字之前好像沒有明顯的編繩痕跡, 而且“險”字處可能受到摩損。不過“緩”字與“肆”字之間折斷,可綴合,簡上編聯處在較大壓力下較容易斷折,而且北大#4在“緩”字與“肆”字之間對應位置有編繩痕跡。可惜現有#N14:1照片清晰度不理想,是否曾經編聯在簡冊中還待考。 [19] 王炳華《精絕春秋》,第91頁。 [20] 林梅村《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第243-244頁。 [21] 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学術考查隊、日中共同ニヤ遺跡學術調查隊《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中,王炳華在第2卷第123頁引用了《夢幻尼雅》,此外,據筆者所知,沒有其他具體討論。 [22] 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1988-1997年度民豐縣尼雅遺址考古調查簡報》,第6-8、14-15頁。 [23] Aurel Stein, Serindia, 第3冊,10圖“Plan of RuinedHouse N.XIII, Niya Site.” [24] Aurel Stein, Serindia, 第1册,第218頁。 [25]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第273、275頁。 [26]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第30頁第35號注釋提出這個字“疑當‘䡞’”。 [27] Christopher J. Foster, “Introduction to the Peking University HanBamboo Strips: On the Authentication and Study of Purchased Manuscripts,” EarlyChina, 2017年,第40冊,第215頁。 [28] 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第58頁。 [29] 王樾《略說尼雅發現的“蒼頡篇”漢簡》,第58頁。關於邊遠地區中的《蒼頡篇》發現,請注意最近在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出土《蒼頡篇》漢簡的報道:http://kaogu.cssn.cn/zwb/xccz/201809/t20180920_4564184.shtml。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18年10月18日19:50。)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