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岩波書店,2013年,2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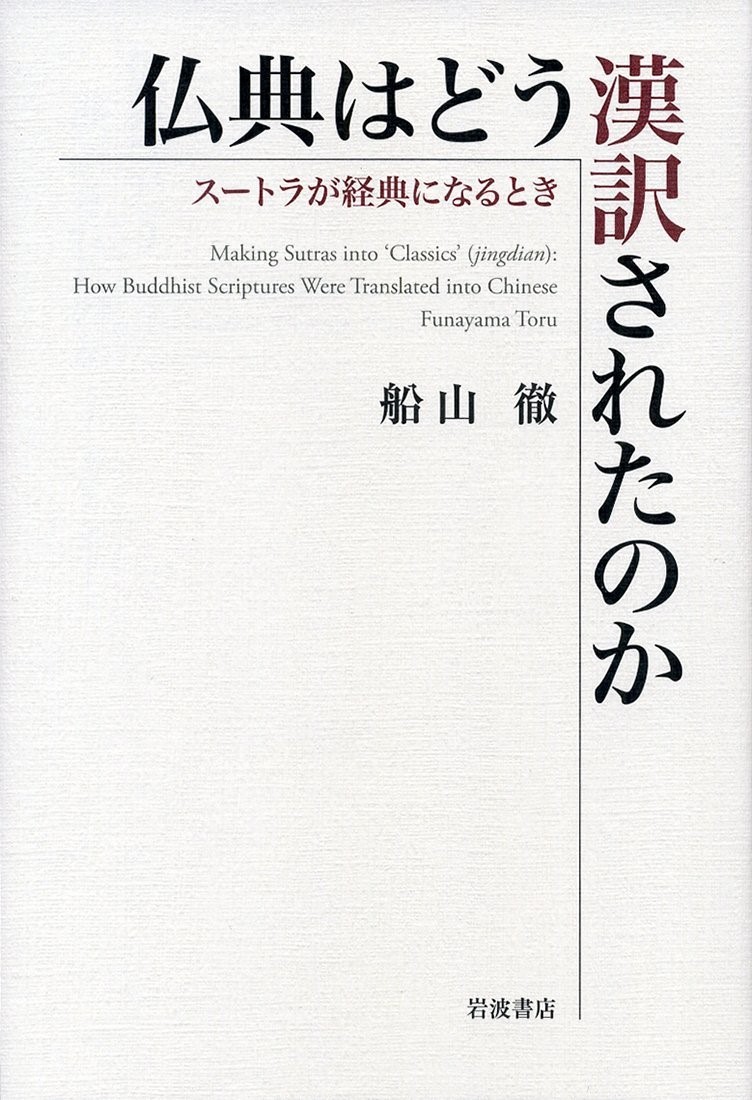 本书是有关佛典汉译史的通论性专著,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船山徹教授撰写。船山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是当今国际佛教学界少数几位“有能力同时从事印度与汉传佛教研究的学者”之一[①]。在印度佛学领域,他主要关注8世纪以后的佛教认识论和论理学,特别是给与西藏佛教很大影响的莲花戒(Kamalaśīla)的思想;在汉传佛教领域,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5-6世纪,从王朝史的划分来说,大致相当于南朝时期,而从翻译史的角度看,则大致是鸠摩罗什来华以后,到玄奘登场之前。这一时期伴随着印度僧人来华,以及汉地僧人西行求法,中印的典籍、文化交往极为频繁,船山先生由此观察佛典翻译、研习的体制,汉地戒律的受容,佛教实践的形态等方面,对早期佛典翻译史,菩萨戒运动的展开,《梵网经》的成立,真谛三藏的生平与著作,地论宗与南朝教理学的关系等问题都有精湛的研究。 本书的写作是基于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目的是向一般知识人介绍佛典汉译史的文化特征。全书目录如下: 序言——东亚世界中的佛典 第一章 走进汉译的世界——从印度到中国 第二章 从事翻译的人们——译经简史 第三章 译作是这样完成的——汉译作成的具体方法与分工 第四章 外国僧人的语言能力与鸠摩罗什、玄奘的翻译论 第五章 伪作经典的出现 第六章 翻译与伪作之间——编辑经典 第七章 汉译给中国语言带来了什么 第八章 根源性因而不可译的部分 第九章 佛典汉译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年表 结语 索引 全书以两种视角展开,前八章在东亚思想、文化史的全局下观察佛教,进而把握佛典翻译史的定位;最后一章在翻译研究的背景中,思考佛典汉译的特色,与西方经典的翻译理论形成对话和补充。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作为佛典原语的各种印度语(Indic languages)如梵语(Sanskrit)、梵文俗语(Prakrit)、犍陀罗语(Gāndhārī)、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等语种的语言学特征,并回顾了近年佛典汉译语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然而作者指出,以汉译语和原语比勘为中心的语汇研究固然在佛典汉译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座城池的“本丸”[②],但正如城市还有其他的建筑、街道、城墙,语汇研究也不是佛典汉译研究的全体。本书的特色在于,重视语汇研究研究,而不囿于此,同时也关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其他关联事项(第10页)。这一特色贯穿于全书始终,在本章的结尾,作者提示了进入佛典汉译研究的几种佛经以外的资料,即大藏经、僧传、目录。特别一提的是,2010年前后,作者与日本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前辈吉川忠夫先生合作,首次将慧皎《高僧传》全部译为现代日语,并加以注释。注释涉及佛教义理、地理信息、文献目录诸多方面,是《高僧传》一书最好的整理本[③]。本书接下来两章的考察别开生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作者对僧传史料的精细解读。 第二章按照时代顺序,介绍了历代重要的翻译家和主要译作。关于最早的汉译佛典,作者赞同冈部和雄的观点,认为今本《四十二章经》与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陶弘景《真诰》有文字上的重合,大致可以确定是5世纪以后成立的。今仍以汉末安世高、支楼迦谶的译作为最早比较妥当。在论及真谛三藏的译经事业时,作者指出,真谛译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并未受到国家的赞助,供养者主要是地方官吏,地点辗转播迁,时常变化;二是真谛在翻译的同时,还亲自撰述了经典的注疏,这些作品有三十多种,散见于隋唐章疏。最有趣的是,作者指出佛典汉译史上存在两个断档期,前者发生在5世纪后半至6世纪初,处在分裂状态的南北朝都出现了译经衰绝的现象;后者发生在中唐般若三藏以后直至宋初,赞宁《大宋僧史略》云:“洎唐元和年中,翻《本生心地观经》,之后百六十载,寂尔无闻。”[④] 这种间歇性的停滞似乎与政治史的事件如安史之乱、会昌毁佛无关,其原因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章[⑤]讨论佛典汉译过程中的方法和分工。古代的译场与现代的翻译活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代的翻译是集体合作完成的。更具体地说,六朝和隋唐以降译场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异点即在于,前者有听众,翻译同时讲说。而后者基本是专家组成的翻译团队封闭作业。作者首先详细解读了《佛祖统纪》卷四三所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天息灾译场的译经程序,以翻译《般若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句为例,分析了每一个作业环节的具体职掌[⑥]。随后上溯至六朝时代,考察了早期译场法会的仪式性特征。本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译者翻译过程中对译文做的增省等改动,还特别指出袭用旧有译文的现象。例如,佛陀跋陀罗所译《华严经·十地品》开头便转用了鸠摩罗什译《十住经》的文字。 第四章分为两部分,前半通过僧传的记载,展现了译经僧人高下悬殊的汉语水平。由此可见,在集团作业体制下,翻译很多时候是依靠通晓梵文的汉地人士完成的,著名的人物有与鸠摩罗什同时,出身于凉州的竺佛念以及刘宋时期的僧人宝云。后半介绍了几位著名译师的翻译理论,比如鸠摩罗什偏好音译的翻译特色,彦琮的“八备说”,玄奘对旧译的批评以及“五不翻”理论,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道安的翻译学说,向称难解。作者指出,“五失本”的含义是翻译中由于梵(胡)、汉文体不同,必须做出的改变,“三不易”的含义传统讲法乃至现代的中国学者或解作“不容易”之意,但本书跟从横超慧日的解读,认为是“不改易”的意思。 第五章从翻译作品引向其对立面,即伪经。首先需要指出,在印度佛教语境里,有世尊时代以来传承有序的阿含经典和较晚成立的大乘经典两大群体,后者严格意义上也不能视为历史人物佛陀所授的真经。但在汉传佛教语境里,只要是忠实翻译过来的,都认为是释迦金口所说。作者给出伪经的定义是“并非由梵语等外国语翻译而来,而是最初用汉语制作,并且采取与翻译经典类似体裁的经典”(第123页),典型的例子是含有中国五行思想的《提谓波利经》,以及明确提到老子、孔子的《清净法行经》。作者随后考察了造作伪经的动机,由内证、外证判别伪经的方法,对造伪者的上报与处置等方面。特别是根据作者个人的研究,分析了伪经《梵网经》成立与《菩萨璎珞本业经》、《仁王般若经》等其他伪经的关系,以及由《十诵律》的口头讲义演化而成的伪经《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 第六章[⑦]讨论了一类特殊的文本形态,即编辑经典。作者罗列了七类编辑本文的形态,即:(1)抄经,如萧子良的抄经;(2)不同译者的译本合成的经典,如《合部金光明经》;(3)项目罗列型的经典,如法数、佛名经典;(4)譬喻、因缘谭集,如《譬喻经》;(5)实践手册类,如鸠摩罗什译《禅法要解》等禅观经典;(6)传记,如《付法藏因缘传》、《马鸣菩萨传》。落合俊典考察日本古写经的调查后指出,《马鸣菩萨传》有刻本和写本两个系统,《大藏经》里收录的属于唐-北宋年间改编的刻本系统,而更早的七寺本和其他日本古写经保存的写本系统也不是严格的翻译,而可能是僧叡根据罗什的教学整理编纂而成[⑧];(7)其他在中国编辑的教理学书,如罗什译《大智度论》、玄奘撰《成唯识论》。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考察,作者提出了他对汉译佛典的三分法(第172页),即: (1)汉译经典(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 CBT) (2)编辑经典(Chinese Buddhist Compilation Scriptures, CBCS) (3)伪作经典(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CBA) 这种分类在翻译和伪经之间划分出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如果说疑伪经研究在于解明中国佛教的实态,那么编辑经典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佛教的学术和仪礼(第176页)。因而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颇有解释力的认知框架。 第七、八两章可以说是由一些语言学的小札记构成,然而在主题上又互相关联。第七章[⑨]讨论佛典汉译给汉语带来的新变化,包括词汇、语音、文体风格各个层面。这里介绍笔者认为最有意思的两条。关于“魔”字,湛然的《止观辅行传弘决》卷5云:“古译经论,魔字从石,自梁武来,谓魔能恼人,字宜从鬼。”[⑩] 《康熙字典》沿袭此说。对于梁以前汉译作品中也出现过“魔”字的事实,宇井伯寿认为此乃后人追改。作者根据敦煌遗书S.4367《道行般若经》卷九、P.3006支谦译《维摩诘经》注这两件早期的写本指出,“魔”字的写法在梁武帝以前就已流行。 此外,作者特别重视梁代宝唱所撰音义书《翻梵语》,并指出此书卷三“迦絺那衣法”是转抄稍早前成立的《出要律仪》的相关部分。 罗阅城 声论者云:正外国音应云“何罗阇那伽逻”。“阿罗阇那”翻为王,“伽逻”翻为城,谓王城。[⑪] 作者首先对这段文字做了校订。“何罗阇那伽逻”和后文的“阿罗阇那”,“何”与“阿”应统一为“何”。断句也应稍作调整——“阿罗阇”(rāja,王)翻为王,“那伽逻”(nagara,街)翻为城。这里有趣的是汉译者处理音写词的微妙差异时做出的努力,即用“何罗”和“逻”分别对应rāja中的长音rā和nagara中的短音ra。这种处理方式在古代的佛教音义书中还有其他例证,而《出要律仪》的这个例子说明此法在6世纪已经出现,因而对考察古代佛经音义的成立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章[⑫]讨论由于文化差异,汉语中不存在对应词汇时的翻译方法,进而探讨了翻译的界限。大体来说,对于没有对应词的情况,有三种处理办法。一是保留音译,二是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中利用旧有词汇创造新词,比如缘起、轮回等等,这两种情况在前面几章都讨论过了。第三种方法是在承认可能产生的文化误解前提下,尽量在目的语中寻找对应词。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作者列举了“nirvāṇa=无为”,“nāga=龙”,“bodhi=道”等等抽象或具体的事物,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和翻译的得失。本章的后半用了较长的篇幅讨论了作为“文化对应型译语”的“圣”字含义的变迁。这个问题的复杂在于,佛教传入以前,“圣”字的观念已经在儒教与道教之间发生了分化,佛教传入以后,作为梵文ārya译语的“圣”又兼具了印度语境中“高贵的”相关的意涵,到了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时,具备二重语义的“圣”字又用于翻译诸如sainthood, holy等词语,因而发生了三重的文化叠加。“圣”字的文化史充分展现出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的复杂机制。 第九章回顾了前面各章的主要内容,对佛典汉译这场历史千余年的翻译活动做了通贯性的反思。包括以下五点: (1)汉译事业的兴盛与停滞,不仅标示着印度本土佛教的运动,同时也反映在汉地佛教的变动之中。作者指出,4-5世纪之交戒律的集中译传,从现有资料看,不是印度戒律文献原典激增导致的,而更多地是汉地佛教僧团的一种迫切需要。此外,前文第二章指出的5世纪后半和9-10世纪汉译的停滞,也并不意味着佛教的中衰。在齐梁时代,我们看到佛教书籍的大量编纂,在中晚唐则出现了倡导“不立文字”的禅宗。佛典汉译与佛教整体的变动之间的微妙关系,尚有许多环节亟待研究。 (2)经典编纂的特征,有两个相反的方向:由于中国人喜好简洁,因而有简略化的倾向;同时,也有类似印度佛教的佛典增广过程。但这种增广不是以合成《大般若经》六百卷那样的方式,而是大型佛教类书的编纂。 (3)与欧洲翻译理论的比较:由第三章所引《佛祖统纪》的记载可知,佛典汉译的过程是先将文本逐字译出,再调整顺序。这种以词语为单位的翻译方式(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不同于现代通行的语句为单位翻译(sentence for sentence translation)。关于“逐字翻译”与“语句翻译”的优劣,是欧洲翻译史上的重大争论。作为古典文学拉丁语翻译代表的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中明确否定了逐字翻译,史称“西塞罗的严命”。在基督教传统中,关于《七十子圣经》的传说似乎肯定了逐字翻译,但圣杰罗姆(St. Jerome)批评了这种倾向。此后一千年欧洲翻译中,一直维持着对逐字翻译的排斥态度,直到马丁·路德翻译德语《圣经》,仍可见其影响。作者认为,东西方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第一,佛典汉译的基本单位是词语,而逐字翻译之后,还有缀文、润文等环节做进一步修饰;第二,佛典汉译中关于文、质的区分类似欧洲翻译史上的逐字和语句之分,但这一分别并没有为鸠摩罗什、玄奘等翻译大家继承,汉译传统追求的理想是“文质彬彬”的风格。 (4)汉译可能产生的误解,这里作者强调的是由于汉语自身的不完善,导致读者在阅读汉译作品时的困难。 (5)文化对应型译语与动态等价。第八章讨论“圣”的文化史,作为文化对应型的译语,可以和Eugene A. Nida提出的“动态等价”(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相类比[⑬]。 由于笔者尚未掌握梵语等印度语言,自然无法全面检讨或复述船山先生的研究。仅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对佛典汉译史的研究提出两点展望。第一,作者在第一章僧传、目录对研究佛典汉译的重要意义,笔者非常赞同,此处还想指出,目录与传记之间常常相互扶翼,例如《高僧传》的叙事许多根据《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序,《续高僧传》的译经门几乎全抄《历代三宝纪》代录部分。对史料进行史源学的考察,能够进一步澄清翻译史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作者在第五章结尾附录中论及西域作为疑伪经成立地的复杂样貌。在讨论西域佛教对汉地影响的同时时,似也应该考虑双向汇流的现象。西域既是印度佛教东传的中转站,有时也是汉传佛教的回流地。这种回传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这就需要从历史学的视角把握西域各地区、各时代与汉地文化的关系。 蒙作者厚意,去年年初得到赠书,书中亲自更定了一些文字讹误,如下: 第viii页第3行:造語である「宗教」,改为:造語としての「宗教」 第123页倒数第2行,旧訳聖書の聖典,改为:旧約聖書の聖典 第196页第5行、倒数第4行:《観無量寿経》,改為:《無量寿経》 总之,佛典汉译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待开拓的方向,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合作展开,而此书则是这一领域难得的概说书。故不揣谫陋,推介如上。 [①] 这一评价来自沈卫荣先生,沈先生认为,“现今国际佛学界内,有能力同时从事印度与汉传佛教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凤毛麟角,知名的仅有日本学者辛嵨静志、船山彻,美国学者Jan Nattier,意大利学者Stephano Zacchetti等。”参见《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注2。 [②] 本丸(ほんまる)是日语词,指一个城池里最核心的据点。 [③] 慧皎著,吉川忠夫·船山徹訳《高僧伝》(4冊),岩波書店,2009年。 [④] 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一,T54.240b. [⑤] 第二、三两章内容的讨论,参见船山徹《漢語仏典——その初期の成立状况をめぐっ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編《京大人文研漢籍セミナー1——汉籍はおもしろい》,研文出版,2008年。同氏《仏典漢訳史要略》,《新アジア仏教史06》,佼成出版社,2011年。 [⑥] 《佛祖统纪》的这段记载,亦见徐松《宋会要辑稿》第200册“道释二六”。 [⑦] 第五、六两章内容的讨论,参见船山徹《六朝仏典の翻訳と編輯に見る中国化問題》,《東方学报》卷80,2007年。 [⑧] 落合俊典《二種の馬鳴菩薩伝——その成立と流伝》,牧田諦亮監、落合俊典編《七寺古逸経典研究叢書 第五卷》,大東出版社,2000年。 [⑨] 第七章内容的讨论,参见船山徹《漢字文化に与えたインド系文字の影響——隋唐以前を中心に》,冨谷至編《漢字の中国文化》,昭和堂出版,2009年。 [⑩]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五,T46.284a. [⑪] 宝唱《翻梵語》卷三,T54.1006a. [⑫] 第八章内容的讨论,参见船山徹《文化接触としての仏典漢訳——「格義」と「聖」の序論的考察》,田中雅一・船山徹共編《コンタクトゾーンの人文学I》,晃洋書房,2012年。 [⑬]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Adler's Foreign Books Inc, 1964.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