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一般从哪里开始?看到一些讲美术史的书,对中国美术的开端追溯的比汉画像石更远,有从图案、图画说起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郑岩:如果看一部中国美术史的教材,当然是从石器时代写起的。但是,就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建构过程而言,是首先从绘画史开始的。中国自己有绘画史写作的传统,但落实到实际作品的,不过是宋元。到后来,根据敦煌的发现和考古材料,逐步向前追溯,构成一部“通史”。“通史”的观念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开启了,只不过那时没有材料,上古的历史,只能写仓颉造字等传说。除了这个传统,中国近代写绘画通史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五四以后的新式美术学校授课的需要。最早的著作是陈师曾、潘天寿等画家写的。他们那时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西美术的优劣问题。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中国美术的传统算一个总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近代“美术”概念的进入,也从结构上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写作,建筑史、工艺美术史便一步步发展起来。 如你所注意到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追溯”的结果。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带着既有的经验,去研究新的材料。我们在分析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乃至史前彩陶时,总免不了用研究晚期绘画史所积累的问题和方法。这些问题和方法,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性的,另一方面也容易简单化。比如,说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就是最早的卷轴画,还有说庙底沟的陶器上花纹就是最早的花鸟画。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个线性的绘画史。但是,我们知道,卷轴画和花鸟画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概念。再比如,发现一幅壁画,就要讨论作者是谁。这样的问题来源于后来绘画史中“名画家-名作”的结构,但考古学的材料,很难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也会比较主动地考虑画像石的工匠、创作过程和技术、语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考古学家考虑得比较少。 您和巫鸿先生基于个案的研究,这种做法是受限于材料,还是说美术、艺术注重个性,所以从个案展开? 郑岩:个案研究只是一种切入方式,口径小一点,可以更深入。刚才说过,就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说民国时期文学史的写作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也是要先算个总账,再跟西方做比较,所以,作为学校教材、讲义的美术史写作肯定是宏观的。但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个案研究的方式,如王逊、金维诺对于道教比较、敦煌壁画的研究,都有很典型的成果。巫鸿等学者对于个案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可能更富有自觉性,与国内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形成了一个反差,所以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 这种差别除了方法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对材料的理解不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有点像大数据处理,研究的是遗存变化的总体规律,以建立年代学的框架,进行文化特征的概括。必须材料全面,结论才更可信。在这种研究中,器物的身份是“标本”。在几十件、上百件器物的综合分类过程中,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独特的价值是看不到的。美术史不同的是,要把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看作是“作品”。普遍性当然重要,但这些作品的独特性也需要加以重视。就像文学史研究中精细地分析李白的一首诗那样,四羊方尊也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美术史就应该对于特殊的作品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式的研究。 当然,我觉得这两种方式也不能对立起来,美术史也关心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艺术团体的总体面貌。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个案研究可以将我们引向细节,但我们不能将局部无限度地放大。我的一个矫正办法是同时注意考古对于共性的总体把握,与美术史的个案研究互相制约。我个人也不是一种写作的模式,我也有比较宏观的讨论,过去几年还参加了教材的编写。编教材给了我一个机会,重新去思考中国美术史整体的框架结构、术语、脉络、理论等大问题。反过来,这些思考问题也可以落实到个案研究中。 对于美术史研究,比如您做的墓葬美术考古,有结合考古、美术,还有结合历史、民俗等文化因素共同去诠释和解读背后的“大历史”,个人的一个困惑在于,一幅画与其背后的“大历史”的联系靠诠释和视觉的呈现是不是足够成立?这个诠释是不是足够支撑起这个大问题? 郑岩:这是美术史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图像材料和文献材料形式上不一样,是两种语言。但它们都可以看作文本,都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它们本身也构成一种历史。图像与文献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虽然彼此可以交叉,但并不重合。它们彼此能够互证当然很好,但它们不是谁从属于谁。就你所说的“大历史”的研究而言,图像也是一种证据,虽然不是像人们说的“眼见为实”那么简单,但它的确是可以用作材料的。美术史家像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家一样,也要从事材料审核或文本批判,比如我们要讨论一种图像本身的传统、材质和技术、形成过程、形式特征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寻找它与文献呈现的各种信息之间有机的关联。大家常常怀疑美术史对图像的阐释,除了很多文章论证本身存在问题外,还在于人们更习惯文字表达。与图像相比,文字的形式更接近自然语言,所以看上去更直接。人们习惯上认为,对于图像的解释,只有找到了文献证据才是靠得住的,但后现代理论早就说清楚了,文献也只是一种说法,是一种文本。 美术史研究的作品是第一是视觉的,第二是物质的,这决定了对它的阐释不能无度地发挥,因为我在说它的时候,你也看得见它。材料的物质性和视觉性对阐释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有制衡的作用。现代意义的美术史要建立一种新的阐释语言,旧的语言是不够的。比如,某甲说:这幅画用笔“高古”。某乙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某甲说:你功力不够!如果美术史局限在某甲这种语言中,就无法成为与其他学科沟通的一个领域,而成为一种秘密宗教,就无法像你说的那样,将美术史与考古、民俗、社会学、宗教学、思想史联系在一起。 至于个案研究是不是能够解答“大历史”“大问题”,我想个案研究是研究的过程,不求马上解决什么大问题,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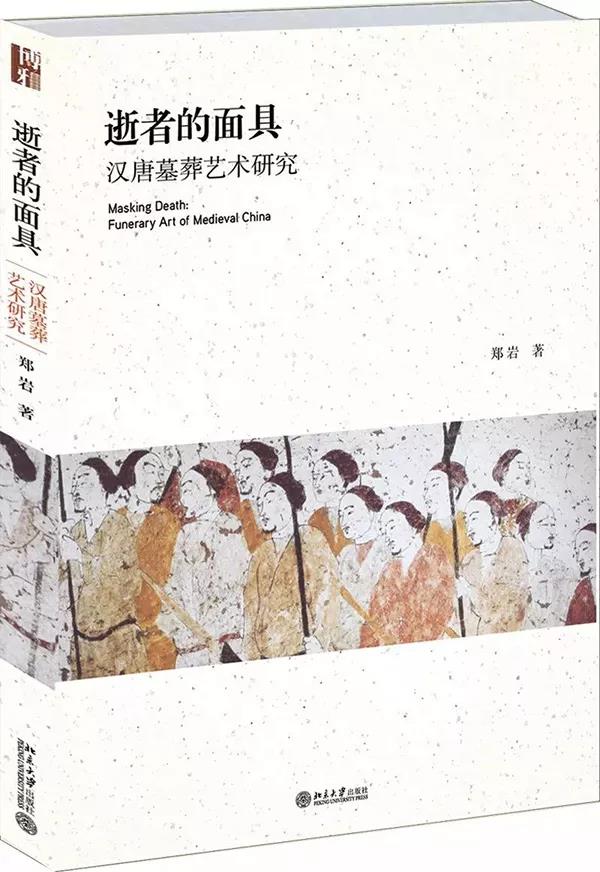 郑岩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