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家和先生:关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一些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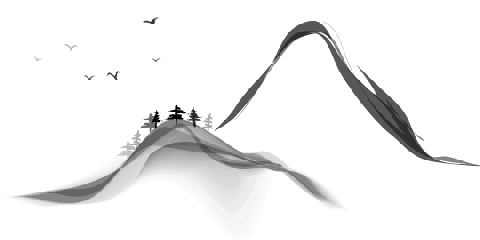 文 | 刘家和 现在我们不难从社会上看到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见解,即以为传统代表过去,重视传统就是向后看,就是保守,就不利于现代化。我相信,一般持有这样见解的人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即渴望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愿意再处于过去那样的经济落后的状态中。有人还把当前的种种贪污腐化之类的丑陋现象与历史上的类似现象联系起来,以为这都是传统的恶习,从而对传统深致不满。这些想法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对于传统文化,仅凭着厌恶的感情或简单的抛弃的决心,人们就真能作到与之彻底地断绝关系吗?在与传统文化彻底地断绝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又将怎么样进行教育?看来这些都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人们往往把传统理解为过去,既是过去,即是“明日黄花”,有理由也有可能把它一脚踢开。按“传统”一词,来自西文tradition(英、德、法文皆如此,俄文实亦同);在一般辞书中,此字的解释大约有“传统”、“传说”、“习俗”、“惯例”等等。这些释义都易使人联想到过去。因此,把“传统”视为过去,也并非全无理由。可是,“传统”虽与过去密切相关,却并非纯粹的过去。按今日西文中的tradition来自古拉丁文traditio。此字除上述诸义以外,还有“交付”、“传递”、“献给”、“贩卖”等义。究其所以,盖此字由tra(=trans,意思是“转”)和dit(来自dare、do,意思是“给”)构成,本义就是“转给”、“传递”;其它义项皆由此引申而来。由“传统”之本义而言,它所表示的只是一种在时间流程中发生的行为,其自身也应当是一种过程。既是转给,就必须有授者,又必须有受者。自受者角度言之,其授者为前行者,而其所授亦必为前所已有,故在时间上为过去。受者自身与接受行为在过程中既是转给,受者必然要转化为授者。如果他在时间上为现在,则他的受者又必然在时间上为未来。由于每一代人在“转给”之流中必然既为受者又为授者(像接力赛跑时的运动员一样),“传统”本身也可以说是由背向过去而面向未来的“现在”(严格地说那只是极限趋近于0的一瞬)的无间断的展延过程。所以,过去的“现在”的延伸成了传统,当前的“现在”即在传统之中,未来的“现在”将为传统的继续。传统是过去,但并非与现在无关的过去,也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延续到现在并对现在起着作用的有生命的“过去”。如果说已死的过去本来就不存在加以消除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存在),那么与现在有密切联系的、尚有生命力的过去就又不是可以简单地一脚踢开了事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历史。历史上有没有过割断传统的事例呢?有,那就是在一个文明或民族由于外力或内力的作用而被消灭的情况下,例如古代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等,以及在近代初期被西方殖民者消灭了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等等。应当指出,这些都不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而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传统”是不能简单地被抛弃的。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人,他们在自觉的层面上是传统的激烈反对者,而在实际上却又是传统的执着的继承者。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批评儒、墨显学称尧舜、重传统,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因而主张抛弃旧的政治和学术传统。但也正是这个眼睛一般总向前看的韩非,却从眼睛一般总向后看的道家那里继承了一种传统。他写了《解老》、《喻老》,继承了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传统以及愚民政策的主张。“文革”中的“四人帮”也是以与传统作彻底决裂的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自以为前无古人;可是,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焚书”之类,所继承的不外乎秦始皇的残暴传统。他们破传统的姿态愈高,而传统之阴暗面在他们身上表现得也愈烈。江青怀着篡权的野心,给历史上的一些女统治者如吕后之流戴上“法家”、“改革家”等不伦不类的桂冠,用比附的方法来从政治上装饰自己。这更是有意歪曲地利用传统,而不是什么与传统决裂了。当然有人会说,上述的人是一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他们只是不让人民知道传统,以便他们自己可以任意歪曲并利用传统。这样说诚然有其道理。不过,如果并无上述人等的策略图谋,而是真诚地渴望抛弃传统,那么人们是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呢?看来答案仍然难以是肯定的。人们对其所要求否定的势力或思潮,往往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须举例。可是,只要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就不能说你已经与所要否定的对象彻底决裂,因为你已经利用了他的传统,因袭了“其人之道”。当然这往往并非是在自觉的情况下实现的。例如,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人出于义愤,对他们歪曲历史的行为作了批判。其中有些人批评江青利用吕后等人为其政治阴谋服务,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有人为了批判江青而把吕后等说成野心家、阴谋家,从而说明江青也是此类角色。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这种批判在政治上没有与江青彻底决裂,可是,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批判在方法上却与被批判者有其相通之处。吕后自是吕后,江青自是江青,批判江青原本不必牵涉吕后。因为江青曾经利用吕后为其服务,人们习惯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又借吕后来批江青。于是不自觉地在方法上继承了被批评者的传统。从这一事例看来,单凭义愤并不足以使人能够摆脱他所要摆脱的传统。  这样说来,人们在传统面前就毫无自由而只能俯首听命了?事情倒也并非如此。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对传统的分析或本来意义上的“批判”(criticize,此字来源于古希腊文,本义是“判断”;无分析便无判断,所以这里用“批判”一词表示“分析和判断”),是对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的反省或反思(reflection)。我们没有任意抛弃传统的自由,却有对它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自由,没有在思想上任意与传统断绝关系的自由,却有反省我们对传统的认识的自由。譬如,现在人们常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说实际是指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人会主张维护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把统一体分解为不同部分,这就是分析;把中国传统文化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也就是对它作了分析。由分析而定取舍,这就是对传统作了批判。其实,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是在批判中进行的。人们总是把好事与坏事分开,取其好者,弃其坏者。这是人们通常都采用的分辨的方法,在此不须多作说明。不过,问题往往不能止步于此。譬如,当人们燃煤或油取暖的时候,燃料中的热能被认为有用的而收取,其他成分就被作为废料以烟尘的形式排放了。这是第一次批判。随后人们又发现,在煤或油的烟尘中还有名种可被应用的成分,只要加以析取,就能从中获得很重要的原料。于是批判进了一个等次。人们对于客观世界总是这样不断地批判着,批判每进一个等次,认识也相应地深入一个等次。对于传统,同样有着不断的批判的过程。这也就是对于传统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人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一现象本身作一些分析。我以为,这一现象本身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人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本身,从一个方面来看,它是知识的增长,其进行的方向是肯定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对于过去错误认识的纠正,其进行的方向又是否定的。《老子》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他是把“为学”和“为道”绝对对立起来看的。我认为,如果把“日益”和“日损”二者结合起来,那恰好就是人的认识不断深入过程本身的基本特征。应该说,这也就是文化过程的特征。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略说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其中表述了个人的一点见解:“文化是人类社会对于愚昧的否定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化不是人类的本能产物,也没有某种先验的文化资源贮藏在人的头脑中,可供随时、不断之采发。蜜蜂能够凭本能准确地构成正六边形的蜂房,而人类在最初试图构木为巢的时候,所能搭起的窝巢必定比蜂房显得拙劣。可是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在于其本能,而在于其能够不断克服其自身的缺陷。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不断否定自身的缺陷,从而能够把他们的居室从不避风雨的窝棚逐渐变化为摩天大厦。当人类最初试图搭盖窝棚的时候,他们是在否定过去无窝棚的状态。他们搭成的第一批窝棚,既包含了建筑技术的最初萌芽,又包含了大量的非科学成份;前者显示了他们的成功,后者则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他们从窝棚的不避风雨和易于倒塌中汲取教训,不断改去错误,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前进。这种否定的过程,也就是文化的过程。现在,我经过多年的反省,又试图否定自己过去认识中的缺陷。文化固然是一种否定愚昧的过程,但又非单纯的否定过程。当人们否定错误的时候,他们实际也是在肯定和发扬正确的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正确是否定错误的结果。同时,在增长中的正确因素又是使错误因素得以纠正的必要条件;无正确因素,又如何能够纠正错误因素?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对错误的否定,又是正确因素积累的结果。所以,人类文化的过程,人们认识不断深人的过程,就是“日损”而又“日益”的过程。无“日损”便无“日益”,无“日益”便无“日损”;有“日损”乃有“日益”,有“日益”乃有“日损”。“日损”与“日益”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一方面是对事物不断批判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自身认识的不断反省的过程。而反省本身,恰好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它以过去的认识为思考依据,因而不能脱离过去;它又以批判过去的认识来寻求新知,因而又不能不脱离过去。对于这种矛盾现象,古代中国人已经有所发现。《易。大畜》卦象辞:“大畜,刚健笃实挥光,日新其德。”而此卦象辞则说:“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卦所以具有刚健笃实的品质,是因为其德日新,不断弃旧而图新;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就在于不断否定过去。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德之建立,又有待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集之;所以,德之建立,又不能与过去一刀两断,彻底决裂。《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在这里,无“日新”,便无“生生”;唯其“生生”,乃有“日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没有在这种矛盾现象的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机智地、也是无比深刻地找到了一条沟通两极的桥梁,用孔子的话来概括,就是“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在这里,“温故”既是对“故”的反省,也是对“故”的扬弃(aufheben,sublate),因而能够推陈出新。  如果以上两点分析无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无论是传统还是文化,或者是传统文化,它本身只能是一种既断又续、既否定又肯定的批判的或扬弃的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讨论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教育的基本功能,按个人的理解,就在于保证人类文化过程的延续和发展。而文化的过程,按以上所分析,乃是对于既有文化的不断的“日损”和“日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当然也只能对传统的文化作批判的传播。如果有人要求教育与传统文化完全断绝关系,那么,他到底将用什么作为他的教育内容?难道作为教育内容的文化可以凭空创造出来吗?可以无中生有吗?这当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不过,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das radikalste Brechen,the most radical rupture);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用了“决裂”(das Breehen, rupture)一词,而且加上了“最彻底的”的定语。这也就是“四人帮”曾经高谈的两个“彻底决裂”的所谓根据所在。可是,人们难道可以把这里的“决裂”望文生意地理解为“彻底断绝关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任何渊源关系,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没有也不应该有其各自的来源的。这样能够说得通吗?何况毛泽东也曾明确地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版,第496页)如果真地按照“四人帮”的方式来理解“彻底决裂”,那么,毛泽东的这一段为大家都熟悉的话,岂不是也成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了?这能够想象吗?因此,对于这里的“最彻底的决裂”,最好还是用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的思想去理解,即理解为“最彻底的批判”(本来意义上的“批判”)或者“最彻底的扬弃”。其实也只有这样才是坚持了辩证法。  极左的“决裂”空谈,从来不能表现为与传统决裂的事实。实际上,这种空谈只能表现出空谈者在哲学上的无知以及他们在实践中的盲目性。正是由于只要求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彻底断绝与传统的关系,而拒绝对于传统的批判,他们为自己排除了理性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可能,而陷自身于盲目的冲动之中。他们对传统文化既不可能没有取舍,却又不能有合乎理性的取舍,于是就只有凭私欲的驱使来行动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行动上,往往从传统中弃其精华而取其糟粕,并且往往不知羞耻地、毫无忌惮地把那些糟粕挥舞到疯狂的程度。譬如,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无政府主义的打、砸、抢曾经被视为最能与传统文化“决裂”的行为,而在教育界里当然也只有交白卷的造反派才能成为“英雄”了。其实,打、砸、抢和交白卷也并非真地史无前例,也根本谈不上什么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而只不过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而已。所以“四人帮”的“教育革命”在历史上只能是一次彻底破坏教育的闹剧,正如“文革”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次反文化的运动一样,岂有它哉。 “四人帮”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散布的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观念,在社会上、在教育界都还残留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由于传统的道德观念曾经被毫不区分地视为无用以至有害的糟粕,人们就惯于把“信义”的观念置于脑后,于是制造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伤天害理地炮制假药等等现象,都乘改革开放之机一齐涌现出来,以至屡禁不止。由于尊重文化、尊重学术的优良传统在“文革”中被涂上种种可笑的油彩然后又撕得粉碎,造成了不易克服的影响,现在要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困难重重。当然,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影响,那也未免把他们的历史作用作了某种夸张。不过,无可怀疑的是,“四人帮”在“文革”中把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扰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自以为是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实际上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乘改革开放之机流入的外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盲目地糅合起来,从而造成了一种最糟糕的现象。这种现象如不克服,必然要给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问题。  以上曾经说到,教育就其内容而言离不开传统文化,离不开批判地传授传统文化。现在面对上述现象,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更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意义了。我们说要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既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外国的传统文化。当然,首先要重视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生活于中国传统之中,不管你意识到或未意识到,自己身上总或多或少地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你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抛弃传统,说不定正是抛弃了优良传统而发挥了恶劣传统。所以,既然是中国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批判的认识;有了批判,我们才能正确对待传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什么还要重视外国的传统文化呢?因为文化并无国界,人类所创造的优良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要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继承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其实中国早已脱离了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时代,早在清朝末叶,洋务派就因形势所迫而开始半推半就地引进外国文化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实际上已经有大量外国传统文化被引人并且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为一体,从而成了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其中有精华与精华的结合,也有糟粕与糟粕的结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有待批判的传统文化了。时至今日,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且行将变为一个“地球村”。在此情况下当然更没有排拒外来文化的可能性了。如果有人担心外来文化中的糟粕会毒害我们的社会,那么这种担心也并非多余的。艾滋病毒就是跟着外来文化的糟粕传进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糟粕(如吸毒、淫乱等)与之相应,它不是进不来、就是进来也无法发展的。所以,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外来文化糟粕与中国文化糟粕的结合,而所需要的却是外来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精华的交融。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不论其文化保守心态,他的话至少也违背了有关“体”、“用”关系的基本常识。体与用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为实质或本体(substance),一为作用或功能(function);一定的体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用,一定的用也必然反映一定的体。故甲体必然显示出甲用,而不能显示出乙用;甲用亦必然反映出甲体,而不能反映出乙体。“中体西用”实际只能是一种类似牛首而马鸣的怪物。那么中外文化的结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可以打个比方,那就是“嫁接”。我们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传统文化分别进行分析,辨明其为精华或糟粕,然后从外国文化中选出优秀的嫁穗,再嫁接在经过精选的中国文化的优秀砧木上。通过这样的嫁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优秀文化品种。它既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兼有中外文化之优长,可以硕果累累。其实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又何尝没有接上中国文化优秀嫁穗的文化植株呢?所以文化交流实际也就是文化互相嫁接的问题。这样的“文化嫁接”工作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但也是十分富有意义的。 文章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上古史、中国思想史等。代表著作有《古代中国与世界》、《史学、经学与思想》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