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鲁迅 《桃花树下的鲁迅》 鲁迅研究 导语:2020年9月九州出版社推出《桃花树下的鲁迅》一书,在学界内外引起反响。鲁迅研究专家、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称作者黄坚是“鲁研界外的高手”。黄坚为江西萍乡人,定居南昌,曾著有《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现特邀两位学者就《桃花树下的鲁迅》展开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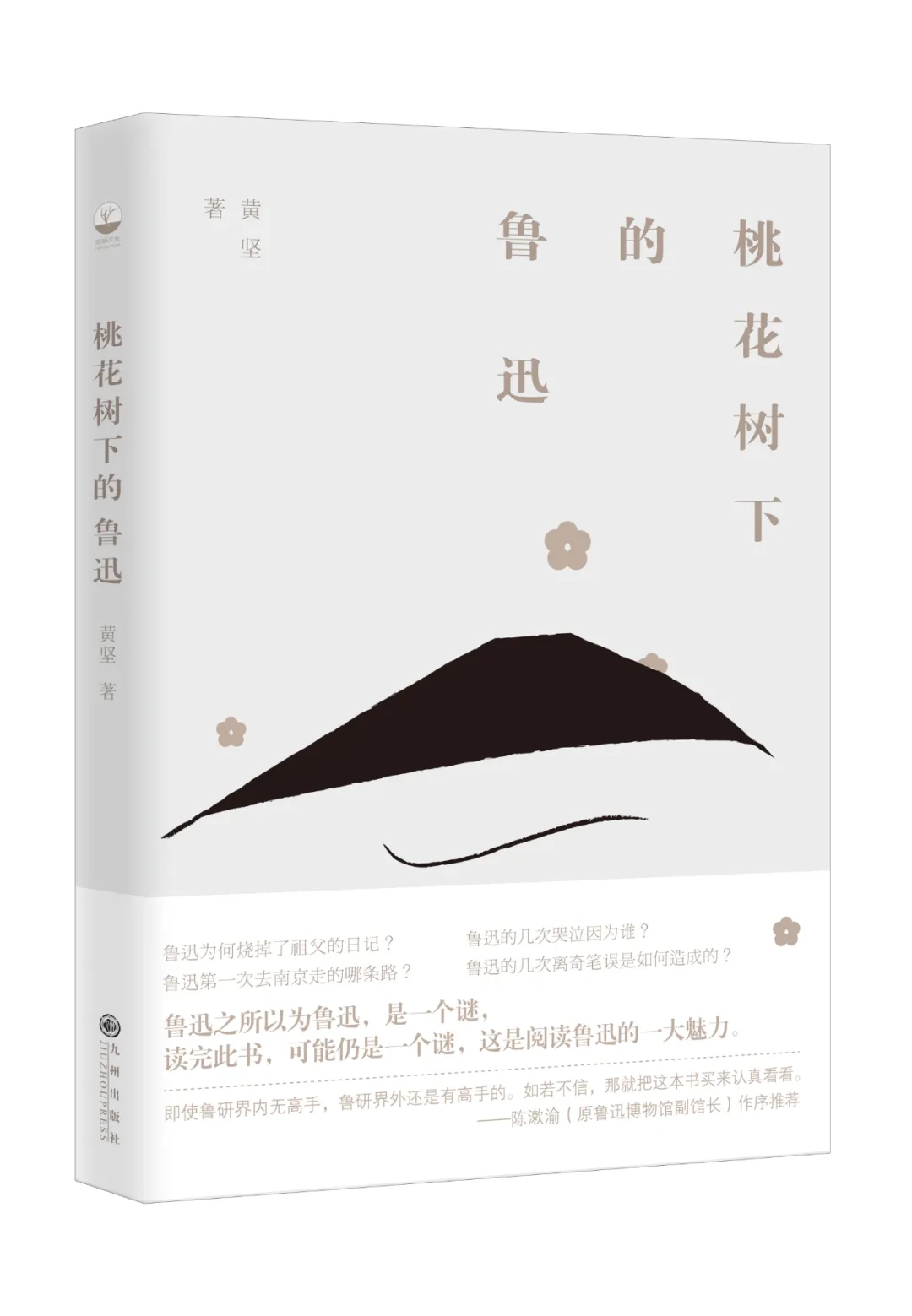 “人之子”鲁迅 黄海飞:看到书名有点意外,“桃花”这样一个指向“春天”“轻松烂漫”的意象在第一印象里似乎很难和鲁迅联系起来。如果让您用一种树来跟鲁迅勾连,您会想到什么树? 胡少卿:第一反应可能是枣树,冬天的枣树,黝黑,锐利。 黄海飞:是,大多数读者第一印象是枣树,就是鲁迅写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作者独独挑出“桃花树”,显出对鲁迅文字的熟稔,以及对于鲁迅形象的别致意见。读完全篇,发现桃花和鲁迅的并列很有道理。作者是要揭示鲁迅温暖或生活化的一面。 胡少卿:努力写出一个真实的活人。 黄海飞:作者抓住了鲁迅生命中非常精彩的一些瞬间。他比较关注鲁迅生命的两端,一端是青少年鲁迅,另一端是老年鲁迅。为什么鲁迅最后会突然想起桃花?当时已经是1936年4月15日,他给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颜黎民)回信,大约颜黎民在信中谈到桃花。 胡少卿:从作者行文中我联想到,这带有一点回光返照的色彩。张爱玲的小短文《爱》里写一个被拐卖的女子,到年老的时候,也总是回忆年轻时在春天月光中的桃树下和一个邻家小伙的偶遇。 黄海飞:是进入了生命晚年的一种状态,书里作者也提到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读鲁迅晚年的作品,大概是1934年以后,能看到一个有点衰老、心力交瘁的鲁迅,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在上海的鲁迅过得一点都不自在。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说我很想出去,但没有办法,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同时也身不由己,他有很多活动,成为他的枷锁。比如书中提到的酒,鲁迅身体其实不能喝酒,但不断地有招饮,必须去应酬。像《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封信其实给了他生命最后一击,加速了他的死亡。 胡少卿:这本书在市场上被归入传记类,其实它不是传记。波兰诗人米沃什说,传记就像一个蚌壳的壳,真实的蚌的生命已经消失了,读传记只是收获了一个壳而已。黄坚采取了一种比传记更为迂回和游击式的方法去靠近鲁迅。他考察的角度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是平视。他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缺陷的人来写。作者选题的角度侧重于生活和日常的方面,比如讨论鲁迅是否好酒、鲁迅的哭泣、鲁迅的遇险与避难、鲁迅的笔误等。鲁迅的生命中不只有黑暗、尖锐、冷峻的东西,也有温暖明亮的东西。黄坚说鲁迅的生命是一面三色旗:“黑色代表历史和力量,白色代表道德和幻想,红色代表浪漫和温暖,这样才构成一面完整的鲁迅之旗。”作者对鲁迅的描述可以和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相印证。萧红说鲁迅是爱笑的,他的枕边放着一张小画,在病中常常拿出来看,画上是一个穿长裙头发飞散的女人在大风中奔跑,地上散落着玫瑰。这些细节体现了鲁迅内心柔软的一面。黄坚以前的著作《思想门》,把孔子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这本书的思路一样。孔子跟鲁迅算是我们树立的两尊雕像,黄坚努力想把这两尊雕像复活为我们身边的朋友。 黄海飞:本书确实对于过去刻板的鲁迅形象进行了反拨,回归到“人之子”鲁迅。我们可以梳理下鲁迅形象的变迁。鲁迅生前,人们对于鲁迅的评价是多元化的,有褒有贬。鲁迅自己很清醒,他没有把学生或朋友的过高赞誉太当回事。别人把他奉为“导师”或者“青年叛徒的领袖”,他是不要这些“纸糊的桂冠”的。很多人把鲁迅跟高尔基相比,鲁迅在书信里则自谦地说:“我那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游移。” 胡少卿:当年刘半农想推荐鲁迅参评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就回信说自己不配得奖:“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黄海飞:从鲁迅逝世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中,鲁迅的地位被抬得非常高,不断“圣化”。“文革”以后开始反拨,出现了非议、否定鲁迅的声音。最为知名的就是21世纪初,王朔等发表的非议鲁迅的文章。近十年来,确切地说是微博、微信兴起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鲁迅的形象变得轻松、活泼,甚至略带搞笑,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成为流量的宠儿,如爱怼人的鲁迅、吃货鲁迅、设计师鲁迅。我称之为“轻鲁迅”。 胡少卿:课上讲鲁迅的时候,学生对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状况特别感兴趣,说他属于当时的高收入群体,生活方式很时髦,常去看电影,也很讲究吃。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鲁迅作为凡人的生理性的一面,如考证说他日记里记载的“夜濯足”是指自慰,而跟弟弟周作人反目的原因是偷看弟媳洗澡。 黄海飞:这就有点跑偏了,甚至可称恶俗。但我们确实能看出这样一个趋势,近十年或者说进入21世纪以来,生活鲁迅、作为人这一面的鲁迅重新回归,甚至占据了主流地位。黄坚这本书是在这个潮流之中的。 胡少卿:鲁迅是普通人,但同时有他的非凡之处。黄坚努力去写出现实的多面性。他在《鲁迅的哭泣》这一章里记载鲁迅的一次流泪,我印象很深。引用的是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这篇文章里的回忆——因为鲁迅说了许多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有个日本歌者在宴席上问他: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增田涉看到鲁迅“眼里湿润着”。从这个细节里可以看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怒骂和批判都是出于对中国的爱。他爱的不是哪个具体的政权,而是这片土地、土地上苦难深重的人们。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把“民族魂”三个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鲁迅有很值得尊敬的一面,不能无限制地把他拉向琐碎、日常,黄坚在写作中是注意到了保持这种平衡的。 黄海飞:上面我提到的“轻鲁迅”现象,是不是把鲁迅看得太轻巧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太沉重,刻意在回避这些东西,但鲁迅沉重的一面反而更有价值。 胡少卿:那才是决定鲁迅之为鲁迅的地方。 黄海飞:您刚才提到的增田涉的回忆,我之前读到那里也很感动。有人曾把鲁迅和庄子做过比较,他们确实有一些相似点,比如,面冷心热。 胡少卿:嗯,就是说话可能很毒,但内里是古道热肠。 黄海飞:鲁迅自己在文章里也提到了,他说我其实是不够世故的,如果够世故,我就不会说出来。正是因为对于民族和文化的热爱,才会造成他的那种“峻急”。他的态度、立场、说话的方式是非常激进的。这也关涉到本书涉及的鲁迅的两面性问题。鲁迅写文章和在生活中其实有两个形象,或者说有两套说辞,这中间存在矛盾之处。黄坚老师敏锐地发现了,本书多篇文章都有涉及,比如《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包括鲁迅一方面是爱喝酒的,但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自述却称不喝酒。不只是喝酒的问题,鲁迅在很多地方都是以一种决然否定的语词来表述的,但跟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完全相反。这时就要区分鲁迅表达的语境是什么,是一种公众话语还是私人话语。鲁迅自己对公和私分得很清楚。 胡少卿:钱理群老师曾把鲁迅的文字分成两种,一种是“为自己的”,一种是“为他人的”。“为自己的”以散文诗集《野草》为代表,会去展露内心比较黑暗、像深渊的一面;“为他人的”包括他的小说集、杂文集,会比较多地给出信心和希望。现实本身就很矛盾、复杂,一个人的性格中也可能纠结了许多矛盾的东西,人不是单面的,作者没有向哪一个极端强调,而是努力让自己的写作符合于生活的微妙和复杂,把握住了平衡。 见微知著 黄海飞:陈漱渝先生在序言中说,作者在写这些“小文章”时下了“大功夫”,不少文章写得都很“厚重”。作者很有问题意识,能在他人不疑处生疑,多问一个为什么。 比如鲁迅与祖父周福清这样一个选题,是过去鲁迅研究界关注很少的。中国知网上从1981年至今总共只有19篇文章,而且大部分围绕周福清的生平及科场舞弊案,对于鲁迅和周福清的关系论述得不多。这个话题还具有开掘空间。 又如《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选取的也是一个鲜为人关注的话题,即鲁迅第一次去南京求学的交通问题。这是已有研究的盲点。其姊妹篇《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以史料集锦的方式关注鲁迅第一次去上海的经历。过往研究鲁迅与上海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上海十年时期,近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施晓燕老师的《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关注的也主要是这一段。而对于1927年以前鲁迅与上海的交集,学界关注较少。如本书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的:“年青的鲁迅和跟他一样年轻的上海,在屡次的擦肩而过和相互注视与映照下,经历了彼此的成长与蜕变。然而,这样一种缘分关系,却至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这里捎带说一句,作者在文章中有一个精彩比喻:“假如把鲁迅的一生,看成是一座现代双塔斜拉桥,北京和上海,就是那两座高高的双塔,其在鲁迅生命中所占的意义,是怎么评估也不过分的。” 胡少卿:作者不仅选题的角度比较清奇,而且带有跨学科色彩,比如《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综合了地理学、社会史等多方面的知识来考证。 黄海飞:对!这篇文章讨论鲁迅为何舍近求远,不走相对直线的运河路线,而要绕道上海、折向南京,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展现出晚清末年杭嘉湖苏地区运河衰败、治安糟糕、吏匪横行的状况,由此来解释鲁迅的选择,合情合理。这是典型的“以小悟大,见微知著”,以鲁迅走哪条路这样一个很小的问题,展现出晚清末年江浙沪的交通史、社会史。又如在《桃花树下的鲁迅》这篇中,作者在讨论鲁迅和桃花这一意象时,突然宕开一笔讨论中国文学史上对于“桃花”意象的评价的变迁,也展现出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视野。 胡少卿:还有一处是典型的以小见大、由小及大。作者考证说鲁迅跟他的祖父周福清在“寄望心太重”这一点上很相似,因为“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而性格“峻急”;峻急不仅体现在对周作人的懈怠“挥以老拳”,也体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上,甚至体现在对自己身处的民族的期望上。这种解释从私人生活引申到了鲁迅的写作风格。为什么鲁迅的杂文里有很大的火气,总是跟人论战?就是因为“爱之深,恨之切”。这样话题就拓展得深广。这是典型的“小题大做”,一种很妙的做文章的方法。 全书带有知识考古的色彩,作者像“史料侦探”一样,在大量的史料里去寻找线索,并把这些线索勾连起来,试图去复现一个多面而复杂的现实状况。可以看出作者是热爱鲁迅的,但这种热爱不等同于盲信盲从。作者要把他的热爱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地基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把前人对鲁迅的讲法的很多虚浮之处都夯实了。比如指出鲁迅的笔误,这是正常人都可能犯的错误,没有必要去为了塑造一个完美的鲁迅而去掩饰。以前通常说鲁迅是革命家,但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本书就去考证,鲁迅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是什么?是很复杂的,鲁迅有时候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怀疑的状态,有时候他甚至身处学生的对立面。通过作者对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热闹的群众运动,多多少少是保持有一定距离的。还有鲁迅对于自己在共产主义中国的遭遇的想象,显示了鲁迅预见未来的敏锐度。在《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一章,作者指出,鲁迅跟论敌的论战,有时会局限于地域上的某种偏见或既定想象,这其实是提示了鲁迅思想中的弱点。 黄海飞:黄坚老师的研究是和学界在一个频道同步共振。他肯定没看过邱焕星老师的论文,但他关于鲁迅与学潮的观点与邱老师是一致的。 微妙感 胡少卿:在求真的基础上,作者行文中还有许多文学化的、带有灵性的成分,让表述清晰而有美感,有点像黄仁宇描画历史的手法,也有点像本雅明的评论,在扎实的基础上加入感性,试图勾勒出历史当中的微妙感,能看到明显的才气。书中提到鲁迅笔名中的“迅”字,跟他年轻时在上海看见的轮船的速度有关。这个观点以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 黄海飞:这个我不太同意,这个判断下得有点急了。“鲁”这个字,大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这就是鲁迅母亲的姓,鲁跟周本来就是同姓的国家。而关于“迅”字则有几种解释,最为通行的说法是许寿裳先生的版本,他当面问过鲁迅,鲁迅回答说是“愚鲁而迅速”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第二种,黄坚在书中也提到了,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说是“狼子”或“大力士”的意思,这是比较奇异的说法。作者在文章里面也不同意侯先生,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猜测“迅”字与鲁迅青年时期对轮船速度很快的观感相关,而且作者在书中还引用了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访问日本时坐新干线的典故。 胡少卿:郭沫若写过一首诗《笔立山头展望》,是他在日本的时候,看见日本的港口停满了轮船,感到很震撼。诗里将轮船冒出来的黑烟喻为黑牡丹,将其视为文明的象征,这是鲁迅的同代人对轮船的震撼体验,轮船在那时就代表着一种现代和进步的力量。 你刚才提到青少年时代鲁迅和上海的关系之前研究得比较少。作者这里揭示了上海对少年鲁迅、青年鲁迅的影响。一个人很多事情,其实在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都已经决定了,他在成年的许多做法,是对以前埋下来的线索的一次追溯、一次印证。作者推测鲁迅后来取笔名为“迅”,跟他在上海所感觉到的轮船的速度有关。当然这本身是无法求证的,只能说是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就意味着鲁迅的“迅”这个笔名代表着鲁迅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迫切心情,希望中国也能够加快速度,赶上世界文明的列车。“鲁”有迟缓的意思,和“迅”正好构成一对反义词。 黄海飞:不得不承认,作者很敏感,他能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很有想象力。青少年鲁迅这一块的研究非常重要,但也是现在鲁迅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因为这段材料很少。有一些学者正在做这一块研究,比如河北大学刘润涛老师,他就专门做鲁迅的前半期研究。在这一点上,黄坚老师跟当下的学术潮流也是暗合的,他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在潮流当中。 胡少卿:作者的写作带有某种文学化的想象,这个结论不是一个真凭实据的连接,而是带有主观发挥。 黄海飞:如果加上“可能”两个字,就更严谨一点。其实作者后来也没有下定论。 胡少卿:作者写作的时候还是很注意把握那种微妙感的,他不完全说透,因为有些事一旦说透了就显得特别俗。比如《桃花树下的鲁迅》这一章,一般提到桃花往往跟爱情、桃色新闻有关,而作者在这一章里也提到了鲁迅在写到桃花的时候,他兴奋的心情可能与他和许广平的恋爱有关系,但作者拒绝绝对地把两样东西套在一起,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这章里面作者写了鲁迅的爱情,也写到鲁迅对桃花的兴趣,但这两者之间又不必然构成某种关系,所以这地方作者是点到即止,这样的处理是很妙的。相对来说低端一点的作家,就容易把这个事情给坐实了。 黄海飞:作者确实很会写文章。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感叹作者写作的巧妙。作者善于设问,就像您刚才说的像一个史料侦探一样,不断地提问,然后回答,然后又提问,他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文章的结尾也结得好。过去人常说开头和结尾是最难的,汪曾祺原先就谈过沈从文的结尾非常好,其实汪曾祺自己的结尾也结得漂亮,结尾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的。黄坚老师很多文章的结尾都结得非常漂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一篇的结尾收束,说是“就像周福清挥舞八角铜锤追打四七”。他很多的结尾都是这样的单句结尾,很短促又很有力,有一种余味、余韵在里面。 胡少卿:作者努力揭示史料之中微妙的关系还有一处令我印象很深。在《鲁迅一生中的避难和风险》这篇里,注解里有一句话:“从某种角度说,幽闭于深宫的光绪皇帝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政治‘喷嚏’,却成为二十世纪初文化思想鲁迅诞生的‘第一推动力’。”是说因为光绪皇帝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很苦闷,所以把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加以重判,而祖父的遭遇又影响了鲁迅的成长,构成了鲁迅的某种文化基因。这个地方有点像揭示史料和史料之间的蝴蝶效应,非常敏锐而有趣。 黄海飞:我联想到柯林武德所写的《历史的观念》。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是需要想象力的,要在观念里面去推演历史。无论是史料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想象力都非常重要。能把两个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勾连在一起,并进行论证,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一家之言。我很认同陈漱渝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黄坚老师确实可以说是鲁研界外的一个高手。 胡少卿:黄坚是民间学者,不属于任何机构,也不属于体制。不过他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的五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宣民先生,曾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助手。黄坚做研究是出于兴趣,就像作者介绍里说的,他“以研究与写作为志业”。他不需要去考虑我怎么写学术杂志才能发表之类的问题,而是按照“我觉得这样写最好,我就这样写”的方式来写作。 黄海飞:是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作者很少受束缚。但是让我很惊讶的一点在于其实作者是很遵守学术规范的。我看到书中不仅重要的材料都有注释,甚至在一个地方使用了转注,这是非常严谨的态度。当然,也有一点不足。我看了作者所列的“参考书目”,还有一些重要资料似乎也可以纳入,如《鲁迅生平史料汇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回望鲁迅丛书》等,尤其是《鲁迅生平史料汇编》至少得加进去。 胡少卿:作者在《随感与遐想:散说鲁迅》这篇里提出一个概念叫“小化思维”,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小化思维”是指,鲁迅在解释一些事情的起因时,会倾向于提供具体而微的细节。比如,鲁迅说自己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看了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而日本学者则考证说,他们不相信鲁迅辍学是因为看了幻灯片。按照黄坚的“小化思维”概念,这可能是鲁迅自己的一种文学化发挥;鲁迅本人在《藤野先生》里讲的“画血管”的故事,就是他的自供状:藤野先生说,你看你把血管画歪了,鲁迅说我这样画是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好看。这个细节揭示了鲁迅的思维方式:很多时候他在作品里那样写,是因为觉得那样写是一种比较好的文学选择。他会为了美而牺牲一部分真,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写。 黄海飞:黄坚对“画血管”这个问题的揭示很有启发性。他说画血管的故事可以说是自我展示或暴露,甚至是一个隐喻。包括下文他又引了周作人的话,说鲁迅好比是个盾,他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仅仅说鲁迅形象是多元化的,这还比较浅,黄坚还看到了鲁迅这样一种矛盾交织的状态。 胡少卿:鲁迅《野草》的很多篇幅都是在表现这种既这样又那样的矛盾状态,比如“影子”,徘徊于无地,又是在光明里,又是在黑暗里,如果完全光明了影子就消失了,如果完全黑暗了影子也看不见了,影子就是处在可进可退、左右为难的局面。鲁迅对自己的概括是“历史中间物”,“肩着黑暗的闸门”,这个形象也是这样,一半身体在黑暗里面,一半身体在光明里面。黄坚引用林彪打仗时说的话:“冲下山去,和敌人搅在一起。”他说他在写鲁迅的时候,常常想起这句话。鲁迅经常会反思自己,他不仅批判别人,同时也更深地去解剖自己。钱理群老师的鲁迅研究特别强调这一点:鲁迅挥向别人的刀子也更深更厉害地挥向自己。比如在《狂人日记》里,狂人批判这个社会吃人,但同时他会思考他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吃过人,“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鲁迅不会像一些特别有道德义愤的作家,只会刀口向外,他的自我解剖、自我分析、自我批判,使他超越了许多同行。 “现代超前性” 黄海飞:鲁迅其实很明了自己身上的黑暗,他下笔的时候不敢把心里的黑暗完全暴露出来。就像《药》里面,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加上一个花环,完全是为读者考虑,或者说为青年考虑。黄坚推崇竹内好的一句话:“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如果把鲁迅的形象单一化、凝固化,就丧失了鲁迅的丰富性、矛盾性。我上学期给学生讲《伤逝》,其中提到启蒙的问题,我们会发现鲁迅在那样一个大家都在提倡启蒙的时代,别人都在高呼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他就比别人想得更透一步。他开始反思启蒙和启蒙者本身,质疑涓生作为启蒙者是否合格,还有启蒙的有效性问题,即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我们有资格来启蒙吗?等等。最后发现是一个悲剧。 胡少卿:《伤逝》让人思考:给你自由,你能用好吗?让你自由恋爱,你能做好吗?鲁迅不仅启蒙,同时也超越启蒙、反思启蒙,意识到启蒙的限度。所以,在现代社会启蒙的神话破产之后,鲁迅仍然是有效的。 黄海飞:再讲一个例子,大一学生读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后也非常震撼,说完全没有想到。那是1919年的文章,100多年前鲁迅对于父母跟子女关系的思考,放在当下毫不过时。很多同学说现在许多父母还是原来那种观念,还是说子女是要报恩的这样一种态度。黄坚老师在书中提到鲁迅当下的价值,用了一个词叫“现代超前性”。鲁迅到现在仍然没有过时,可能是因为他揭示的是普世化的人性问题,是人性根本上的一些弱点。 胡少卿:鲁迅写的东西在以前被人们当作“国民性批判”来接受,但其中也蕴含了普遍性意义。比如说阿Q形象,很多国家的研究者发现他们国家也有阿Q,或者说他们的人性中也有阿Q的一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个人类的普遍性弱点,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弱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作家,他不仅展现我们自身的民族批判的一面,也展现人类性的一面。《野草》里对于内心深处黑暗、绝望情绪的描写,是一种人类共通的现代感受。他引用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说的就是人类其实活在一个极大的虚无里。鲁迅本质上是什么都不相信的,这种什么都不相信的绝望状态,就是现代人的状态。他和卡夫卡出生年相仿,他肯定没读过卡夫卡的书,但他像卡夫卡一样,使用寓言的方式写作,也写人的各种“变形”,也生活在一个神圣世界瓦解之后的那种空虚和黑暗之中。他们的现代情绪是相通的。 黄海飞:鲁迅自己一直都有世界视野。把鲁迅的作用局限于“国民性批判”,是把他缩小了。其实他是一个现代作家,“现代”两个字非常重要。 胡少卿:以前把他当成一个过渡期作家,他其实不是过渡的,而是在现代这个时段一直适用。鲁迅本质上是个象征派作家,他的小说、散文诗是带有象征含义的。他的小说其实都是些剪影,人物是一些寓言性人物,像诗一样。李长之在《鲁迅批判》里说鲁迅的小说本质上是诗,鲁迅本质上是个诗人、战士——后来到沈从文才真真正正变成了小说家的方式。比如说短篇小说《长明灯》,小说中的那个疯子完全是象征化的,他总是念念有词,“熄掉它罢,熄掉它罢”,眼睛里射出狂热。这个疯子是一个象征的形象,不是个现实人物的形象。小说整个的场景特别荒诞,跟卡夫卡小说很像,是寓言式的。 黄海飞: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长明灯》非常晦涩,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彬老师以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吹灯”到“放火”》,解读很精彩。您这么一说,这里面可能还有阐释空间。 (作者单位:胡少卿、黄海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记录整理:张德地)  胡少卿,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新诗,著有学术论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1978— )》、《驶向开阔的世界》等,诗集《微弱但不可摧毁的事物》,编有《顾城哲思录》《杀像之意:废名诗选》等,主编有“星空诗丛”等。 黄海飞,江西南丰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