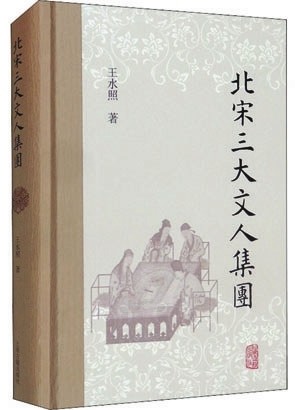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 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 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 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 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 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 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 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 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 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 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 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 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