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宁愿做台湾学界的“毒药猫”(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04 中华读书报 2009-11-04 记者 燕舞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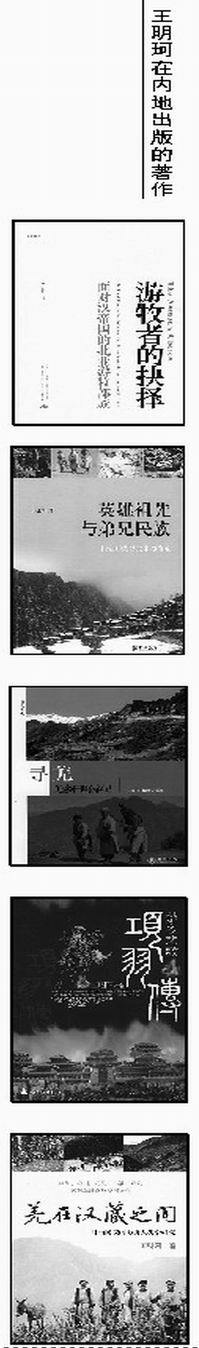 问: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研究情况。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王明珂: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历史语言研究所拥有约55位国际著名大学的博士(其中近半数是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又享有大量学术资源,目前的研究成绩是远远不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研院”其他各所一样,有十分严格完备的升等﹑续聘﹑评鉴办法,学术环境是不错的。然而,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以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在我的经验中,史语所并未有学术腐败的威胁。“中研院”倒有个学术伦理委员,近年来也没有处理过学术抄袭案件,这规范完全是建立在学者自重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匿名评审制度相当完备﹑彻底。有一年,一位审查者给我的文章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建议与批评,但我只得耐心答复。当时我是集刊编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召集人,也是本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人,但由于制度完备,我不可能知道审查者是谁。 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 问:我同意您以适当方式介入社会变革、表达现实关怀的主张,但如何守持学术本位?像内地这几年通过《百家讲坛》热播而走红的一些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难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被尊敬,一些二流学者通过和大众媒体的互相利用得以获取非常多的声望资本。我也听说您的同事王道还先生虽贵为岛内科普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但年年都面临着可能被解聘的危险? 王明珂:恪守学术本分难道只是教教书、写写与世无争只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文章吗?我认为,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以历史学强调台湾历史始于三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以人类学强调台湾的南岛民族特质与平埔族(平地原住民)文化。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若有一天两岸统一,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是否以上的遗传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都要重新来过,以证明台湾人便是中国人? 我认为,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以上许多学者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上所做的所谓“学术贡献”,正应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因学者自身的族群﹑性别﹑社会阶层等身分认同所造成的认知偏见。这些学者将学术卷入个人的政治见解与活动间,或更普遍地以重量级学者身分支持其学术见解,或以学术领导地位推动有政治目的之大型研究计划,以学术经费﹑奖金推动具意识形态的特定研究,都是学术灾难。 在台湾,以上学者毕竟并不多。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譬如有些学者已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田野方法与理论﹑词汇所创造的知识,让边缘人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原住民﹑少数民族等)持续边缘化。如在国际上,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人类不平等﹑剥削与迫害,但若不平等﹑剥削﹑迫害是民族宗教或文化的一部分则无可厚非——这多少是人类学的“贡献”。 我对《百家讲坛》的内容﹑这些名家出版的书不太了解。然而谈到知识常民化,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什么样的知识常民化?争论一些历史事实,而造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一个边缘人群的异类文化,让他们永远存在于现代与变迁的边缘?通俗﹑有趣,容易让一些观点﹑价值普及于群众之间;但也常因为通俗﹑有趣,让包裹着许多偏见的知识广泛传播。 王道还先生在史语所的边缘地位突显了一个学术世界的现实或荒谬:在世界学术圈——以一中国史专题来说,其核心大约是个数十人的团体——中发表﹑传阅﹑讨论文章才算是学术贡献,而王君所写的,让上百万民众、学生看的科学普及化文章不能称作学术贡献。 问:说到学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又想起《寻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这位传奇人物在史语所1928年创立时即受聘为助理员并迅速开始考察岷江上游的民俗,但1929年从川西回到史语所又迅速离职,1946年竟惨死于铲除鸦片的靖华县长任上(而且他还是回民)。黎光明当年是很不为傅斯年喜欢的,您后来把他和王元辉合著的尘封了74年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整理出版了,您会担心被视为“不务正业”么?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原报告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一个不具人类学背景的调查者所写的学术报告,是为了突显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特点。黎光明与王元辉描述的是许多活生生的个人;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个人”不见了,我们只见到苗族﹑藏族。黎光明与王元辉记载一些偶发的事件;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事件”不足为道,那只是浮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灭的光影。黎光明与王元辉不隐瞒他们在“落后民族”中看见的新事物,但人类学家刻意无视于此,而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寻找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后,黎光明与王元辉不掩饰他们对“边疆同胞”的偏见,但人类学者的偏见被学术包装起来,将造成我们今日对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台湾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与人类学界,我早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了。很早便有史学前辈公开说,“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便是他对“历史记忆”的了解。而资深人类学者也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人类学,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穿梭于各学科边缘,根据我的毒药猫理论,我是有可能成为各学科主流威权心目中的“毒药猫”的,如同RenéGirard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论中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是无辜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但我宁愿自称“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或我也可以自称“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武装”是说我认真研读各学科经典之作,那些(代表学术正统威权的)追捕者若无适当学术武装,就别惹我这“走私者”。 (特约记者 燕舞)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陈连山:作客中国新闻网解读春节文化
- 下一篇:[笔谈]传统的复兴与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