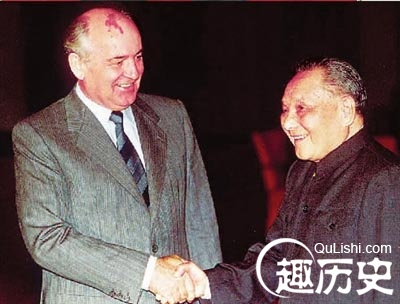|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