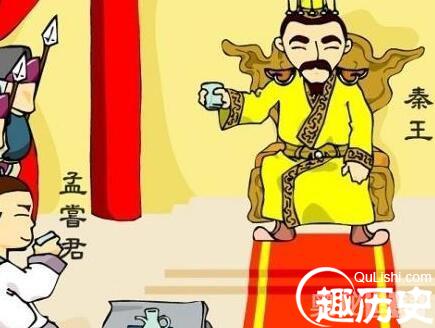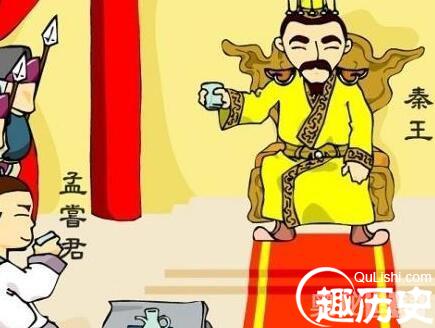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司马迁以平原君的故事为主线,辅以虞卿和其他一些宾客,而虞卿的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在最后的太史公评论中,也是对虞卿作了点评,可见平原君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的高。司马迁这样的叙事结构,既能够保证主要人物的故事完整性,又能够附带论述相关重要人物,而且从传文及评语的篇幅和评价上也能够看出传记人物在当时的地位。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网络配图
战国四公子传中所展现的社会风气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何以异哉!”这样的评论是可以用在战国四公子传当中的,总的来说,司马迁以其精准的历史眼光看到了天下之乱,从天子至庶人都是利的缘故,只不过战国时期四公子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司马迁在这里道出了战国时期趋利至怨的社会风气,其中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说明趋利是违背圣贤教诲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说:“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战国之士并未受儒家思想统治,其士风重名利,轻国家,更鄙弃大道。
另外,战国四公子传中还塑造了一些生动形象的女性,如举子文母、贪狐白裘幸姬、笑美人、盗兵符,她们形象、品行、善恶不一,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却为叙事的流畅生动,为突出战国四公子及宾客士人起着重要的衬托作用。在战国四公子传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社会阶级极度不平等,《史记·平原君传》有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谷,余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可见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司马迁并没有评论,却把它放在传文正文当中以平原君宾客之口说出,更见真实。
战国四公子传中最突显的世风之一是重禁忌。《史记·孟尝君传》:“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索隐引《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首先,孟尝君信禁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折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命”与“户”的差异所反映出来的天命正统思想还未统一,这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真正嵌入人们的思想。这样的禁忌之风是在不断发展演进当中的,至两汉之际,社会风气更加禁忌谶纬化,在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当中随处可见对于先秦以来社会风俗的禁忌之盛,而到了魏晋时期就又转型,似乎魏晋风流都不要禁忌了,其实是脱离政治的一种异化表现。
战国四公子传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风气是养士之风,这对于后来我们理解士人的演变很有帮助,在西汉、东汉时代,还有战国养客的一些影子,而三国时期更是盛行,不能忽视某些文化因子的传承影响。《史记·春申君传》中春申君上秦昭王书可算作是战国时期贵族文辞的代表。此篇文章有几个特点,其一,开篇点题,主旨明确。文章开始即说明秦、楚两国的重要性,以及秦欲伐楚的消息,紧接着要求改伐楚为善楚的上书目的。其二,对称之美。
文章丰富的字句相等作对,有段段之间相对,更有事例正反相对,这样所营造的对称之美既丰富了文章气势,又达到了简洁明了之效。其三,巧于论辩。文章作为上书言事,必然要明理通达,而春申君所说正是以谨严精密的逻辑力量取胜。不唯有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传体现的就是战争背景下养客之风,宾客为了迅速得到主人的赏识就会说一些异于常规的话,而在权谋论辩当中就必然是以论说为本,通过逻辑严谨、排比渲染、言辞精当的话展开争锋,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语言风格。
《史记》战国四公子传真实生动地塑造了四公子及宾客群体形象多性恶乏善、重权术心机、偏江湖义气的群体形象,司马迁因人而异直言或赞或批。《史记》战国四公子传看似平静的语言背后都是热烈的情感,只有在太史公曰中才会直抒胸臆,司马迁采取的叙事风格,既有利于历史叙述的散文化,又能将表情达意深刻化。《史记》战国四公子也描绘了当时的世风、士风,包括风俗,这能激发《史记》带给我们的史鉴意义。
战国四公子现象  网络配图
战国七雄中,无所谓“公子”的,只有秦、燕、韩三国。燕、韩国力尤为弱小,似乎不具备产生此现象的条件,而秦国为什么没有“某君”呢?所谓的公子,无非是由于国君碌碌无为,代替国君执政而已。齐国自湣王后国力每况愈下,退化成一个二流强国;赵国仅在赵武灵王时有所崛起,赵惠文王是一个平庸之辈,而赵孝成王就是赵国灭亡的掘墓人,此时具有雄狮之心的平原君应声而出,这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楚国的楚怀王、顷襄王、考烈王极似查理一世、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二世三人,一个比一个昏庸,楚国成为六国第一个因战火而迁都的人。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背景下,若再无一两个极有魄力的人力挽狂澜,那么秦之统一也太轻松了。反观秦国,战国后期的国君更容易为读者记住。何者?
秦国的战国国君大都个性鲜明,建树独特。国君一人就能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还需要什么“君”干什么呢?或许有些人认为这些公子影响了国家的前途,其实不然。他们做的仅仅是使社会不退步的工作罢了。然而就这个也鲜有人能做到,或者是根本没有。赵国的平原君是赵国灭亡的溯源。
众所周知的长平之战竟是以秦韩之间的交战为开端,平原君缺乏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贪图韩国的土地,却使赵国精锐尽失。诚然,败仗是赵括打的,然而即使是廉颇参战,在前期作战中也损失了5万士兵,被迫采取防守措施。如果再相持下去,不善于打野战的赵军只会失败。平原君的这个措施实在荒唐。
那些君子们只会收养门客,却缺乏把他们合理分配在各个岗位的能力、观念,更别提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了。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国君听君子的,君子听门客的,每个人都在培养自己的势力,缺乏自上而下的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远非秦国敌手。
如果上述还缺乏说服力的话,试比较韩赵两国。韩国起初连与赵国相比的资格都没有,领土、士兵只及赵国一半,而赵却因平原君的一着不慎,丧失了与秦相比的可能性,于韩灭亡两年之后灭亡。这是怎样一种滑稽而可怕的现象。战国四公子们若看到自己倾注心血的国家数十年后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不知做何感想。看来选对治国的方法至关重要啊!
成语里的“战国四公子”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其他诸侯国为了对付秦国,竭力网罗人才,因此养“士”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他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不少成语都是从有关他们的故事中演化而来的。
狡兔三窟  网络配图
狡猾的兔子准备了好几个藏身的窝。比喻隐蔽的地方或方法多。有个叫冯谖的人投奔了孟尝君,他住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事都不做,孟尝君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热情招待着冯谖。终于有一次,冯谖主动要求替孟尝君到他的封地薛地去讨债。但是,冯谖到薛地后不但没跟当地百姓要债,反而还把债券全烧了。薛地人民都以为这是孟尝君的恩德,心里充满感激。
后来,孟尝君被齐王解除了相国的职位,前往薛地,受到薛地人热烈的欢迎,孟尝君这才知道冯谖的才能。一直到这时候,不多说话的冯谖才对孟尝君说:“通常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洞穴,才能在紧急的时候逃过猎人的追捕,而免除一死。你现在却只有一个藏身之处,我愿意再为你安排两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于是,冯谖又用自己的智慧为孟尝君做了两件大事。之后,冯谖对孟尝君说:“现在你有三个安身之地了,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
鸡鸣狗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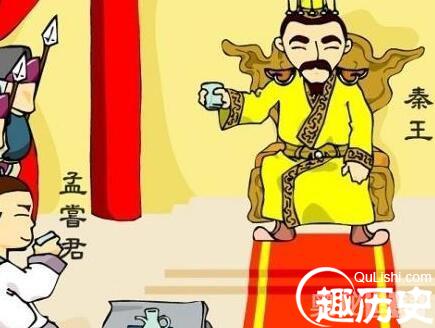 网络配图
指微不足道的本领,也指偷偷摸摸的行为。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想让他留下当相国。可秦国的大臣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齐国王族,怎么会真心为秦国办事呢?”秦昭王觉得有理,便下令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关起来,想找个借口杀掉。孟尝君得知后,派人去求秦昭王的宠妃。宠妃要孟尝君将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给她做报酬。
可孟尝君已经把那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就在这时,有一个门客说:“我能把狐白裘找来!”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便将狐白裘偷出来送给了宠妃。于是,宠妃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送他回齐国。孟尝君可不敢再等,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逃走了。到了函谷关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