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炎武,被梁启超称作是“清学开山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最早即是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的概念,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这些圣哲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不说主观,只说客观,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时代,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所读主要是教科书与教辅材料,用来应付考试,而一定程度的博览几乎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借钱买来二十三史,才有机会认真读史,这是那些书香世家决不会碰到的尴尬情况。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历五年,他还在读《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这些书却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毕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创建湘军,日事戎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认真读书。常言虽说湘军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说的是激励将士,晓以大义,不要以为参军就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应有一些精神追求。作为统帅,每天要筹款,要指挥作战,要应付各种关系,不可能认真读书做学问。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只要长期在军中,还能做出大学问的,基本上是没有的。还有独学无友的问题。幕府的宾客,究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切磋学问的时间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没有深造学问的环境。 第三,个人兴趣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发点却不全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他真正爱读也常读的,仍然是诗文。他的学问虽不能在学术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学的成就,在近代文学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说他开创了湘乡文派的。我们看看各种文学史,再看看各种学术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炼八事 曾国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学,读书固然重要,但不仅限于读书,还要治事,还要修炼。上班打卡就不说了,说说八小时以外的修炼工夫。去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增订《曾国藩全集》,收入旧版所没有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部日记就记载了不少如何修炼士大夫之学的内容。 这部日记是一个课程表。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学家讲究每天都用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我们从日记看曾国藩静坐,往往不过是打了个盹,而非静坐常思己过,或静坐以游太虚。如此则违背了静坐的宗旨,他常会自责。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大致分两种,一是为朋友写的序跋,偶也自定题目写上一篇,还有一种,则是奏折。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办公,其时他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对客,一是在家里搞接待,一是出门拜谒各界贤达。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几乎每天都要出门拜会他人。对客既如此频繁,必然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其他几项,日常生活是绝不轻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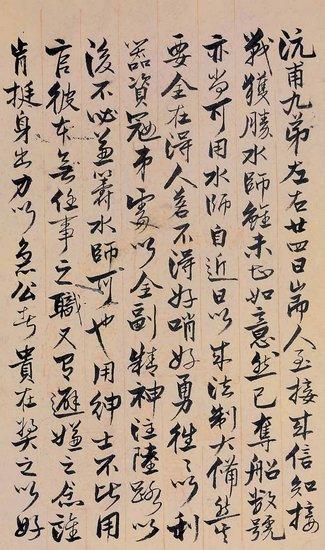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 与对客性质差不多的是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寄自北京的家书很重要。要了解政治中心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外省尤其是乡间的人来说,日常只有这个途径。家书读者也不限于亲属,只要其中没有特别隐密的事或者国家机密,家书是要拿给朋友甚至地方官绅传观的。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尽管拟定内容轻车熟路,但因为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直至逝世前夕。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幅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自曾国藩纪念堂。 尝试解说数语。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