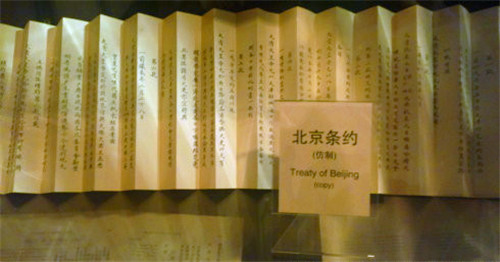 《中法北京条约》中第六条款有一个要求是这样说的:“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但比较这一条约的中法两种版本,我们会发现,这一条款只出现在中文条约中,作为标准的法文条约竟然没有这一条款,这也让这一要求没有任何依据,只能是无用的“废款”,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中法英美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并没有承认这一条款的问题,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措施。 一、早已知情的中法政府 教会在华置产权经历了从口岸到内地,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并与居住权、传教权等息息相关。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外国教会先后获得通商口岸的居住、租买房屋和租地建房权,中俄、中法《天津条约》还给予传教士持证赴内地传教权,根据“最惠国待遇”,各国教会分享这些权利,但均未获得在通商口岸的买地权及内地置产权。从条约层面讲,传教权和居住权、置产权之间存在不平等。从实际情况看,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居住和置产不可避免,因此获得内地居住和置产权变得迫切,并且也想通过买地获得所有权,为教会建立永恒之基。这一愿望在上述中法《北京条约》中文版第六款中得以实现,这一突破性条款不仅将置产权从通商口岸扩展到内地,更增加了购地权。同时也将传教士特殊化,其他外人并不享有内地置产权。虽然还未提到内地居住权,但由于清政府在实际中默许了传教士到内地居住,也没有引起中外争议和交涉,有学者认为居住权是附属传教权自然而有的。 如前所言这一条约依据并不合法,因此严格来讲传教士并无内地置产权。但1860年后各国传教士以此为据,在内地租买房地、建堂造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当时以奕为首的中方不仅未发现中法文本间的差异,对“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也未引起重视,在给咸丰关于条约谈判的奏折中对此只字未提。而此后数年该条约下发各省后,各地都是根据第六款处理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买地的,比如1861年山东巡抚清盛就依据第六款办理报请定夺,总理衙门予以同意。而总理衙门在为天主教传教士盖印的护照上也有“内地来去居住,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字样。 对于条约文本差异何时被发现,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1.顾维钧认为1869年有人查出了中法文约本间的差异。威罗贝(W.W.Willoughby)、史维东(A.R.Sweeten)均支持这一说法,而细读顾书可知他是指1869年英国政府知晓这种差异。王中茂也认为这一差异是在1869年被发现,并提出是由总理衙门法国股工作人员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核查条约时发现的,可是文中并未注明这一说法的史料来源。2.吕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内的《查核法国条款底本》提出同治七年(1868)之说。当时为修约总署派人检查中法条约,由赫德及总署法文官发现了法文原本没有该款。但吕先生根据《查核法国条款底本》首页所列奕、文祥、崇纶、宝鋆、董恂、徐继畬、谭廷襄职衔推断,只能说明总署最迟在1868年知晓,以前是否已知不得而知;3.季压西、陈伟民则据赫德日记提出最迟在1864年6月总理衙门已明了法国在其中的欺诈行为。 第三种意见将发现提前到1864年6月,但其证据还有进一步可议的空间。查阅日记,赫德在1863年7月16日、17日、18日、20日、21日的日记接连提到和总署董恂一起核对中法条约的中法文本并核对完毕。日记未点明何约,季、陈两先生认定是《北京条约》并提出赫德很容易发现问题,但不知他是否告诉总署官员。按常理核对范围肯定包括《北京条约》,不过日记并未明确提到发现了差异,而董恂是否发现也不得而知,当然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其次该书引用赫德1864年6月11日日记赫德与文祥谈话,中文版为“法国条约的原件已经制定,条约第11款在法文原本中并未见到传教士在内地有‘购地与建造’的任何权利。文祥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遇有适当的机会,将从这一点得到好处”,作者将原文第11款误写为第一款,并认为是第六款之误,而得出1864年6月之说。不过日记未指出具体条约名,译者注释是《中法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约》,但不知何所依据,查该约11款确实谈的是租地问题,日记英文版也确是第11款,但疑问在该约是1861年签订且天津紫竹林是通商口岸中的租界,何以会扯上内地,殊不可解。结合日记上下文,尽管季、陈的逻辑稍显武断,但其结论可能是正确的,日记所谈应该就是《北京条约》第六款,因为两人谈论的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内地引发的一系列麻烦,特别是贵州教案给文祥带来巨大困扰,所以恰合语境,鉴于赫德日记手迹存在辨认困难,有可能是罗马数字Ⅵ(6)与Ⅺ(11)之误,不过这一点有待到英国查阅日记原版。 但笔者的另一重大发现恰恰可与此相互印证。同治三年(1864)十月一日福建巡抚徐宗斡向总理衙门报告福安天主堂被毁案,徐指示地方官赔偿原地价,但不同意另买地基建造,理由是之前英国牧师在漳州买屋建堂,总理衙门曾指示“漳州系属内地,英国条约十二款亦系专指通商口岸租地买屋而言,并无内地字样,应饬按约禁止”,因此认为“今福安亦系内地并非通商口岸,与漳州事同一律”。徐以英国条约论法国之事遭到法国教士的强烈反对,该教士直言英约与法约不同,根据法约“在内地无论何处均可买置建造堂屋”。领事也以此向闽抚伸陈。十月十一日(11月9日)总理衙门在给闽抚的回复中写道:“该教士引法国条约,谓可在内地买置建造堂屋,查法国条约第三款载明以法文为正,该领事细译法文,便可知悉,并无此语。”由此可知,总理衙门此时不仅知道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为法文本所无,也清楚中法文本有争议时以法文本为准。 而同年三月直隶总督请示法国传教士鄂荅位到大名府建堂一事,总理衙门的指示还是“今鄂教士属自行租建,查与法国条约第十款和续增条约第六款相符,原可准行,惟必须两厢情愿”。同年四月四日(5月9日)总理衙门在给户部的文中写道:“法国条约续增第六款,有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之语,是只有各省字样,并无内地字样,只有传教士字样,并无外国人字样。”同是天主教传教士到内地建堂,三月总理衙门的指示为符合《北京条约》第六款,四月行文也明确承认第六款有“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而到十月时却明确指出法文本中并无该条,由此推断总理衙门是在同治三年四月到十月间获知文本差异的。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肯定总署确实是在赫德和总署法文官核对中法文条约时发现这一差异的,而时间应该就在1864年6月前后,最晚到11月9日。此后这成为总署内部公开的秘密,比如1865年7月9日赫德日记提到:“我们向他们谈外国人的善意等等,他们提出了《法国条约》,指出条约的中文本同外国文本有许多不同之处”。第六款作伪成为赫德的中国同僚奚落他的证据。 然而总理衙门并未将此公之于众,也未向法方提出交涉。1864年法国田鲁斯主教在会稽买地建堂,会稽县令报宁绍道台请上海通商大臣李鸿章定夺,十一月三日(12.1)李以《北京条约》中只有“各省”并无“内地”字样,判定在通商口岸之外买地建堂违禁。会稽县据此将卖地民人拘押,并照会宁波韦副领事,韦一面以田所领执照内有在浙省来去居住、买地建堂自便文句,且有恭亲王和法使大印回复,一面报上海总领事请公使定夺。法驻沪总领和法使柏尔德密(Jules Berthemy)认为“各省”指内地毫无疑问,并向总理衙门抗议。平心而论,李以咬文嚼字来退拒法方是站不住脚的,但从反面说明李以及会稽县令、宁绍道台等都不知第六款文本差异。而总署在明知第六款作伪的情况下并未借此契机与法方交涉彻底解决,本案由地方上升到国家交涉后,最终以中方的妥协而告终,总署的理由是“内地建堂由来已久”,只要载明卖作本处天主堂公产,“仍系中国之产,自应准其办理”。 总署之所以在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如此答复浙江,是因为在正月二十五日(1865.2.20)与法方达成协定:“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史称“柏尔德密协议”。会稽案中法方争辩的依据是中文版第六款最后一句,可见其已知晓文本差异。但法方不会如实告知,而是诱使中方另行承认,除强调教会乃厉行善举外,主要是认为教堂产业非个人私有,而是教中人等公共之业,所以仍为中国人所有。这似乎给了总署一个顺势而下的台阶,因为总署最担心的是中国之地沦为外国之地,所以进而要求契约内声明卖作教堂公产的同时由奉教中国人出名,但被法使以中国教徒多不可靠拒绝,仍要求以教士出名。各不相下,最后妥协各不出名,以卖入本处公产议结。只要还是中国之地,总理衙门就答应了,当然总署未向法方理论,还可能因篡改的是中文本,总署已获皇帝批准通行在案,教士进入内地置产已成事实,所以不便再与法方交涉再生事端。 法方利用会稽案契机将原本非法的权利合法化,不知是否就是会稽案争议导致法方明了第六款差异,因未能看法文资料,在会稽案前法方是否及如何知晓文本差异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1860年后法国公使为传教士发行护照,照内即有第六款最后一句,比如1860年12月白德理护照载明“传教士白公在四川省内来往传教居住,勿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前述田鲁斯主教类同此例。而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哥士耆照会同样表明根据第六款,“主教诸人自行价卖地址,建造天主堂公所,原可听其自便”。而三月一日总署回照中也指明“条约内载于言明查还旧堂之外,虽有任其自行租买田地建造之语”。三月八日法使再复“任其自行买建,原系和约所定”。可见法方是非常有可能先前已知文本差异的,只不过会稽案发促使法国不得不寻求彻底解决,而这种解决是明知文本差异的刻意而为,在下述法使施阿兰(A·Gérard)话语中进一步印证。 “柏尔德密协议”后30年,第六款悬案在清廷内部未再起波澜。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8.8)张之洞上疏总理衙门,明确提出传教士经常援引的第六款“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在法文本中没有。张是从美国议院所刊各国交涉政书中发现的,该书中有一份美国公使1886年10月6日报告,报告言明第六款的中法文之别。张将此份报告译文上报给总理衙门。此外还援引《英例全书》中有关购产来历不清、立契约不法等的相关规定,并提议总理衙门根据上述事实与法使商议限制教堂内地置产之法。张上呈的美国报告在当时影响较大,《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中也存有该报告译本《节译美国公使致外部公文:论传教事》,翁题有“传教事庚申内第六款华文与法文互异”。也许翁是经张报告知晓此事的,因为时年翁为军机大臣。另该报告曾有单行抄本流传。 面对此份上疏,总理衙门不得不做出反应,八月九日即照会法使,言明第六款中法文有别,根据条约传教士无权在内地置产。对此法使施阿兰回复:“中法各文两歧一层,本因当年深知情形,且恐两国文字因出两歧,或致将来误会生事,正所以法国驻京大臣会同总理衙门,于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另行商定专章之故,所谓柏大臣章程是也”。该公使直白地承认了1865年另订协议的真实用意,意在用“柏尔德密协议”取代第六款,通过外交交涉使不合法之权利合法化。此后当中方再指责法方无权在内地置买房地时,法方总以“柏尔德密协议”论之,而不提及第六款,这一点所带来的影响是总理衙门始料未及的。 在照会法使前,总理衙门曾于七月初八日分别致函美国公使田贝和英国公使欧格讷询问张之洞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公使之报告与英例全书之内容有无舛误。七月十二日田贝回函则未对张所译之内容正确与否作直接回答,只言“但系熟谙英汉文者,均可将全文译出”,但却指出中国既然已与柏大臣签订协议,认明了教会在内地置产权,现在如欲改之则为“有意背章也”。田贝实际上是承认了张所译之内容是正确的,但作为第三方不便对此明言,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在问题的症结已不是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的差别,而是“柏尔德密协议”。英国公使是否做出回复不得而知,《教务教案档》中未见相关记录。 法方以“柏尔德密协议”巧妙地为天主教解决了内地置产问题,新教传教士依据“最惠国待遇”成为第六款的受益者,而这一条款又被证明是缺乏条约效力的,新教传教士在知晓真相后态度是复杂的。卫三畏(S.W.Williams)认为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在条约中文本中擅自增加内容的行径是不值得的,同时这一增加的内容也是无效的。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也认为法国这一行为没有必要和意义,他认为1846年道光皇帝颁发了给还教产的谕旨,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可以重新回到内地了。也有传教士认为中方对此也有责任,丁韪良(W.A.P.Martin)就指出篡改的文字是中文的,总理衙门没有理由抱怨受到了欺骗。李佳白(Gilbert Reid)更是认为中方接受的是中文本,只有当中法文本产生争议时才以法文本为准,由于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条款没有遭到中方拒绝,没有产生争议,因此不能认为这一款是无效的。 清政府在知晓条约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允许天主教到内地置产,并在实际中默许了新教传教士享有同等权利,这样的举动似乎令人费解。张之洞曾对此作出解释:“其添设分堂医院学塾等所皆系善举,并非为牟利起见,故格外通融办理。”曾为传教士后担任驻华公使的何天爵也支持这一看法,他指出中国政府没有对传教士进入内地居住和开展工作提出官方抗议,是因为认识到传教工作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正是认识到传教工作的慈善性质,传教士成为有别于其他外国人的特殊团体,得以深入内地置产建堂,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按约被限于通商口岸。 二、英国的态度:努力限制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的“造伪”以及“柏尔德密协议”的出台也使得英美在对待教会内地置产问题上显得更为复杂。相较而言,中英条约中关于传教的专门条款很少,且即使到1902年《马凯条约》,英国传教士在华都未能获得内地置产权,特别是其中的购地权,如果要进入内地置产,只得通过“最惠国待遇”援引法国条款,但总署早期并未同意英方援引,比如上述福建漳州案内,所以不断有英国传教士请求获取与法国同行相同的权利,但英国政府对此却并未予以积极配合。 从英国第一任驻北京公使卜鲁斯(F.W.Bruce)开始,这项政策似乎是一贯的。进入内地置产传教,同样是英国传教士的向往,他们时刻关注条约权利的进展,当发现他们的法国同行已经突破港口,他们也纷纷追随其脚步进入内地,但他们更希望中英条约正式给予他们这种权利,不过这种希望被驻华外交官扑灭。据1864年6月17日赫德日记记录,当日他与公使谈话,布鲁斯表示他不会为传教士的利益来运用他的官方影响力,但会给予他们与其他英国国民同样的保护,因为他相信如果中英再战,那将是内地一些传教纠纷引起的结果。很显然,他受到法国悲剧的刺激,1856年马神甫进入内地被杀事件是中法战争的导火索,而1861-1862年贵阳教案、1862年衡阳教案导致中法关系再度紧张,他不想英国步法国的后尘。 而在他知道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作伪以后,更有了拒绝传教士的理由。1864年6月19日赫德日记载英国公使馆职员柏卓安(J.Meleavy Brown)来访告知,厦门传教士巴恩斯缠着布鲁斯,根据中法《北京条约》英文版(应该是翻译自中文版——笔者)第六款,要求正式申请在内地拥有土地。公使向巴出示法文原本,他大为惊讶,因为看到了法文本没有给予拥有内地土地的权利。可见,英驻华使馆已知第六款故事,但不知从何而知,时间上与前述赫德、总理衙门不谋而合,可能并非巧合,鉴于赫德与英使馆间的密切联系,也许是赫德转达的。不过尽管英国外交官不欲为教士谋取内地置产的条约权利,但也没有禁止他们进入内地。 而布鲁斯的态度为其继任者所延续,当然有一些变相的波折。1868年正值《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期,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曾写信给外交大臣斯坦利(Lord Stanley),建议借修约之际在条约中加入允许英国传教士到内地像在通商口岸一样拥有居住和购买土地的权利,这一提议于5月2日由斯坦利告知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而8月又发生了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在扬州租房引发的冲突,阿礼国不得不正视该问题,9月11日他致信斯坦利:“我并不认为需要增加新的条款赋予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购买土地和居住的权利。关于这一点中法条约的第六款已经非常明确了,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赋予法国传教士的权利也同样地赋予英国。……但从传教士的安全、维持和平与秩序、选择在何处定居便于管理来考虑,将这一条约权利付诸实际是否明智与谨慎,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见阿礼国认为从条约权利而言,英国传教士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法国一样享有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但从实际出发,他并不十分赞同将此权利付诸实际。可能受回复的影响,12月1日斯坦利的答复是:“关于在全国各地购买土地和居住的权利,英国传教士要谨言慎行,尽全力避免冲突的发生,如果当地政府拒绝承认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不要强求应搁置争议,向驻华公使投诉。如果发生了迫害传教士的骚乱,公使要向北京的官员控诉,要求惩罚肇事者并赔偿受害者”。斯坦利和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传教士有内地买地权,但似乎并不鼓励传教士进入内地去实践这项权利,担心引发冲突,不过仍然会承担保护传教士的义务。 但1868年底斯坦利去职,克拉伦登伯爵(Lord Clarendon)出任外交大臣,12月18日他转来伦敦浸礼会咨询件,该会在山东栖霞因捐产而发生纠纷,特来信询问根据条约有无租买房地及接受捐产的权利。1869年3月12日阿礼国进行了详细答复:1.按条约规定,英国人民不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租赁、购买或以赠送的形式接受土地或房产,以供教会或其他目的之用,但对法国是例外。法国传教士根据中法条约第六款中文本最后一句获得内地租地建房权,但这一句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而且根据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以法文本为依据;2.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当局已经采取新的方法(指柏尔德密协议)同意天主教在内地获得产业;3.法国获得的这种权利英国传教士经过抗议是有可能获得的。因为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当局不可能拒绝英国享有法国一样的权利,但传教士到底能否成功在各地置产与当地反对与否的实际情况有关;4.英国政府应否为新教传教士求得与法国政府为天主教会在内地获得的相等的特权问题,应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5.传教士已经进入内地,一旦发生纠纷英国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但希望传教士能够用智慧和节制规范其自身行为,减少与中国民众的摩擦。阿礼国的态度可简单地总结为:无条约权利,但仍可争取,争取与否有待于政府决定,但对传教士进入内地置产持谨慎态度。 阿礼国报告明确表示英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不享有任何置产权,并指明法国的条约权利也有问题。而他在1868年9月没有提到这一点,这种态度的变化,很有可能是因为阿礼国直到1869年才知晓第六款搀假之事,顾维钧先生就持这种观点。1869年5月19日克拉伦登在得知法国条约的真相后,明确表示不会以中法条约中文本中添加的几个字为依据为英国传教士争取与法国同样的权利,还指出英国传教士不享有超出一般英国人民的任何特权,甚至指示阿礼国可警告传教士倘若他们妄想寻求更大的特权后果自负,“不能指望女王陛下政府方面为救护他们而采取任何行动或强制性的干预”。这一态度表明英国政府的立场再次退却,不但不支持传教士寻求的条约权利,且较布鲁斯的态度更为严厉。 克拉伦登随后就此在英国上议院演说,英国各大报刊也予以了报道,引发了教会方面强烈的反响。先是1869年7月14日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包括伦敦会的艾约瑟、德贞和圣公会的包尔腾、顾惠廉联名致信阿礼国,对克拉伦登和阿礼国所持的观点进行逐条辩驳,不赞成他们所坚持的将教会限制在通商口岸的观点,也不承认传教是导致中英冲突的根源,而对法国条约的作伪,他们的解释是“虽然法国条约的法文本没有订明这一条文,同时,从政治上的原因考虑,谁都清楚清政府是乐于撤回这一特权的,但事实上法国传教士业已获得这一特权”。接着传教士又借用《北华捷报》等公共舆论表达不同的意见,香港维多利亚教区主教柯尔福也致信质疑克拉伦登:倘若天主教在法国保护下深入西南,而禁止圣公会传教士进入内地,难道是公平和正当的吗?甚至汕头领事阿查理也认为教会的发展有利于商业利益,其所到之处会为商人、旅客和官员铺平道路。圣公会甚至认为克拉伦登上任后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逆转,斯坦利和阿礼国先前是支持传教事业的,但被继任者克拉伦登否决,后者坚持“除了天津条约第八款外,中英间没有其他特别的条款可引证”。 但这些反对声音并未动摇英国外交部的态度,12月13日克拉伦登回复柯尔福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深信其他的政策都将危及维护本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并使女王陛下政府的人民在该国的巨大商业利益陷于困境,英国政府方面惟有采取克制和和解的政策始能获得这种利益”。克拉伦登和阿礼国站在同一战线,部分受到他报告的影响,阿礼国一直向伦敦表达这样的观点:中国官绅对传教有强烈的反对情感,各地反教即为证明,所以必须限制传教士在条约允许以及领事能够保护和干预的范围内,这样不但传教士能够安全的工作,“不断威胁两国关系的根源亦将断绝”。所以他视传教为可能导致两国冲突的根源,这必然会危及英国在中国的更大利益——商业利益,总理衙门在来信中也谈到传教问题“与商业利益的关系极为重大”,所以必须谨慎应对,“因为商业是一个伟大而又强大的国家所依靠的有力支柱”。正是这些成为了英国官方的主导意见,并支撑其政策走向强硬,而教会在各地引起的纠纷加剧了这种观点。 在谋求添加内地置产权失败后,英国教会不得不在既有的条约上做文章,因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二款“各口并各地方”描述,传教士想从中寻找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1870年4月7日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向外交部请愿,认为“各地方”可解释为内地。但并未获得外交部的认可,7月14日回信指出:“联邦政府并不打算接受你们所提出的关于条约第十二款中‘各地方’的延伸性解释,否则将交易限定在通商口岸就变成多余了。不管法国政府是如何声称其所代表的传教士的利益,联邦政府不认为传教士与其他英国公民相比享有任何特权。”外交部的回复打破了传教士的最后一丝希望。显然不能将“各地方”解释为“内地”,否则依据中英《天津条约》早已享有内地置产权,就不会有前面的争论了。 随后继任驻华公使威妥玛(T.F.Wade)向各地领事发布两份通知,对居住和置产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指导。第一份通知于1870年9月20日发布,首先向各位领事转达了上述外交部对苏格兰圣经公会的回复,即英国传教士只享有居住在通商口岸的权利,不享有其他特权。其次,有关通商口岸的区域界定,由领事根据各地情况自行判断,总原则是“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领事对其所控制地区负责并进行保护,不要随便批准英国人到遥远的、孤立的地方永久性居住。”这一规定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政策,强调传教士不但最好不要去内地而且只能限定通商城市的有限区域。最后针对传教士已深入内地的事实,威妥玛指示“尽管我现在非常明确的要求你坚持不要让人们在远离你的地方获取土地或房屋,但我认为现在突然让英国教会放弃已在内地获得的传教点也是很不明智的。”12月7日外交部批准了威妥玛上述通知的内容。对传教士而言,这表明英国官方想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通商口岸,这对传教而言是不利的。 1872年2月20日威妥玛再次向各地领事发布通知,这份通知不仅再次向领事强调不要让传教士到远离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置产,还进一步建议传教士把在内地的产业置于当地人名下,并言明领事不对在其保护和控制范围之外获得的房产或土地提供支持。这份通知也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根据英国圣公会的档案记录他们在1872年6月7日收到了外交大臣的来信,信中转达了威妥玛给领事的通知并建议传教士遵守威妥玛的要求。威妥玛两份通知自发布后没有撤销或修改,尤其是让教会将内地房产置于当地人名下的做法,引起传教士们的不满。圣公会曾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修改威妥玛的政策,但未获成功。 英国政府对教会内地置产不仅受到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差异的影响,也与19世纪60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然而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并不如意。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使英国意识到战争代价太大,因此决定放弃武力威胁。而太平天国运动也大大影响了英国的在华利益。对此,英国转而寻求通过一种和平的环境和稳定的政局来维系其长久利益。为此,英国采取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减少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接触,这样就可以尽量降低破坏两国和平的摩擦。英国对在华传教士在内地置产的态度,是与英国政府的这一原则一脉相承的。 1902年中英商讨《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之际,英方曾想借此机会为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所有英国公民获得内地居留和置产权,但这一提议未获中方同意。虽然英国传教士一直没有获得内地置产权,但其并未遵守外交官的决议,1860年以后传教士深入内地租买房地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三、美国的态度:积极保护 在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签订以前,美国传教士也只享有在通商口岸居住和置产权。美国官方在讨论置产问题时常常从居住权出发,这是因为居住与置产不仅息息相关,更是置产的基础。这一点在条约描述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美国民众是在享有居住权的基础上才被允许租赁房地的。对于居住权,何天爵曾这样总结:是否支持传教士在内地居住对美国政府而言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支持任何阶级或职业享有特权,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以公民为基础提供保护。对此历任驻华公使的态度较为统一,即虽然根据条约美国传教士无权到内地居住和置产,但美国政府有尽力保护公民的义务。 和对英国一样,总理衙门1860年代早期并未同意美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1864年传教士梅礼士在山东登州租屋,本来1858年登州已被开放为口岸,但因不便停船于1861年改设烟台,所以登莱青道报请山东巡抚请总理衙门定夺,山东巡抚认为登州非通商口岸,按约不准租房,总理衙门同意,回复山东根据中美条约十二款“所有准租民房,系指通商口岸而言”,“今美国教士欲在登郡租房,既非通商口岸”,“核与条约不符”,并以此答复美公使蒲安臣。蒲安臣只得解释登州本来是口岸,不得已被烟台取代,“今洋租赁登州地方已历几载,非背条约”。可见总署根据中美条约并不同意美国教士有内地置产权,而美国公使也承认这一点。 所以美国传教士也与英国同行一样不断寻求法国条款的美国化,1867年美国传教士也曾向驻华公使请愿,希望借修约之际增添与法国条约第六款相似的条款,让美国传教士在各省获取租买土地建造的权利。自然美国公使未能同意。但事实是美国传教士早已突破口岸进入内地,比如在杭州,到1872年杭州置产案爆发时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思敦(M.H.Houston)、郝理美(Ben Helm)已在杭居住数年。案发后美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明确指出美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之外没有永久居留权。当然他也承认要求传教士撤离不合时宜,仅能尽力保护,但不希望传教士在内地扩充原有的机构或新增传教机构。镂斐迪公使还指出以法文本并不存在的条款为依据而享有内地置产权是不妥的,所以美方也知晓了第六款的作伪之举。 虽然没有条约依据,但美国官方并不反对传教士通过自己的努力享有与法国传教士同样的特权。1874年12月28日公使艾忭敏(B.P.Avery)在回答福州领事戴兰那(M.M.De Lano)有关传教士在内地居住和持有房产问题时就指出传教士可通过自己的谨言慎行享有这一特权,还声明本公使不会妨碍他们已有的冒险行为,也不建议他们从已获得中国官员允许的地方撤退,并不会阻止在必要时对他们提供合法的帮助。该公使并进一步提示传教士如果做了任何违背法律或超越条约权利的事,仍可依据治外法权要求由本国政府的官员来处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美国传教士可援引“最惠国待遇”认为自己享有与法国一样的权利,但法国传教士在内地租买田地也是缺乏条约依据的,首先第六款最后一句没有法律效力,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说“柏尔德密协议”不是条约,只能算清政府给予法国传教士的一种特权,因此对美国传教士而言,只能说是他们自己争取到的特权。艾忭敏公使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国务院的完全赞同和支持。 更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885-1898年出任驻华公使的田贝(Charles Denby)报告,1886年他给国务院的报告明确指出按约传教士和商人一样“仅得在通商口岸买地造屋居住”,他提到传教士曾向其援引法国条款,1885年前任杨约翰致国务院文也曾援此条以为教士可以住内地之例,但他强调中法条约法文本并无此句,根据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则教士不可在内地居住固属无可疑议”,并且美国“历任出使大臣皆不以为然”,“英国政府向来亦明执此议,不肯援此条为其国教士可入内地居住之例”。因中国对外人无管辖权,所以不便让外人任意居住。不过因传教是慈善之举,各国偏袒教士,所以教士进入内地官府并不干涉,本来美国也可援此专许教士入内地居住。但为传教士谋取超越其他国民的特权与美国法律法无歧视不符,所以欲修约为教士另立专条必须获得中国首肯,而要达此目的必须让中国官绅明了教士所为乃有益中国之事业。田贝明了第六款作伪,也清楚美国历来政策,但似乎并不排斥为教士争取,不过10年过去并未成为现实。 直到1895年初,164名美国传教士联名向美国总统和参议院请愿,要求在中美条约中明确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居住,并可以个人或教会的名义持有房产。传教士们还特别指出所求并非新权力或特权,因为中国政府已给予传教士在内地居住权好多年,只是要求在条约中明确加入。在请愿后不久,成都教案、古田教案等先后爆发,面对教案纷起,民教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1896年9月田贝在国务院指导下起草了五条阻止排外骚乱的办法,经国务院同意后于1897年2月正式报给总理衙门。其中有两条与美国传教士在内地居住和置产有关:第一条为请中国政府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承认美国传教士有权在内地居住;第二条是说明美国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购地,并可以差会或教堂名义持有契据。 总理衙门对第一条的答复是:“这一权利在条约中已有。中央政府已经下令要求对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进行保护。”田贝虽然认为总理衙门的回复是很有价值的承认,但也指出直接的承认更有价值。对于第二条,总理衙门认为“尽管中美条约中没有提到,但在此问题上美国传教士应与法国传教士受同等对待”。对此间接回复,美方也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希望清政府发表一份公开谕旨,并下令各地官员遵守执行,而非仅在信件中承认这些权利。不过总理衙门的答复颇令人不解,因为条约只有通商口岸的居住权,并未言明内地居住权,中美中英中法条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总理衙门的意思也许是既然已给传教士在内地租买田地权,那就相当于已经给予内地居住权了。 直到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订立,美国教会内地置产权才得以实现,该约第十四款规定:“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这一条款为美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各地租赁房屋、地基的权利,尤其是“永租权”,这在其他条约中是没有的,但永租并不等于购买,因此在根据中美条约美国教会始终没有取得购地权。但这一条款也带来问题,因为条款是“美国教会”而不是“美国传教士”,那么不属于任何差会的自由传教士是否有权到内地置产就成了一个新问题。1906年3月22日美国国务院在给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指示中表示根据中美间的条约自由传教士无权到内地置产,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权利让予了传教士,国务院并不反对其在实际中获得这种权利。 从严格的条约意义而言,只有美国在1903年中美新约中获得了内地租赁和永租房地权,但没有购买权,英法则始终没有获得内地置产权。尽管法国通过“柏尔德密协议”使清政府同意了天主教可在内地置买田地,但该协议不是条约。中法双方从未正式公布或签署过“柏尔德密协议”,这一协议是法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在往来照会中形成的,因此只能算是清政府给予法国天主教的一种特权。清政府考虑到宗教活动的慈善性,在明知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不仅同意了“柏尔德密协议”,也默许了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到内地置产。然而深入各地的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教堂、医院和学院,还引发了无数的教案,其中置产问题就是矛盾的焦点之一。正如马士评价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这一规定以巨大的权力武装了天主教士,便于他们扩大宣传到内地去,并注定引起未来的很多摩擦。 对于传教士深入中国各地置产传教的事实,以及清政府的默许,英美政府采取了“大同小异”的态度。所谓“大同”即两国均明确表示传教士无权在内地置产,但也并不要求传教士从现有的传教点撤离,一旦发生纠纷也不会坐视不管。也就是说,英美在承认传教士的既得利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小异”是指与美国相比,英国希望能够尽量将传教活动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减少民教冲突,进而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维护其在华经济利益,因此不支持其依据“最惠国待遇”享有法国传教士的特权。而美国却支持传教士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与天主教一样的特权,并积极地为此提供帮助和保护。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