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师之师邓之诚先生(1887--1960)小照  1997年6月,于学位授予仪式后,与导师锺翰先生合影  1994年春,永君留影于清代翰林院故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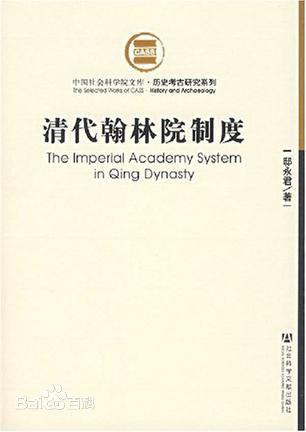 拙著《清代翰林院制度》2007年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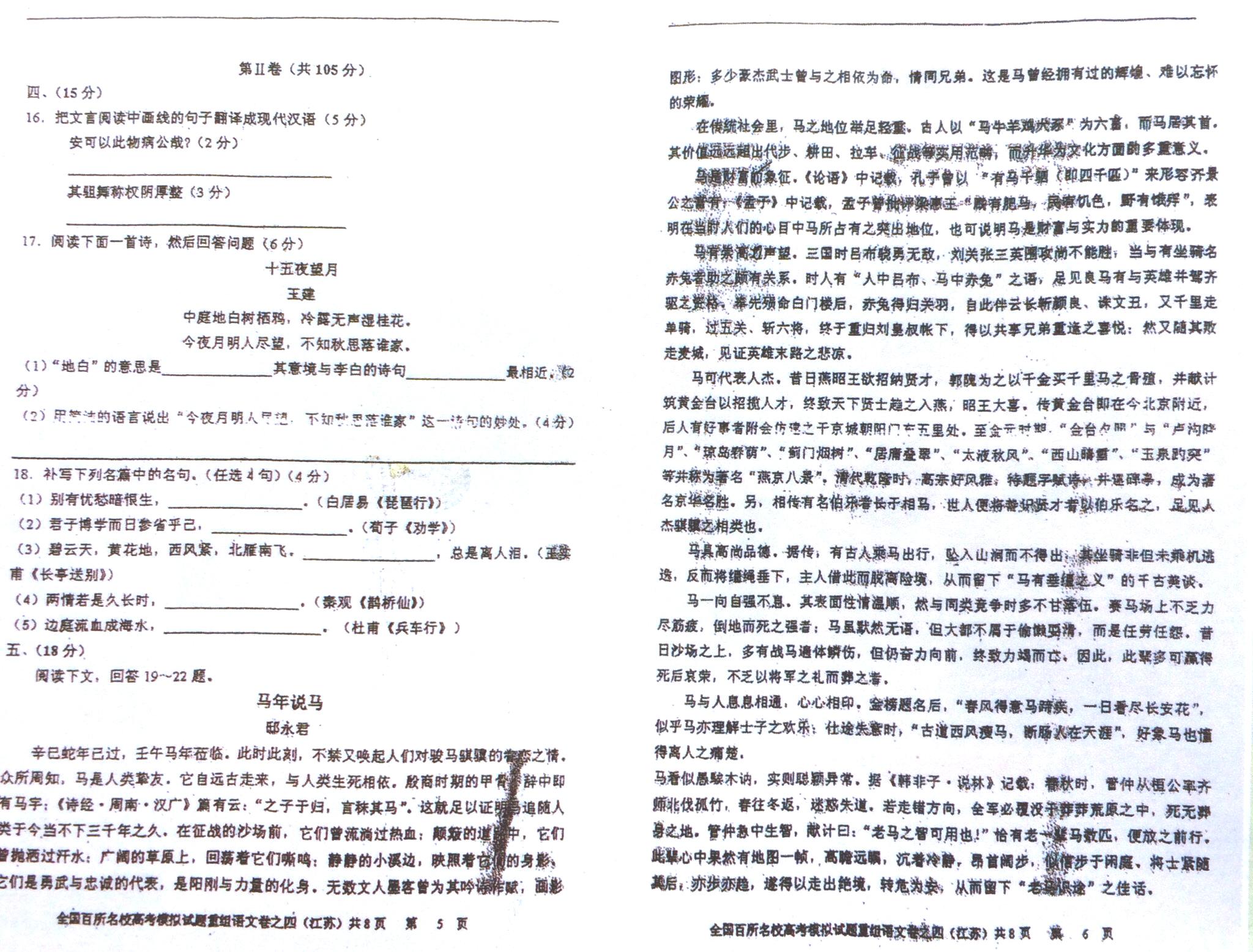 江苏省2002年高考语文模拟试题所用《马年说马》 十年前,吾曾撰《关于中国新史学之思考》一文,后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文中提出如下观点: 评判史家,我中华历来有自己的标准,讲求思想深邃,通今博古,文采上乘,德才学识兼而有之。而当今诸多史家,却视野狭窄,才思枯竭;史学著述骨瘦如柴,干瘪生硬,缺乏情感之交融,才情之流淌。其实,史家诸多精彩之论,断难仅从客观史料中必然推演得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综观当今史坛,虽有不少前辈上下求索,不舍昼夜,华发苍颜,著述等身,然其成果能否成为传世佳作,却不敢恭维,见仁见智。其中一大原因,即行文水准远远未尽人意。 本文拟将二十年来吾于行文风格方面之些许心得奉上,冀与诸同道切磋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正之。 就行事与写作风格而论,我们五零后一族,无论处世理念,还是行文风格,皆因自幼耳濡目染,颇不乏造反思维,斗士遗风,惟我独尊,偏执狭隘;行文更是难脱文革语体,信口开河,豪情万丈,气冲霄汉,声嘶力竭。而最缺乏者,无疑是自知之明,人文精神,谦逊美德与学术滋养。因此,产出之“科研成果”与“高论”、“雄文”,大都内容干瘪,空洞乏味,令人不忍卒读,却敝帚自珍,怡然自乐。 就本人而论,所谓写作基础,全部来自黑板报、决心书、批判稿等文革范式,尽管经多年恶补,但童年记忆最为清晰,熏陶最为浓烈。拼凑起来的知识积淀,究其大要,无非是“红宝书”、《老三篇》及样板戏唱词,再有就是革命歌曲与重大社论授予我们的豪言壮语,皆烂熟于心,萦绕于腹,经长期而强烈的反复刺激,已达到倒背如流,至死难忘之境地。而其他种种,均属后来叠加,因基础太差,凹凸不平,所以整个知识结构显得杂乱无章,摇摇欲坠。好在吾入道甚晚,四十岁前几乎无机会与能力发表文章,反而未露马脚,真不幸中之大幸。 误打误撞而考取北大历史系硕士生,是吾一生命运转折之点。吾靠突击背诵词条及几分小智小慧而侥幸过关,入学后才意识到,词条背后所依托的宏富史料,竟几乎一篇未读。在导师袁良义先生指导下,吾按为吾开列之《必读书目》逐一恶补,得以渐窥门径。良义先生祖籍安徽宣城,受桐城古文派熏染至深。以“独立思考、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客观公允”为训,授吾以治学之基、撰文之道。先生嘱吾云:“史学属于科学,而文学属于艺术,二者尽管有联系,但绝不可混为一谈。既然投身史学,自当循规蹈矩。尽量运用中性词句,行文以平实、精准为上,感情色彩应降至最低。尤不可轻发妄议,以论代史。”在先生指导下,吾完成硕士论文《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计三万余言,后全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成为本人立身之作。 然而,吾原本最喜古诗词,亦偏爱韵文骈赋,并对正史鼻祖司马迁老前辈之《史记》笔法心仪神往。尽管当时谨遵师命、亦步亦趋,然自忖有些文采,辄思“拽文”,却不能尽兴。不免常生压抑之感,心戚戚焉。 忝列锺翰先生门下,终于时来运转。先生治学一大特色,乃秉承先师邓之诚(文如)先生家法,对字工夫要求甚严。注重行文质量,结构严整,字斟句酌,绝不止于文从句顺,而是崇尚行云流水。锺翰先生得邓师真传,总结归纳为“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乎、者、也;史料力求准确可靠,立论力求精当公允,行文力求洗练流畅,结构力求紧凑合理;不用乖僻字,不引艰深典,不坠无谓谈,不惜文章短”。嘱吾精读邓师祖所撰《古董琐记》、《中华二千年史》等经典,并断言“他年尔若能得文如师文笔之半,即可纵横天下,卓然成家”。吾谨遵师命,坚信不移。 谈及白话文体,先生在肯定其为当今潮流的同时,曾批评道: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先生要求,写文章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之原因,殆乎此也。关于文章节奏之掌握,先生认为以四字句为基干最为恰当,但应适当变通,以免生硬刻板;要兼用三字、五字者,六七字一句偶尔也可用之,再长则不美,一般不宜超过十字,因长句会使读者有喘不过气之感。先生援引桐城三祖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等三方面为标准,并以当今学术话语予以阐释。认为“义理为思想性,即构筑理论之框架,属于哲学层面之精神关怀;考据即学术性,乃取舍史料之方法,属于史学层面之学术功力;词章即可读性,即结句行文之风格,属于文学层面之造诣水平。故而就现代史学而言,根基不仅在史料之考据,哲学层面之义理当居首位,而文学层面之词章亦必不可少。最为庆幸者,先生对我“拽文”之好,不但未予打压,反而十分赞赏。重申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遗训,强调学者若思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并长期为我的习作修改润正,授以诀窍与机宜,使吾登堂入室,渐有心得。另一方面,先生亦强调曰:“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须在严谨精炼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且一定要发挥有致,否则难免过犹不及,以末伤本,反招诟病。”在先生耳提面命之下,吾受益良多,写作风格已悄然改变,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并积三年之力,完成博士论文《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于2002年由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名曰《清代翰林院制度》;2007年,又作为首批入选成果,收于我院“学者文库”再版。封底刊有吾师钟翰先生之评语:“本书论点鲜明、论据可靠、论证充分、文笔流畅、结构严整,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学研究专著。”因导师首肯,加之学界认可,此著荣膺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吾亦由此跻身史坛,安身立命。饮水思源,皆先生点拨教化之功也。 任职民族所后,吾于研究科研任务之同时,开始撰写散文随笔。尽管不算科研成果,但属真心喜好,兴之所之,不求回报,唯觅知音。而民族所离中央民大教授公寓甚近,所以尽管已经毕业,我仍不时去锺翰先生家中拜望并请教,而得益最多的领域,即谋篇之法、撰文之道。2001年底前后,锺翰先生曾与我谈道:“欲思文章精美耐读,适当引入骈文因素,应是妙法。曩日燕园问学期间,邓文如师曾命我向张孟劬尔田先生求教骈文写作之法。孟劬先生颇擅四六,且诲人不倦,使我笔力大进,得益良多。你有拽文之好,若能在此方面多用心思,必会有所收获。当然,正宗骈文作起来费力,若功力不逮,极易搞成不伦不类,招‘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我只是建议你将其节奏感强,用词考究、对仗工稳、行文顺畅等特点引入文章即可,而非严格按照四六句式而作茧自缚。且务必注意篇幅不宜过长,长则难以凝炼,反而不美。写作题材亦很重要,以不美之物为题材,则万难写出妙曼之文也。”寥寥数语,令吾茅塞顿开;且深以为然,频频称是。 吾过去亦甚喜骈文杰作,尤其是初唐王勃所撰《滕王阁序》,每每诵之,辄拍案叫绝,心仪神往。虽偶有效颦之念,终因自忖才情不及而放弃。此番幸得点化,不禁手头发痒。便思写上几篇习作,请锺翰师指点。转眼壬午马年春节将至,又得《院报》副刊编辑杲文川兄约稿之命,为《春节专版》撰写生肖随笔一篇,题材为马。吾当时就想到,马形象高大,姿仪优雅,是撰写美文之难得题材,故而立即应允,并按锺翰先生指点,以起、承、转、合之顺序安排文章结构,适当融入骈文因素,且字斟句酌,尽量压缩篇幅,遣词炼句,逐字敲打,撰就《马年说马》一文,约3000言。真可谓绞尽脑汁,索遍枯肠,冥思苦想,不遗余力。文中有两段融入骈文因素之段落,分别安置于第二段与倒数第四段,达到了预期效果。 文章发表后,好评如潮。当年五月,本文即被江苏省选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阅读范文》,从而大大激发了我撰写散文随笔之兴致与自信。此后,吾笔耕不辍,曾连续12年为《院报》春节专版撰写并发表生肖随笔,且至今已被《光明日报•春节专版》三年以主旨文章连续刊用;此外,另发表各类作品近三百篇,得到不少读者谬爱。到目前为止,已有14篇作品陆续被选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对吾“拽文”所获一得之功,锺翰先生曾十分欣慰,不时予以鼓励。于激励吾迎难而上、不断探索,作用至大。转眼间二十载时光忽焉而过,吾业已初步形成特点鲜明之行文风格。饮水思源,皆钟翰先生点化教诲之功。 2007年12月12日,锺翰先生溘然仙逝,驾鹤西归。吾等顿失山斗,四顾茫然。悲痛之余,唯有将先生所传之学发扬光大,方不辱使命,告慰恩师。墓址择定后,同门诸君将撰写先生碑文之任,委之于吾。吾诚惶诚恐,苦想冥思,以207字,将先生一生辉煌浓缩升华,以垂永久。文曰: 师姓王氏,讳锺翰,祖籍湖南东安。十龄就傅,后赴雅礼,嗣入燕大,从邓文如、洪煨莲诸师游。敏而好学,博闻强记。传邓师学,字斟句酌,行云流水;遵洪师命,专攻清史,毕生不渝。而立年撰《清世宗夺嫡考实》,崭露头角;不惑岁掌中央民院教席,授业终身。其间校勘史籍,枣梨《列传》;发微辩难,裘集五《考》;体大思精,誉满士林;海内同侪,尊为山斗。循循善诱,成就者多;门人廿余,情若父子。性喜豪饮,弗逊太白;兰馨鹤寿,远胜湘绮。 师母讳荫松,姓涂氏。贤淑敦厚,相执偕老;大爱无垠,子弟怀之。有子楚云,女湘云、应云,孙禾。皆自强自立,湘云守其学。 戊子春日众弟子叩述 碑文由王忍之先生以魏碑体书丹,勒之贞珉,冀存恒远。以此抒桃李报春之情、记先生再造之功、慰吾师在天之灵,吾心稍安矣。 随年齿日增,吾愈发认定,撰文之道乃当代学者之一大短板。入民国后,因桐城古文派无奈淡出,白话文长驱而入,浅薄无品,飘然失根,书面语口语化、粗鄙化横行无忌。至今百年已过,而行文风格竟一直无范可依,仍处于“旧规尽破,新规未立”之过渡阶段,真真“路曼曼其修远”也。绝大多数学人,尽管倾其全力,奋笔疾书,终身劳顿,著作等身,而行文水准却一直于低层次徘徊,于撰文之道毫无长进。究其原因,乃既无人点拨,复无心感悟焉。逝者不复生,青春安可再?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来日方长,任重道远,若仍随心所欲,狼奔豕突,西风瘦马,踉跄而行,势必重蹈覆辙,令人扼腕。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信然。对于学者而言,立言于当时,流布于后世,则足以不朽焉。欲“虽久不废”,则须精研撰文之道,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吾尝于首部随笔集《愿将心事付瑶琴•自序》中提出:“诗词乃文章之浓缩与升华,则文章乃诗词之放大与延伸。”若以写赋诗填词般殚精竭虑、炼句择词,“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又何愁文不美,名不彰、道不传哉! 金代大儒元好问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悟其意旨,乃赋得好诗,可任人欣赏,而个中奥秘,则不可传于他人。于资源共享、思维开放的当今时代而言,此种理念已明显老旧,不合时宜。其实,金针无非工具,更为珍贵者,绣技也。吾一直认为,授人以鱼,远不如授人以渔。故将心中块垒和盘托出,以祈就教于大雅君子。 永君按:五零后一族,颇不乏才疏志大,好为人师,眼高手低,痼疾难改者,本人尤甚。谦谦君子固然可爱,低调虚心确属美德,然作为从业专家,于自身领域却一生唯唯诺诺,欲言又止,左顾右盼,语焉不详,则非“虚心”,而是“心虚”也。故而大言不惭。读后一哂,聊作笑谈无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