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仲殊的学术生涯与治学思想——《王仲殊文集》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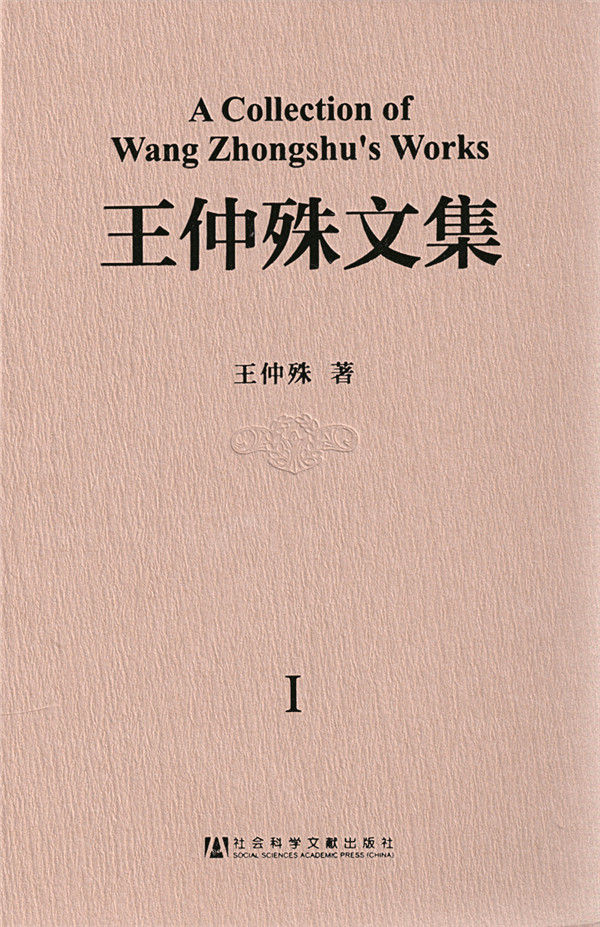 时值王仲殊先生年届九秩之际,学界期盼已久的《王仲殊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终于面世,这是继《唐弢文集》《夏鼐文集》《罗尔纲全集》之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又一学术经典。《文集》共收录王仲殊先生的代表性论文70余篇,并节录部分田野考古报告。编者将《文集》厘定为四卷,卷目依次为“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和“中国古代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限于篇幅,王仲殊先生出版的中外文学术专著,《文集》一概没有录入。 王仲殊先生接受过系统的田野考古训练,拥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兼具良好的外语基础,其治学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界可谓别具风格。王国维曾经说过:“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关于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夏鼐先生也曾生动地说过,二者的关系“犹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王仲殊先生的父亲曾长期担任宁波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他自幼便受到父亲的熏陶。今天我们回头看王仲殊先生的研究,举凡碑文、墓志、玺印、镜铭,都受到特别重视,并与传世文献相参照,表里求证,相得益彰,堪称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结合的典范。举例而言,著名的好太王碑碑文有“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之句,这一段文字通称“辛卯年条”,因为涉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但是“以辛卯年来渡海”如何标点、解读,中日韩诸国学者莫衷一是。王仲殊先生举葛洪《抱扑子》和陶弘景《真诰》等六朝文句为例,说明“来渡”是古汉语中常用的动词搭配,故辛卯年条应该标点、判读为:“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济)、(任那或加罗)、新罗,以为臣民”。此论一出,中、日、韩三国学者纷纷表示支持,聚讼多年的“辛卯年条”问题尘埃落定。 汉唐都城制度研究和中日都城比较研究是《文集》的重要内容,王仲殊先生曾主持西汉长安城遗址和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考古发掘,他在考古实测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绘制的“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北魏洛阳城平面示意图”时至今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20世纪60年代,王仲殊先生作为中朝联合考古队主要负责人,主持了渤海上京龙泉府都城遗址的发掘,并编写了发掘报告《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文集》有节录),该报告是目前有关唐代渤海国考古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1950年,夏鼐先生在王仲殊大学毕业来到考古研究所之初,就与之探讨其学术发展方向,考虑到王仲殊文献功底好且日语优良,便鼓励他向汉唐考古和中日交流史的方向发展。纵观王仲殊先生60余年来的治学历程,可以说正是沿着这条学术道路发展的,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予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实属殊荣。 王仲殊先生关注中日两国古代都城的渊源关系。1983年,先生发表《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论证日本古代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的形制布局是模仿中国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与洛阳城,而非日本权威学者岸俊男先生所言的北魏洛阳城。后来他又继续撰文,论证洛阳城的影响。自魏晋以降,中国古代宫城正殿多以太极殿为名。王仲殊先生追本溯源,详考太极殿(日本称大极殿)的沿革,发现自曹魏至唐代,共有六处都城在宫城中建太极殿以为正殿,包括魏晋洛阳城、六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唐长安城等。而日本自8世纪以降,亦仿效唐朝都城制度,先后在平城宫、难波宫、恭仁宫、长冈宫、平安宫修建正殿大极殿。太极殿肇始于中国曹魏洛阳城,而终结于日本平安京,而后者又有“洛阳”之称,可以视为中日两国都城源流史上的佳话。 “三角缘神兽镜”是王仲殊先生研究日本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已达500余枚之多,而中国和朝鲜半岛却一无所见。此前日本学界多主张其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载魏朝皇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王仲殊先生从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制、纹样、铭文出发,论证其为三国时期东渡扶桑的吴国工匠在日本所制作,正如铜镜铭文所言“本是京师,绝地亡出”(“京”为地名,在今江苏省镇江,孙权曾以此为都城)。后来日本发现两枚“景初四年”铭铜镜,乃孤悬海外的吴国工匠错误使用历史上本不存在的“景初四年”年号所致(曹魏景初三年翌年已改元“正始”)。王仲殊先生有关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论证缜密细致,结论坚强有力,已成日本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1972年,日本奈良发掘了轰动一时的高松冢古坟,王仲殊先生确认高松冢古坟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与西安唐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为“同范镜”,而墓志记后者的下葬年代为武周神功二年(698年)。据此,王先生判断高松冢铜镜为第七次遣唐使于庆云元年(704年)从中国长安携归日本的,又因高松冢古坟壁画颇具唐风,其墓主人应为热衷于仿效唐朝文化、并负责编撰《大宝律令》的忍壁亲王,这一观点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和赞同。 1784年,日本志贺岛出土了有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印应为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给倭的奴国王的,但因印纽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被认为与汉印传统规制不合,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仍对此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56年,云南省晋宁石寨山西汉滇国墓出土一枚“滇王之印”的金印,王仲殊先生撰文指出,“滇王之印”为蛇纽,印文为刻凿,与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规格一致,同属汉王朝所赐,终于使将近200年来笼罩在“汉委奴国王”金印上的疑云顿时消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仲殊先生关于日本倭国国名的研究。日本学术界素有“倭面土国”之提法,以为其乃《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倭地三十国之一,是日本倭国国名源起之例证。王仲殊先生查证后认定,日本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倭面土国”,之所以出现误解,是因为如淳注《汉书•地理志》形容黥面的倭人“如墨委面”,而“委”字被《翰苑》作者张楚金误解为“倭”,并在文献传抄过程中由“倭面上国”再讹为“倭面土国”。此论解决了日本国名历史的一桩悬案,日本学者多有折服。 王仲殊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是站在通晓中国文史的基础上来探究日本考古学与古代史的,可以说是冯承钧先生所倡导“一国之史可补他国的不足”的经典学术范例。 学术的进步必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客观求实却是各时代学者们的共同追求。当年潘次耕在为其兄潘力田的名著《国史考异》作序时就曾经说过,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是“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以此形容王仲殊先生的治学态度,可谓正相吻合。 王仲殊先生之所以在中日两国学术界拥有很高声望,与他严谨治学、刚正不阿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日本很多著名学者,诸如岸俊男、西岛定生等先生都与王仲殊先生有厚重的交情,但涉及到具体的学术问题,双方都有过认真的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交锋。王仲殊先生秉持史实,据理力争,体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风格与气质。当年裴駰在评价太史公《史记》时曾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若以此比喻王先生的道德文章,毫不为过。这对于时下的青年学者来说,更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 (《王仲殊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四卷本,定价680元)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10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