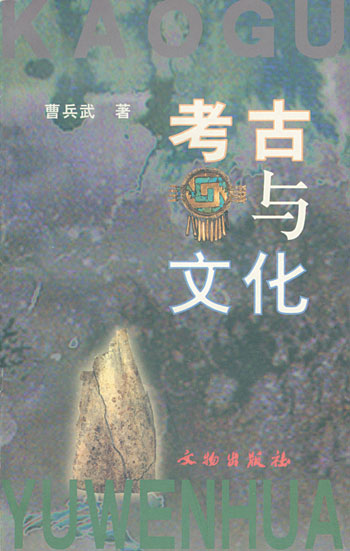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我的第一本考古随笔《考古与文化》1999年出版后,一个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您的这本集子没头没尾的,没有序跋,没有前言和后语,像一件来历不明的出土文物。我也开玩笑地回答:我留着“关键柱”(编者注:考古术语)呢。当时,那本集子是我从事考古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文章结集,而且主要是选择一般学者认为不成器的随笔杂文——虽然自认为每一篇都是有感而发的精心之作,但是毕竟不能算是正经的研究性文章,而且我知道当时有一些同行尤其是先生们对这种东西是颇有看法的,心里自然有些发虚。同时,当时我还有一个不小的野心,希望能够在《考古与文化》之后继续撰写《文物与文化》《博物馆与文化》《文化与文明》之类的学术随笔续集,因为我已经深深地感到考古学像一个巨大的时空实验场,正是观察文化与文明演进的一个良好的角度,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够从人类残缺不全但却扎实可靠的古代遗存出发,借助于考古学宏大的时空透镜与理论方法,管窥文化与文明的若干重大问题,逐渐构成一个系列。 那本小册子出版时我已经从中国历史博物馆((2002年起并入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与纯粹的出土之外的文物打交道的机会多起来了,涉及面也更宽一些,除了考古,也有机会从保护、博物馆收藏展示甚至是古玩交易管理等角度来体认文物的价值。我认识到至少是在我们国家,文物是一个比考古要大得多的概念,考古只是文物行业的一个小小的分支。如果说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等则主要是一项具有很强学术背景的社会性和公益性事业,因此与文化的关系更密切也更直接。加之当时正在阅读一些由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描述历史与文化的当代命运与未来路向而引发的论争,深感我们的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归根结底应该还是文化问题。相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文化是最繁难的,也是决定前几个选项气质与灵魂的东西。在关于文化的上百种定义中,我最心仪的是人类考古学中的“超肉体的适应方式”(新考古学家宾福德语)的概括。而无论是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的进步与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于个体的文化素质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及由文化而沉积起来的一个社会具普遍性的价值选向与适应方式。说开来,文化就是社会或社会中的个人的真正灵魂,是人类整体的适应性工具。我相信在弘扬这一认识的过程中,考古学应当是一门大有作为的学科,它虽然发掘、整理文明和文化的碎片,研究与拼凑人类的古代,但是它试图复原并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极具时间深度和空间幅度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图景。现代的社会过于复杂且趋于平面化,人类只有在这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整体图景之下,才可能进行当代和未来文化的体认、整合与文明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往碰撞,往往是见仁见智,各不相让,无异于瞎子摸象,甚至酿成惨剧,而考古学早已见惯历史舞台上的文化演替、文明兴衰,深知文化与文明之间像生命和生态系统一样的内在关联,正可以为塑造新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自觉意识提供宏阔的视角。 当时尚无法说出和说清这样一个宏愿,因此只好不了了之,没头没尾的小书像一篇悬在地层中和背景缺乏有效关联的陶片一样,等待着时间来完成它的复原与闭合,更默默地压迫着自己继续努力不敢放松。而今时间又过去十多年,当我重新整理这些年与考古相关的随笔杂文时,这样一个空洞宏大的设想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我的想法还是如同悬在半空的一件没有着落的出土文物,和时空地层及前后背景难以关联起来,于是只好选取部分有所关联的杂碎文章再次成册,供读者参考和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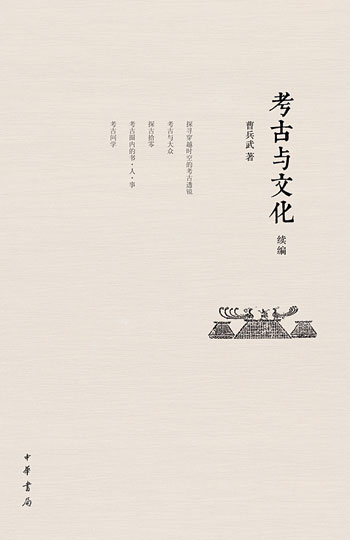 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的目的是复原历史,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考古学至多是发现一些关于过去的不清晰的碎片和一些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而其实,无论如何人是需要有个历史的,不管这历史是真实的、想象的,被人告知的还是自己发现的,人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属于谁,没有这种认同,人就不是人,民族、国家等认同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对于社会、人的发展来说,准确完整的历史记忆会比混乱破碎的记忆要好。考古学最伟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重新发现了早已淡出人类记忆的时间和历史,同时也在于其实物性——它为人类重新面对历史提供了一种活生生的物证,这种物证不仅供考古学家自己研究和解释,也供每一个愿意的个人去直面,获得自己的体验和认知。人自古以来就有极强烈的历史意识,但是由于各种局限却一直苦于没有很好的发现和留住历史的方法,考古学却可以让消失的时间、生生灭灭的文化和文明重新走进今人的视野。这使人的视野空前扩大。 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也曾经打算这次给这本小册子取一个具有考古学特征也更时髦一些的名字——《古往今来》或者《时间的模式》之类——虽然集子中基本上仍然没有收进我讨论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具体文化方面的论文,但是仍然希望藉此纪念一下这些年来伴随着考古学走进人类古代宏大叙事与时空场域的冲动和体验,同时也希望将它们交付于时间的浩荡洪流中,并希望它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是,考虑到寻觅思索所得仍然只是一鳞半爪,而且也从未找到所谓的规律与模式一类的东西,因此又渐渐决定放弃这个想法。几经犹豫,仍然将它们含混地称为是《考古与文化》的续集,以表示这个寻觅仍然没有完成。而且有幸的是,主要收集这段时期内我关于文物保护与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些思索也拟以《文物与文化》为题,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两相照应,读者可能会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更容易理解,而我自己在通往早年目标的路上又往前迈进了几步。 需要补充交代的是,《考古与文化》的许多小文基本上是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和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写出来的,时间上截止于1997年;这本集子的文章则大多数是1997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特别是2000年调入中国文物报社工作以后所作,很多是为了工作和报纸版面的需要急就的评论,因此有些篇什是相当粗糙的。与《考古与文化》一样,这些文章还是属于正文以外的杂文,因为从事考古的人都知道,希望从古代遗存的一鳞半爪中全面地、正面地、深入地探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问题往往是多么地力不从心,然而浩瀚无垠的古代,丰富新奇的考古材料和现象又不断刺激我们的遐想,让我们拿起笔来。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从各个方面涉及到考古发现的价值、理论方法、历史、考古学关注的热点、中国与世界考古的若干前沿、考古学的大众化等问题,也有一些读书心得和借工作之便对若干著名考古学家的访谈,这些考古学家都是中国考古学某一方面的巨人,做了很多历史性的工作或者提出过非常有意思的看法,自己从他们身上学习了不少东西,我想读者如果真的喜欢考古学,想探究一些人类古代的事情,他们的工作、生活、想法和观点应该是很好的阶梯。 (《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18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