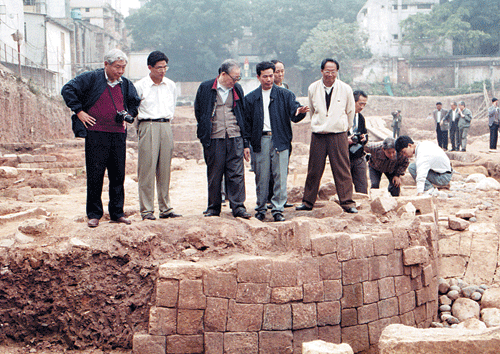 1998年徐苹芳(左一)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址现场考察 2011年5月22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辞世了。噩耗传来,南越王宫博物馆全体同仁感到无比的悲痛,我们深切怀念徐苹芳先生。广州文物保护事业特别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每走一步无不倾注着徐苹芳先生的心血和智慧,过去十多年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97年,广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西侧一建筑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一条长约160米的曲流石渠遗迹,为国内罕见。在遗迹的发掘和保护问题上,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林树森同志指示要求做到认真发掘,实事求是,听取国家文物局的指示。1998年1月9~10日,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对这一重要发现进行考察论证。专家组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率领,成员有徐苹芳、黄景略、宿白、郑孝燮、傅熹年、罗哲文、张忠培、李伯谦、傅连兴、刘庆柱、李准、王丹华、辛占山等13位考古、文物保护、古建筑、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徐苹芳先生被推选为专家组组长。专家组全体成员在考察遗址发掘现场及周边环境并听取工作汇报后,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召开论证会,会议由徐先生主持。专家组对遗址的发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中国宫苑实例,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古代广州城)、古代建筑史和古代工艺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徐苹芳先生还特别指出: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要对遗址做好切实的保护。正是由于徐苹芳先生等一大批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精深的认知,从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高度总结这个遗址的重大价值意义,以及他们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执著与努力,加上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南越国宫署遗址才有幸保护下来。为此有人写文章评价:“遗址受到如此妥善的保护,这是它的幸运,也是民族文化的幸运,更是华夏子孙的幸运。” 徐苹芳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和复原的考古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如广州这种古今重叠城市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州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据历史文献记载,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番禺城(今广州)以来,广州城市中心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1995年和1998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达6米,文化遗存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如何把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完整地揭露出来并尽最大可能复原当时的历史面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正因为有了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元大都遗址提出把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互结合研究的成功案例,为我们对古今重叠式城市进行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为此,在2002年以后的发掘中,我们采取了整体布方、逐层发掘、重点保护的方法,对遗址的堆积情况和各时期的建筑布局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成果显著。通过发掘确证:遗址既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南汉国的王宫所在地,也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郡、县、州、府官署所在地。遗址层层叠压,自下而上还有秦、汉、三国、两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等历史朝代的文化遗存,如同一部无字的编年史书,见证了广州城2200多年的发展历程。 徐苹芳先生对广州文物考古工作十分关心,只要有问题向他请教,他都会给予热心的帮助。2004年11月,我们在南越国宫苑遗址西北处发现一口南越国时期的渗水井,在井内出土100多枚南越木简,该发现不仅填补了广东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更大大丰富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是南越国考古的重大突破。2005年3月29日,徐苹芳先生在考察了南汉德陵和康陵后,又特地到南越国宫署遗址了解南越木简发掘和资料整理情况。徐先生生前曾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对中国汉代简牍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南越木简采取“木简整体提取,井体保持原状”的工作方法给予高度的赞同,并对下一步木简的清洗、脱色、整理和研究等提出许多建设性建议。 2009年,在配合南越王宫博物馆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在遗址西部发掘出五代南汉国时期的一处大型宫殿基址。该宫殿是一组由多进殿堂、庭院和回廊组合而成的大型建筑院落。其中第一进殿堂北面的庭院是用蝴蝶牡丹纹方砖铺地,尤其精美。囿于我们的认识水平,素仰徐先生在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地位,我们就这种花纹砖出现的时间和使用含义等问题特地写信向他请教。徐先生收到来信后,经过认真考证后回信认为:“蝶纹主要为铜镜上的纹饰,主要是唐镜。丝织品上有蝶纹装饰,金银品上少见,瓷器上似乎未用。南汉宫署用在铺地砖,确是首见。铜镜上所见多为对蝶,而南汉铺地砖是对角四蝶,这在建筑装饰纹上亦属孤例。”对于此砖的使用含义,他进一步推测或如“梁徐防赋得蝶依草诗曰‘秋园花落尽,芳菊数来归,那知不梦作,眠觉也恒飞’。砌此砖于园径上,正表示满园落花,群蝶飞舞之景。此乃假想也,仅供一笑。”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先生对中国历史考古研究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精通,对治学态度的严谨,以及对文博同行热情的帮助和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无私奉献,令我们敬佩和感动。 徐苹芳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中去,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应有的力量。 (《中国文物报》2011年6月17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
